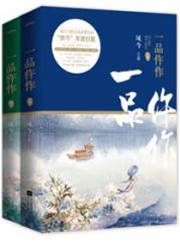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暴君的寵后[重生]》 158
在這段話下面,淮述安又以小字補了一段話:“那時年輕,見他相貌昳麗,為所迷便輕信了他。如今回想,他那時神采奕奕連一憔悴都沒有,怎麼會是在海上漂浮了三日的人?他之神異,早端倪。只是那時年并未察覺。”
安長卿按照封面上列出的時間,一本本看過去。手札上大多是寫二人相識相之片段,除了開頭提過一個名字,再未提起過余嶠的其他信息。加上許是年紀大了許多事都記不太清,記錄的文字也大多簡短零碎,安長卿一目三行看得極快,直到看到載德二十一年的記錄時,事才起了變化。
手札上寫道:“載德二十一年春,北地雨,逢大旱天。至秋時,糧食欠收,朝廷苛捐雜稅卻越發沉重,聽聞殍千里,死人無數。雍州南地,雖未大旱,但數月雨連綿,大壩決堤淹沒農田。朝廷不肯撥銀兩救災,災民死傷無數,瘟疫橫行……蕭歷來信于我,約我到京都共謀大事,余嶠好奇京都形,與我同行。此乃我此生最后悔之事,是我害了他。”
這一段字跡力紙背,足見淮述安心中悔恨。安長卿急急忙忙地往后翻,卻發現后面連著的是大片空白,翻過幾頁空白紙張,后面記錄卻直接跳到了兩年后的載德末年。
載德末年,前朝魏國因君主昏庸無道民不聊生。八位大柱國共謀起事,歷時兩年,終于帶兵攻了京都,推翻前朝建立新朝。其余七位大柱國共同推舉蕭歷為帝,改國號大鄴。
這中間三年如何淮述安并未寫出來,只是寫道:“我們花了三年時間占領各地攻京都,所有人包括余嶠都愿尊蕭歷為帝。余嶠曾說他是心懷天下的明主,是值得信任之人。但實則他不過是個貪權勢的偽君子罷了,我們都被他騙了。”
Advertisement
安長卿繼續往后看,卻發現同先前一樣,這一段又空了出來。不知是淮述安不愿意回憶,還是他怕寫出來被人窺探當年,遂刻意去了。
安長卿翻到最后一頁,卻見上面只寫了一句話:“余嶠不見了,若是當初我能早些帶他回雍州,或許一切都會不同。”
載德年間的記載到底戛然而止。安長卿了眼睛,正準備起去尋后面手札,卻忽然一陣頭暈目眩。蕭止戈及時扶住他,給他倒了杯茶水,讓他坐著緩一緩:“你先歇歇,不必看得那麼急。”
安長卿喝了一盞茶,又了眉心,道:“這些手札里有用的容太了,看到現在也只知道畫中人余嶠,跟淮述安一同去了京都,結識了太.祖以及另六位大柱國。但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卻無從得知。”
蕭止戈卻道:“我這邊的手札也沒找到什麼有用的容,不過我找到了一幅畫。”
他將手邊的畫卷遞給他:“跟西蜣那副畫一模一樣。”
安長卿將畫卷緩緩展開,就見那畫像果真與薛無送他們的那副畫一模一樣。但是一副在西蜣,一副卻在雨澤,這兩幅畫之間,必定有什麼關聯。
“我們跟淮如峪說一聲,將畫卷帶出去比對一番。”安長卿道。
薛無說薛常派出的商隊很可能是出了海,當初他們分析,自西蜣去海邊要經過雨澤國境。而這兩人又同時判出大鄴,顯然是有某種聯系。若是薛常派商隊出海是與淮述安合建鮫人墓,那他們一人保存一副畫卷便能說得通了。這畫卷上或許就藏著鮫人墓的線索。
蕭止戈看了看被夜明珠照得通明的庫,這里不見天日并不知道時辰,但他估著時候也不早了,便道:“出去再說吧,剩下的可明日再來看。”
Advertisement
安長卿坐下這會兒也覺得還有些頭昏腦漲,便帶上畫同他一起出去。本來以為出去時那兩個看門人會阻攔他們帶畫出去,卻沒想到對方并未阻止,只在他們出來后,又謹慎地鎖上了門。
兩人沿著臺階上去,才發現已經是月上中天時分。除了淮如峪的心腹侍從在廳中候著,淮如善也在。
見他們出來,淮如善困倦地打了個哈欠道:“那庫里可是有無數沒人,你們竟然在里面待到了這個時辰才出來。”
蕭止戈看了看外面天,問:“現在什麼時辰了?”
侍從回道:“丑時末了,王上見兩位貴客一直未出來,便奴候著。王上還在書房理政事。”
“久等了,庫中不見天日,分不清楚時辰,就耽擱的久了些。”安長卿道。
侍從彎了彎腰,說了一聲“我去請王上”便離開了。
倒是淮如善又打了個哈欠,睡眼迷蒙地看著他們手中的畫軸問道:“你們可找到了什麼線索。”
“確實找到一點線索,不過還有待確認。”安長卿道。
淮如善一聽,立刻神抖擻地湊過來:“是什麼?快給我看看。”
安長卿將畫軸背到后去,慢吞吞道:“大鄴沒有大象,也沒有白孔雀。”
“???”淮如善出來的手僵在半空中,瞪圓了不可置信地看著他,氣道:“我現在知道了,你比我哥蔫壞多了。”
安長卿笑出一口小白牙,像只機靈狡黠的小狐貍,又可,又好看。淮如善頓時就屈服于貌了:“行行行,大象送你一只,白孔雀也送你。你快給我看看。”
說著便手去他后搶畫軸。反正等會淮如峪來了他也會看到,這會兒安長卿就沒有跟他爭,將畫卷給了他。
Advertisement
淮如善將畫卷展開,興的表在看到畫中人時凝住了,他卷起畫卷,瞇起眼看向安長卿:“你不會是拿自己的畫像在訛我吧?”
安長卿道:“我訛你做什麼,這畫中人余嶠,大約……是我的祖先?”
淮如善將信將疑地將畫卷又展開細細看了一遍,方才發現了不同。他將畫卷在案幾上鋪開,看看安長卿又看看畫像,嘖嘖嘆道:“鮫人族可真是厲害,各個都是大人。我聽哥哥說那圣使容貌也是一絕。”
“你就記得這些七八糟的話,怎麼就不記得我你別摻和這事?”
一道聲音遠遠傳來,淮如善一回頭就看見他大步過來了,立刻端起諂地笑湊過去:“我記得啊。但我這不是擔心你嗎?多個人也多份力是不是?”
淮如峪瞥了他一眼,神有些無奈。到底沒有趕他回去,只目轉向安長卿與蕭止戈道:“這幅畫可是有什麼特殊之?”
安長卿先前并未同他說過畫像與西蜣寶之事,倒不是刻意瞞,只是事太多還沒機會說出來,因此淮如峪自然不知曉其中特殊。
“我這里也有這麼一幅畫,是西蜣先王薛常傳下來的。”安長卿將西蜣寶之事告訴他,正巧派去取畫的人也來了。安長卿將畫接過來都給淮如峪道:“你先看看吧,一模一樣。”
淮如峪接過畫像,鋪開放在先前那副畫邊上,發現果然是一模一樣。
“你們懷疑當初鮫人墓其實是先王與薛常一同建的?”淮如峪問道。
“沒錯。”蕭止戈道:“西蜣寶是薛常留給畫中人,也就是余嶠的。而淮述安建鮫人墓,也是為了余嶠。他們二人相識,會合作也并不意外。”
Advertisement
安長卿補充道:“可惜那些手札略去了許多重要事件。若是能弄清當年發生了什麼,我們探尋鮫人墓或許會簡單許多。”
淮如善沉思一陣,緩緩道:“其實鮫人墓雖是為了余嶠所建,但我翻遍所有手札,卻覺得余嶠也許本沒有葬在鮫人墓。它雖稱作鮫人墓,但其實只是一座孤島。”
他蹙起眉,似乎不知道如何闡述:“我從前翻閱那些手札時就覺得,先王記述中,并未當余嶠已死。鮫人墓不像是墓地,更像是打造了一座海上桃源,他一直在等著余嶠回來,但至死也未等到。”
他從前約有這種想法,但并不能太過確定。直到今日聽到了薛常的言,方才覺得自己的猜測或許并沒有錯。
“先王和薛常,好像都覺得余嶠不會死,并且還會再回來。”
安長卿被他一點,眼睛也亮了一下:“沒錯,淮述安最開始的手札上有一段話,說自己早該發現余嶠的神異之。能被稱之為神異的……會是什麼?”
“長生不老。”蕭止戈忽然開口道。
見三人都看向自己,他沉聲道:“我看了庫中留存的余嶠畫像,你們有沒有發現,那些畫像明明間隔了數年,但余嶠的樣貌卻一點都沒有變嗎?”
從淮述安在海上遇見余嶠,到他們建立新朝,中間一共經歷了七年。手札中從未提到余嶠的年歲,但從零星片段中大約推算,余嶠與淮述安差不多大。從弱冠之年到近三十,便是老的慢,也不可能一點變化都沒有。但那些畫像中的人,除了裳裝扮變化,容貌卻沒有半點改變,連一細紋都沒有增加。
雖然也可以解釋淮述安畫畫時特意畫了余嶠年輕的模樣,但是按照這種種跡象來看,更可能的是余嶠這些年里,樣貌并未變老。
如若余嶠長生不老,那薛常與淮述安的態度便可以解釋通了。
安長卿一時啞然,但是仔細想想又覺得這猜測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否則薛常與淮述安怪異的態度本說不通。
“可是這世上,當真有人能長生不老麼?”淮如峪擰起眉,只覺得一寒意從腳底鉆上來。前朝總有帝王追尋長生之,但他卻只覺得可怖。試想當相識的親人朋友一個個地死去,最后只剩下自己孑然一,孤獨地活著。這不是恩賜,分明是懲罰才對。
安長卿下意識想說長生不老太過神異,話要出口時,忽然想起自己重生之事,又將邊的話吞了下去,他擰著眉道:“是真是假,去鮫人墓一探就知。”
三人相對無言,淮如峪道:“罷了,我們在這瞎猜也無用。我盡快將事安排妥當,咱們盡早出發去南海吧。”
作者有話要說:
喏喏:不需要搶,大象和白孔雀我都有了。
慫:給喏喏打call
——————
謝在2020-01-12 22:46:12~2020-01-13 21:59:38期間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營養的小天使哦~
謝投出地雷的小天使:紫月閣主 1個;
猜你喜歡
-
完結1754 章

肥婆種田:山裡相公太腹黑
一朝穿越到古代,塗新月發現自己成了死肥婆。不僅又胖又傻,還被表妹和未婚夫聯手設計,嫁給了村裡最窮的書生!沒事,她可是21世紀的特種兵軍醫!還有靈泉在手!渣男背叛?一巴掌啪啪啪打臉!極品親戚?一腳送她們上一天!說她醜的?她搖身一變美瞎對方的眼!隻是,她本想安靜的種種田,發家致富。那俊俏的小相公為何像打了雞血,不僅夜裡猛如狼,還一不小心權傾了朝野……
314.9萬字8.25 728874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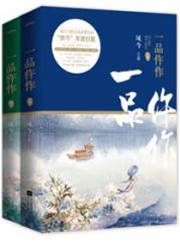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7667 -
連載287 章

世子嫌棄,嫡女重生後轉嫁攝政王
雲念一直以為自己是爹娘最寵愛的人,直到表妹住進了家裏,她看著爹爹對她稱讚有加,看著母親為她換了雲念最愛的海棠花,看著竹馬對她噓寒問暖,暗衛對她死心塌地,看著哥哥為了她鞭打自己,看著未婚夫對她述說愛意,她哭鬧著去爭去搶,換來的是責罵禁閉,還有被淩遲的絕望痛苦。 重來一世,她再也不要爭搶了,爹爹娘親,竹馬暗衛,未婚夫和哥哥,她統統不要了,表妹想要就拿去,她隻想好好活下去,再找到上一輩子給自己收屍的恩人,然後報答他, 隻是恩人為何用那樣炙熱的眼神看她,為何哄著她看河燈看煙火,還說喜歡她。為何前世傷害她的人們又悲傷地看著她,懇求她別離開,說後悔了求原諒,她才不要原諒,今生她隻要一個人。 衛青玨是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從未有人敢正眼看他,可為何這個小女子看他的眼神如此不成體統,難道是喜歡他? 罷了,這嬌柔又難養的女子也隻有他能消受了,不如收到自己身邊,成全她的心願,可當他問雲念擇婿標準時,她竟然說自己的暗衛就很不錯, 衛青玨把雲念堵在牆角,眼底是深沉熾熱的占有欲,他看她兔子一樣微紅的眼睛,咬牙威脅:“你敢嫁別人試試,我看誰不知死活敢娶我的王後。”
52.8萬字8.18 49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