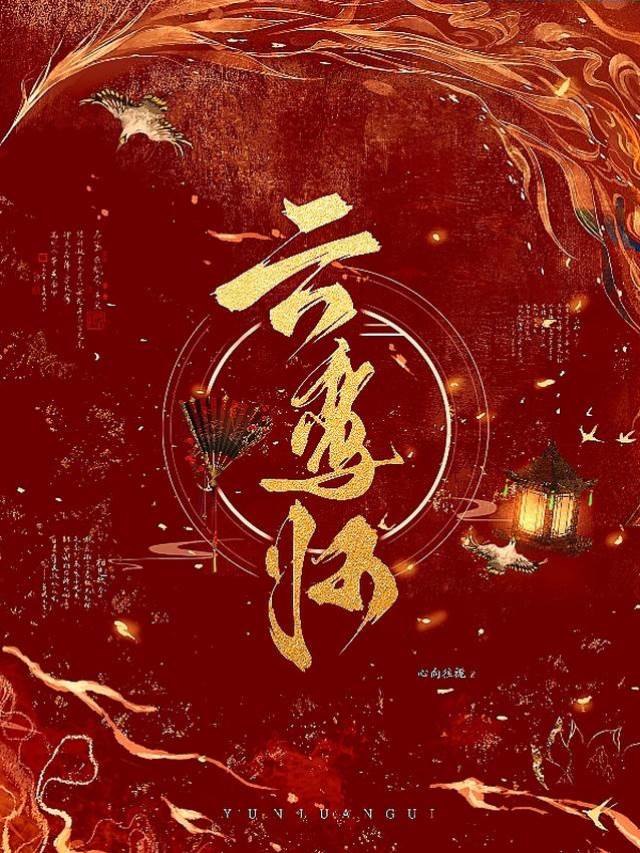《側妃上位記》 第19章
周韞回到錦和苑,才想起今日是孟安攸進府的日子。
聽時春說罷,有些驚訝:“已經進府了?”
午時還未過,相較于方偌近傍晚時剛進府,孟安攸來得有些早了。
時秋吩咐人打水進來,周韞凈了手和臉頰,扔下了帛巾,就見時春遲疑地點了點頭。
周韞沉默了片刻,才堪堪回神:
“進便進罷,先傳膳。”
時秋擔憂地喚了一聲:“主子……”
周韞抬眸,時秋頓時噤聲,將余下的話掩去,只心中還存著些擔憂。
這頓午膳,周韞用得有些食不知味,倉促用了幾口,就放下了木著。
時間越來越晚,快至黃昏時,錦和苑就越發寂靜。
前院的消息素來傳得很快,今日爺會去綏合院用晚膳。
消息傳進錦和苑的時候,婢剛呈上茶水,不經意手輕抖,險些滴灑了周韞一。
那婢臉剎那間煞白,跪地:
“奴婢不是有意的,求側妃息怒。”
周韞側躺在榻上,翻著賬冊,腳上的繡鞋要褪不褪,弓著腳背,斜眼覷向地上跪著的人,有些嫌棄:
“不經事的東西。”
爺不過去了一趟綏合院,這錦和苑就半日沒了點聲響。
這還只是孟安攸,日后可還了得?
抬眸,漫不經心地掃了一圈房噤若寒蟬的下人,撇了撇,輕哼:
“行了,別守著了,下去罷。”
懶得和這些人多說,雖經不得事,但好歹知曉規矩。
待人皆下去了,周韞才扔了賬冊,稍稍擰了擰細眉,有些心不在焉地斂眸。
時秋和時春面面相覷,們知曉,王爺進了旁院子,主子心中不舒坦,可們不知該如何勸。
其實周韞不用們勸。
比任何人都知曉,這種景遲早會遇到的。
Advertisement
自進宮,見得多了子失意,單只說姑姑,誰人不羨慕珍貴妃得圣寵多年,可即使如此,圣上不是依舊三年一選秀,從未停止。
周韞懨懨地斂眸:“乏了,歇著吧。”
時春想說什麼,卻被時秋攔住:“奴婢伺候主子洗漱。”
待洗漱后躺在榻上,夜深人靜時,才睜開眸子,臉上沒有一困意,甚是清明。
翻了個,枕在錦被上,強迫自己閉上眼,指尖卻無意識地捻著錦被一角。
夜深且長,孤枕難眠,這不過是第一日罷了。
一側耳房,時春推開時秋的手,有些擔憂和不解:“你作甚攔著我?主子明擺著緒不高!”
時秋沒和爭吵,坐下拿起繡帕,遞給,只平靜地低聲說:
“那你要怎樣?”
“勸主子嗎?”
“這般不好嗎?”
連問三句話,時春啞聲,吶吶遲疑地說:“這怎會好?主子不高興啊。”
時春的聲音越來越低,眸子稍紅,狠狠接過帕子。
一夜到亮。
不過卯時,綏合院就已燈火通明,張崇走進來,剛準備伺候主子爺穿,就見床榻上的孟良娣披著外衫起了,地走到主子爺前:
“妾伺候爺穿。”
傅昀沒說話,只是平靜地應了聲。
張崇一頓,退后了一步,主子爺在錦和苑歇久了,倒他忘了,后院主子每日該是起伺候爺的。
孟安攸臉上春意盎然,作間輕,甚是規整理好腰帶,才地服,問了句:
“爺,妾剛進府,今日可是要去給側妃姐姐請安?”
忽地提起周韞,傅昀下意識皺眉,垂眸看了一眼,冷淡地說:
“你看著辦吧。”
其實沒有給側妃請安的規矩,徐氏等人那次,是因周韞第一日進府,該是見見這后院的人。
Advertisement
這之后進府的人就沒了必要特意過去一趟。
他話音甫落,孟安攸就為難地擰了擰眉。
自行看著辦?就是不知該怎麼辦,才問得爺。
傅昀低頭理了理袖,仿佛沒看出的為難。
總歸,去與不去,那人都要不高興的,他才不給人出主意,省得最后那人埋怨皆落在他上。
傅昀沒給孟安攸再說話的機會,待理好裳,就轉出了綏合院。
孟安攸見他態度冷漠,原先的褪盡,不忿地咬了咬,后的婢秀云走近,就聽見一句:
“爺究竟是何意思?”
想不想讓去請安,不過一句話的事,這般模棱兩可的話,怎知該怎麼辦?
秀云不知說什麼,只好說:“側妃如今管著后院。”
們昨日進府早,這消息還是從府中打聽出來的。
的言下之意,側妃管著后院,還是去與側妃請安為好。
孟安攸知曉這個道理,但還是煩躁:“就周韞那子!”
都是京城貴,又同是一屆秀,孟安攸就算對周韞了解不多,但總歸聽說過些關于的事。
更何況,昨日剛進府,就聽說了比早進府幾日的侍妾方氏,從錦和苑被抬著出來的事。
忽地說:“若非……我又怎會只是良娣!”
秀云知曉想說什麼,卻沒敢接話。
府上最想要的是賢王妃的位置,但們也知曉,本不可能,但有孟昭儀在,至側妃還是唾手可得的。
但可惜,一道圣旨,賢王府唯有的兩位側妃之位,皆有了人選。
們主子,只能退一步了良娣。
周韞昨夜睡得有些晚,時秋喚醒的時候,眸子里盡是乏意,手背遮住眼眸,含糊地問:
“何時了?”
Advertisement
“還未到辰時。”
周韞一頓,還以為是自己沒聽清,細眉擰起,不耐地睜開眸子,撐起子坐起來,著子:
“本妃作甚?”
傅昀宿在錦和苑時,都是辰時后才起的床,今日這般早喚,實屬反常。
時秋聽話音,就知心中生了氣,頓時低聲:
“是孟良娣,來與主子請安了。”
周韞一怔,終于清醒了些,倚在時秋懷里起,蹙眉有些不解:
“作甚子要來給本妃請安?”
又非是方偌,在府中毫無基,又被攔了人,才在進府第二日不得不來給請安。
時秋沒能給答案,周韞忍著不耐,起了,溫涼的帕子蓋在臉上,周韞才徹底清醒了過來。
待出了室,已是半刻鐘后。
周韞第一眼瞧見的,就是孟安攸一臉遮掩不住的春。
出乎周韞意外的,來人不止孟安攸一人,有些訝然地看向另一人:
“你怎得也來了?”
劉氏規矩地行禮后,才笑盈盈地說:“昨日就想來和姐姐說說話,姐姐可莫要嫌棄妾。”
周韞笑著覷:“貧,來人,給劉良娣上些糕點。”
見到周韞和劉氏說笑,孟安攸心中有些驚詫,也跟著彎請安,只不過似有些不舒適地扶了扶腰。
這番作態落旁人眼,劉氏一頓,不著痕跡地斂下眸中神,瞧了眼周韞。
側妃子素來不好,也想知曉這般況下,側妃會如何做?
然而,周韞懶洋洋地倚在梨木椅上,好似沒看見孟安攸這副作態,含著乏意,懨懨地說:
“你昨日剛進府,來本妃這作甚?”
刻意將孟安攸調到綏合院,就是不愿和孟安攸打道。
但卻不代表,人都裝模作樣到地盤了,還會當作看不見。
Advertisement
周韞心中冷笑,若非進了賢王府,依著孟安攸的份,擱往日,和說句話,還得挑心好的時候呢。
懶散態度一出,明顯沒將孟安攸放在眼中,孟安攸子稍僵,扶在腰間的手訕訕地放下,心中有怨,臉上卻帶了笑:
“正因妾剛進府,才想著來與姐姐請安,好有個可以說話的。”
似有些,又低了低頭,垂眸:
“爺也說,妾來給姐姐請安。”
王爺自是沒說這話,但知曉,不會有人拿這事去問爺,所以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心虛。
周韞捧著杯盞的作一頓,指尖按在玉壁上,卻人眸輕斜,含著些嗔怪地說:
“爺真是不會疼人!你昨日初經人事,怎能你過來請安。”
說:“本妃又非正妃,綏合院又離本妃這錦和苑甚遠,真是平白折騰你。”
一番話,直孟安攸臉上的褪盡,多了幾分尷尬。
劉氏險些笑出來。
孟安攸說爺特意來請安,只在說一件事,那就是爺昨日歇在那兒,還特意和說起請安一事。
爺是何人?若能親自和人代這些,必然是格外看重這人的。
側妃甚絕,你覺得爺這是看重?
就赤告訴你,爺若真心疼看重你,就不會你跑這一趟。
待周韞說散了后,孟安攸幾乎是紅著眼出的錦和苑,既是氣惱的,也是窘迫的。
劉氏看了場好戲,也沒有久留,只在離開前,笑呵呵地說了句:
“妾聽說,徐姐姐養了半月的病,也似快要養好了。”
周韞了然,這才是今日來的真正目的。
稍擰了擰眉,這徐氏倒是頑強,這種況都能養得好病,怎擔得起爺一句子骨差?
想到傅昀,周韞頓時憋了口氣:
“旁人來給本妃請安,他也真做得出來!”
沒忍氣的習慣,手中的杯盞砰得落了地。
碎片濺了滿地,殘余的杯盞卻是一路滾落,最后停在剛踏進來的人腳前。
猜你喜歡
-
完結1159 章

慕南枝
前世,李謙肖想了當朝太後薑憲一輩子。今生,李謙卻覺得千裡相思不如軟玉在懷,把嘉南郡主薑憲先搶了再說……PS:重要的事說三遍。這是女主重生文,這是女主重生文,這是女主重生文。
220.9萬字8 26428 -
完結226 章

首輔大人的白月光是我
尹湄剛到京城時,做了一場噩夢。夢中她被太子看上,陰鷙殘忍的太子將她當做玩物,她不堪折辱自盡而亡。眼看夢境一一實現,尹湄拼盡全力自救。★一場春日宴,宴中哥哥設局,將她獻給太子。尹湄記起這日來了不少權貴,包括首輔大人和瑞王。首輔大人沈云疏雖是新貴權臣,可傳聞他心狠手辣不近女色,恐怕難以依仗。瑞王溫和有禮寬以待人,是個不錯的選擇。尹湄好不容易尋到瑞王,可藥性忽然發作,她誤打誤撞跌進了一個人懷里。他松形鶴骨,身量頗高,單手桎住她宛如鐵索,“姑娘身子有異,可需幫忙。”“謝,謝謝大人,您真是良善之人。”“……”等到她醒來,看著身邊躺著那位朝中如日中天的權臣沈云疏,哭紅了眼,“不是這麼幫……”不是不近女色嗎?★新任首輔沈云疏在官場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心思深沉,人人畏之,卻討好無門,不知其所好。無人知曉他已重活一世。他仍記得上一世,太子邀他入府觀看“美景”,見尹家那位雪膚花貌的美人被太子鎖在金子鑄成的床上,滿身血痕、雙眸無光。待他終于手刃太子大權在握時,卻聽聞她自盡于東宮,香消玉殞。這一世,他顧不得什麼禮法人倫,在她身邊織了一張大網,只靜待她掉入陷阱。心機白切黑深情首輔X嬌軟可愛有點遲鈍的求生欲美人
34.3萬字8.18 44444 -
完結179 章

世子寵妻錄
林紈前世的夫君顧粲,是她少時愛慕之人,顧粲雖待她極好,卻不愛她。 上一世,顧家生變,顧粲從矜貴世子淪爲階下囚。林紈耗其所能,保下顧粲之命,自己卻落得個香消玉殞的下場。 雪地被鮮血暈染一片,顧粲抱着沒了氣息的她雙目泛紅:“我並非無心,若有來生,我定要重娶你爲妻。” 重生後,林紈身爲平遠軍侯最寵愛的嫡長孫女,又是及榮華於一身的當朝翁主,爲自己定下了兩個目標—— 一是:再不要把一手好牌打爛。 二是:不要與前世之夫顧粲有任何牽扯。 卻沒成想,在帝都一衆貴女心中,容止若神祇的鎮北世子顧粲,竟又成了她的枕邊人,要用一生護她安穩無虞。 * 前世不屑沾染權術,不願涉入朝堂紛爭的顧粲,卻成了帝都人人怖畏的玉面閻羅。 年紀尚輕便成了當朝最有權勢的重臣,又是曾權傾朝野的鎮北王的唯一嫡子。 帝都諸人皆知的是,這位狠辣鐵面的鎮北世子,其實是個愛妻如命的情種。 小劇場: 大婚之夜,嬿婉及良時,那個陰鬱淡漠到有些面癱的男人將林紈擁入了懷中。 林紈覺出那人醉的不輕,正欲掙脫其懷時,顧粲卻突然輕聲低喃:“紈紈,爲夫該怎樣愛你?”
28.6萬字8 16229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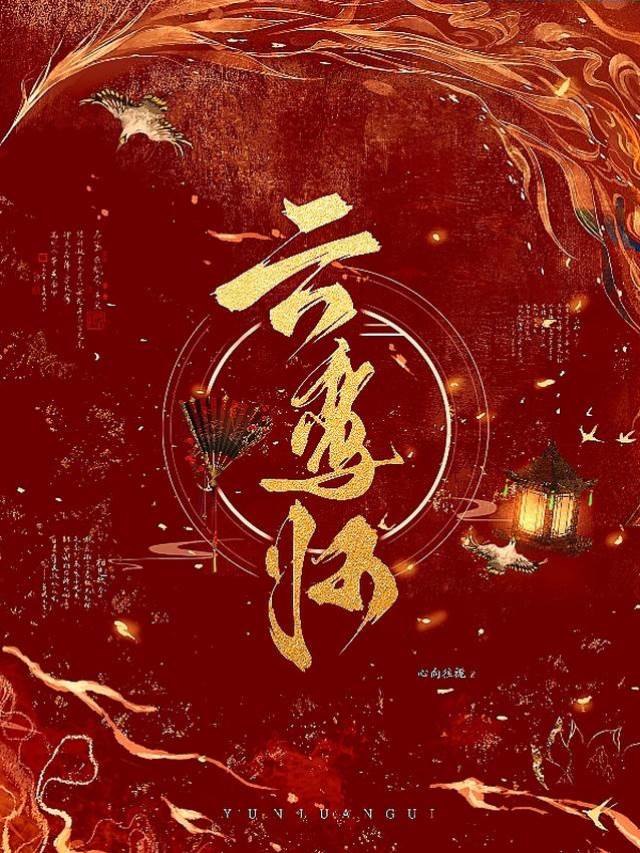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