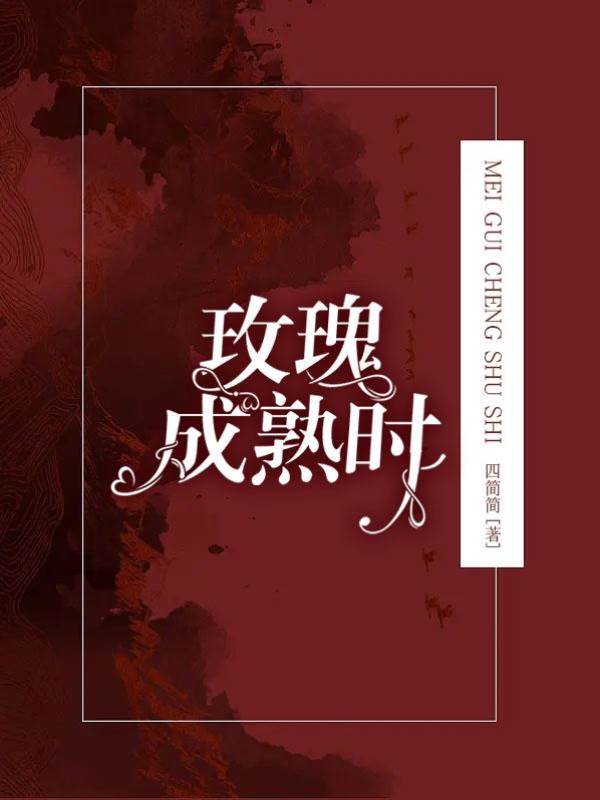《女校》 第一百二十四章 青紅
還能怎麼樣呢。
靳譯肯這個人賣起可憐來是一把好手,親完,回去的路上好說歹說,終于讓龍七暫時打消了讓他睡沙發的念頭。
對于會不會被連芍姿發現的擔心,也漸漸被近在咫尺的陪伴蓋過,開始跟靳譯肯聊些有的沒的,聊他在英國吃什麼玩什麼,喝過多酒泡過多妞。
他很識相,聊到最后那個話題時就把手機出來,說那幾個月跟所有人的聊天記錄都在這里頭原封不地留著,隨便看,敞開了看,發現一個貓膩算他輸。
“你這麼開心干嘛,一副早有準備的樣子。”
“沒,”他剛好停完車,“就喜歡看你查崗的樣子。”
真欠。
訂的是山腳的一家景區酒店,這個點沒有人走,從停車場到前廳到酒店長廊的路程都很安靜。
雨淋得上黏乎乎的。
所以回房間后又重新洗了個熱水澡,同意跟他同床了,但多的不能有,現在困得只想睡覺,就算不想睡覺,去檢查之前他也不能有什麼想法,給安安分分地在左手邊躺著,都不要。
靳譯肯不服。
趁洗澡的時候就開始一套一套地甩一些關于hiv傳播方式及保護措施的長篇大論,著兜,靠著門,慢悠悠地講,給聽得煩了,開玻璃門砸了個浴球,他的腦袋一斜就躲過,子紋不,不干擾地繼續叨叨。
吹完頭發上床,靳譯肯又以又又香抱著舒服為由,圈著不放,掙得都熱了,然后聽他說話,本來就怪喜歡他的,這種任又有界限的接快要了的命,手往他哪兒放都燙,后來干脆被握著放在他的膛口,他把上了,撐著手臂到上,抵著額頭,鼻息挨著鼻息,說想睡覺,靳譯肯說你睡。
Advertisement
說完就在上,還偏偏舌頭,就好像是他養的小兔子,只要得住就使勁欺負,就那麼纏了很久,長時間的,短時間的,激烈的,蜻蜓點水的,像有使不完的力一樣,一直不肯消停,但好在他還算聽話,沒有的服,他的上再燥熱,也終究放一馬。
折騰到最后,真正睡著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三點。
定的是六點的鬧鐘。
只睡三個小時,導致吃早飯的時候,整個人反應遲鈍,不就發呆出神,這個時候就覺得靳譯肯厲害了,洗漱的時候,他已經找好了這片區域最好吃的早餐店,穿服的時候,他已經在沙發上抬著二郎打游戲,他很在意那游戲被他親媽破了記錄,等梳妝那會兒一直在打,最后還是因為被催著出門而自放棄。
這一片的當地特是一種牛,他選的早餐店也是一家店,這家牛分兩種口味,經典的和香辣的,龍七兩種都想嘗,靳譯肯就給點了兩碗。
上來后,用筷子各卷一,被其中一份辣得皺眉頭。
“喜歡哪碗?”
用紙巾筷頭,用眼神指一下經典口味那碗。
他就把那碗移到跟前,把辣的那碗挪自個兒跟前,著筷子笑:“跟你說你吃不了重口的。”
“你不是也吃不了辣,別吃了靳譯肯,再點一碗。”
“在外頭呆久就什麼都吃了。”
這話聽得還怪心酸,看他一眼,他低頭夾。
但下一秒就被吃到牛的滿足給蓋過,胃口很好,平時只肯吃一個牛角面包的,這一回把一整碗連著湯都喝完了,小鎮的早晨比大城市醒得更晚一些,空氣里殘留著隔夜雨的充沛氣,穿著初中校服的孩子獨自吃,斜背著小包的上班生一邊往湯里加醋,一邊看桌上的手機,對面的男友在打游戲,還有一桌趕早務工的中年男子,吸湯聲呲溜呲溜地響,戴著很低的帽子,說這是最近吃過最好吃的一頓。
Advertisement
“我回去給你做。”靳譯肯說。
“你還會做這了?”
“我現在什麼都會做。”
“那我還是什麼都不會。”
“不嫌棄你。”
桌下的腳往他那兒一踹,他了一下,椅腳地面,改口:“養你。”
“覺得好吃不是的原因,”說,“是因為你陪我吃的。”
這句話聽著就舒服了,靳譯肯抬額看一眼,就好像從來沒聽過一句來得這麼容易的“表白”,有點心疼,又有點得意,桌底下的剛好著他的小,穿的是九分的牛仔,出的腳踝那塊兒涼,他正慢悠悠吃涼菜,右手夾筷子,閑著的左手則到桌底,一言不發地把的腳踝撈起來,握在手心。
捂暖了。
再晚一些的時候,店里的食客漸漸從當地的小鎮居民轉變旅客,雖然是淡季,年輕還是多的,這家門面店沒有包廂,好在和靳譯肯這桌在二樓回廊,一樓沒坐滿,抬頭往上找位兒的人之又,環境安全的。
一碗不夠靳譯肯吃的,他又點了些蒸糕。
龍七用筷子搗著涼菜盤,七點半了,說好八點集合拍攝,群里到現在仍舊一點兒靜沒有,像個個都沒醒,說:“待會兒送我回民宿后你就回酒店,外頭人多眼雜的,你這戴罪之,就在這種遍地都是wifi的地方晃悠,知不知道。”
他沒應,吃蒸糕,一副“你看爺聽不聽你”的德行,龍七的腳踝往后一,他握,沒讓得逞:“吃完再說。”
“你怎麼一副司柏林的樣子?”
“什麼司柏林的樣子?”
“死鬼。”
他笑,就在這時候,一樓有響,又進來了一撥食客,人聲喧雜,嗓音年輕,龍七一下子就聽出其中伍依珊的大嗓門,側頭,正好聽見伍依珊的一句:“哎就這兒!”
Advertisement
“我查的就這家最好吃,評分最高!”
??
回看微信群,仍舊沒有任何消息,但這堆人就跟約好了似的,包括傅宇敖,陸陸續續,一個不地進這家店,合拼了一個大桌后就開始點單,其中傅宇敖還是跟葛因濘保持了距離,兩人離得最遠,半句不搭腔。
店老板養了只貓,在靳譯肯腳邊轉悠求食,他正閑著沒事逗著,龍七則一言不發地看著樓下,他逗完,看,而后順著的視線看下去。
“你同學?”
沒應,剛好其中一個負責劇本的生點完單,說:“哎我把寫好的文檔發群里,你們先討論一下領一下角。”
那一桌的手機陸陸續續發出群消息提示聲。
二樓,的手機一片安靜。
懂了。
假設說昨天他們玩牌的時候約好了這個點集出來吃早飯,那能理解,偏偏現在擺明就是撇開另建了一個群,事無巨細總歸先在那個群討論商量好,再把一個結果拋向,不管有何反應,得到的永遠不是第一反應的回復,這麼一層蓋一層的,無聊,也難看,夾一筷子涼菜,低頭吃,然后再倒一杯熱茶:“等們吃完再走吧,免得看見你。”
靳譯肯看,臉頰徐徐地著。
樓下,都上了,傅宇敖對老板說:“經典牛和蒸糕再加單一份,打包。”
葛因濘沒說話。
那林幫腔:“等送上去湯都收干了傅宇敖。”
“那你們讓一個人在半山腰吃什麼?”
“關我們什麼事,民宿不是有早餐嗎。”
“晚點再說晚點再說,我們先討論劇本吧。”伍依珊挪話題。
茶沒了,老板拎了壺剛煮好的熱茶上二樓,靳譯肯倒茶,往的杯里也加一點,茶水很香,熱騰騰。
Advertisement
……
樓下,他們閑聊著吃上了。
葛因濘沒筷,一直看著手機里的文檔,等其他幾人領角領得差不多,把一角讓給的時候,開口:“那個角給龍七吧。”
“為什麼給?”那林有點反應。
“有沒有不需要和男一對戲的角,我演那就行。”
男一是傅宇敖。
“那就是三了。”寫劇本的生說。
“就三吧。”接著說,“最后一場,男主升華,我覺得了點東西。”
“有嗎?那需要加點什麼?”
葛因濘看了看那林,再看傅宇敖:“加場吻戲吧。”
傅宇敖抬眼。
那林也看向葛因濘,伍依珊也是,他們都看向葛因濘,二樓,龍七呵笑一聲。
“額……這個要問一下龍七同不同意。”
“好啊,去問。”
“不用問,”傅宇敖打斷,“沒必要。”
“我覺得有必要。”葛因濘接得很快。
“你想干嘛?”
傅宇敖這一記有點無奈,低著聲,斜著額,直視葛因濘。
“我很認真地在提我的意見,難道你以為我帶著私人?”葛因濘從容地回,“別稚了傅宇敖。”
“我不覺得一場吻戲那麼有必要。”
“那你自己看啊,結尾很突兀。”
“那就加別的容,或者改結尾。”
“你以為這真的是在玩,你以后進組拍戲也這樣?不喜歡就讓編劇改戲,讓導演陪著你重拍?你書白念了?”
話語很嚴厲,傅宇敖聽著,無可奈何地搖頭,往椅背上靠,眼神像看著一個全然陌生的人,葛因濘話鋒一轉:“還是你自己帶著私人,怕龍七萬一真的有hiv,被傳染?”
樓上,靳譯肯放了筷,咔噠一聲響,臉有一點沉,但好歹總算吃飽的樣子,龍七的腳往他那邊兒靠,沒讓他。
“你要是這樣事事針對,何必同意進組?”
傅宇敖問。
那林不滿:“等一下,因濘事事針對?”
“好了那林你說兩句……”伍依珊話。
“不是,這話我不同意啊,因濘從頭至尾都在講專業好嗎,是你另有心思吧傅宇敖,因濘都沒有追究昨晚上你跟龍七干嘛了。”
伍依珊耳朵尖,一愣:“昨晚上?什麼事?”
傅宇敖同樣也問:“我跟干嘛了?”
全桌人都不知不覺間停筷,專注看這一場戲,葛因濘這會兒不說話,那林了主要話語人,幫閨嗤笑一聲:“別裝蒜了傅宇敖,龍七昨晚上本就不在房里,我五點起過一回,房間門開著,阿姨在清掃,你倒是說說早上五點的時候你在干嘛?”
“我在晨跑,你說不在房里?”
“也就是說你也不在房里,你和龍七都不在房里。”那林總結,輕笑,“那麼巧的啊。”
樓上,攔不住靳譯肯了,他打一響指,前臺的老板聽到,上來結賬,靳譯肯的下往底下一指:“那桌一起結了。”
“你要干嘛?”龍七問。
他沒說話,嚼著顆用來解膩的薄荷糖,結完賬,拿了小票收據,額頭一斜,一副“爺此刻就想走人”的樣兒,被牽著手腕起。
“你覺得我跟在一起?”傅宇敖問。
龍七跟著他下樓梯。
“你們來的路上就在車里你儂我儂了啊,其實傅宇敖,好歹也等到活結束,你倆自個兒開房開房去,沒必要非趕這趟,有點難看了啊。”
“我真他媽在晨跑!”
“也別假惺惺地說不拍吻戲,你倆什麼程度了自己清楚。”
“沒……”
啪一聲。
穿過走廊,經過這一桌的時候,靳譯肯就那麼目不斜視地將收據小票按在這一桌面上,響而利落,毫不客氣地打斷傅宇敖費力的否認,背靠走廊的伍依珊和一男生都猝不及防地抖了一下肩膀,回頭,那林和葛因濘也抬頭,整一桌都抬頭,靳譯肯繼續慢悠悠地走,邊走邊看了這桌一眼,話也懶得說一句,反正見上了,也記著了,一個個的帳他都結上了,日子那麼長,悠著慢慢過,那眼里暗沉沉都是這麼一個意思。
龍七著外兜,被牽在側。
那一桌還沒人反應過來,前一刻的劍拔弩張瞬間偃旗息鼓,仿佛通通陷在背人說小話被抓包的剎那坐立不安中,雀無聲,葛因濘的心口起伏,而那林盯著靳譯肯的背影看,傅宇敖起了,老板說打包的牛和蒸糕好了,他盯著龍七走的門口,半晌沒回話。
……
猜你喜歡
-
完結1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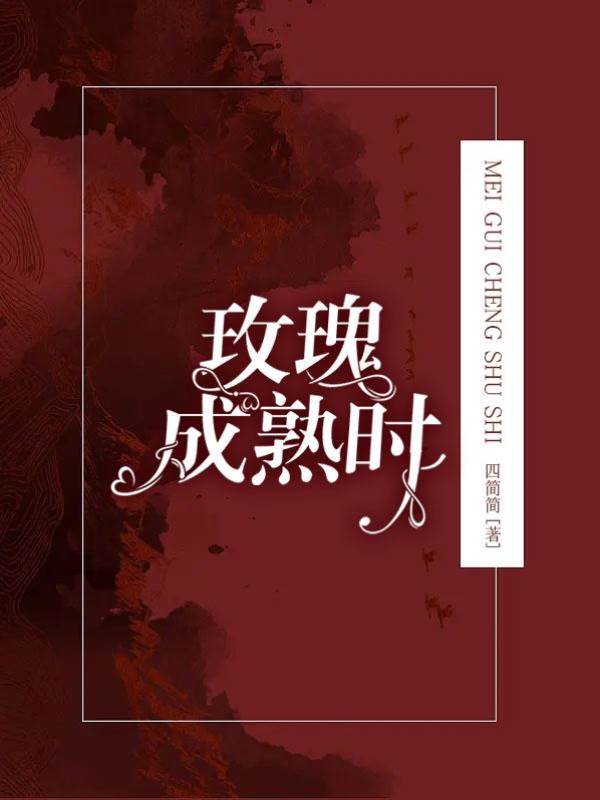
玫瑰成熟時
蘇落胭是京北出了名的美人,祖籍南江,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有著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嫵媚。傅家是京北世家,無人不知傅城深是傅家下一任家主,行事狠辣,不擇手段,還不近女色,所有人都好奇會被什麼樣的女人拿下。蘇落胭出國留學多年,狐朋狗友在酒吧為她舉辦接風宴,有不長眼的端著酒杯上前。“不喝就是不給我麵子?我一句話就能讓你消失在京北。”酒吧中有人認了出來,“那個是蘇落胭呀。”有人說道:“是那個被傅城深捧在手心裏小公主,蘇落胭。”所有人都知道傅城深對蘇落胭,比自己的親妹妹還寵,從未覺得兩個人能走到一起。傅老爺子拿著京北的青年才俊的照片給蘇落胭介紹,“胭胭,你看一下有哪些合適的,我讓他們到家裏麵來跟你吃飯。”殊不知上樓後,蘇落胭被人摁在門口,挑著她的下巴,“準備跟哪家的青年才俊吃飯呢?”蘇落胭剛想解釋,就被吻住了。雙潔雙初戀,年齡差6歲
23.5萬字8 17045 -
完結125 章

甘愿沉淪
陸時謙是北尋赫赫有名的律師,工作嚴謹,爲人正派,法庭上屢屢勝訴,人稱金牌陸帥。分明長了一張頂流明星臉,卻偏偏清心寡慾,不近女色。 然而這樣的人,不聲不響地跟個花瓶結婚了。 朋友問爲何?陸時謙泰然自若地合上案本,語氣平淡:“緣分。” . 溫絮聽到這句話,嘴角抽抽,只有她清楚,兩人的婚姻是被迫綁在一起的。 她無所謂,有錢有顏,還有個工作狂不愛回家的老公,日子不要太爽。 結婚前,她是這麼想的。 然而結婚後....... 煙霧繚繞的的浴室裏,燈光昏黃曖昧。 清冷矜貴的男人,將溫絮強勢抵在盥洗臺前,低聲輕哄:“還在生氣?” 溫絮羞赧地抓住男人領口,蔥白如玉的手指在他胸膛上輕點:“……自己破的戒,可別想賴我頭上。” 陸時謙輕笑,低頭一遍遍親吻,她眼角那顆讓他着迷的淚痣:“嗯,怪我。”
18.4萬字8 21034 -
完結96 章

你敢給我算一個試試
孟玳玳凡事得過且過,喜歡說算了。 小時候,被人搶了玩具,發小要找人去算賬,她說算了。 長大後,被閨蜜搶了男朋友,發小扛着棍子要去揍人,她說算了。 直到有一天,她不小心醉酒,犯下了不該犯的錯。 第二天醒來,面對一牀的凌亂,她落荒而逃,發小窮追不捨。 堵到一小巷口,兩人對峙。 孟玳玳期期艾艾,“就……算了吧,我不用你負責……” 發小氣急敗壞,“孟玳玳,你敢給我算一個試試!”
15.4萬字8.18 57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