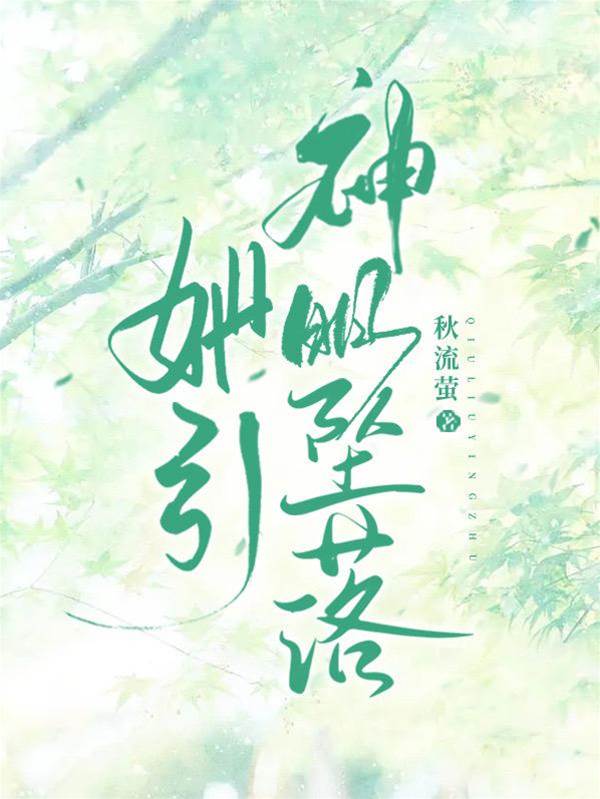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晚風漪》 第26章
方才在碧海方舟,紀悠之沒有追上顧瀾, 眼睜睜看著開車帶著Meggie揚長而去, 把他一個人扔在了江澤予家門口。
再上樓看那兩人卿卿我我、互訴衷腸更是要命,紀大爺只好憋屈地徒步二十幾分鐘才走到小區門口打車。
然而禍不單行, 他剛到辦公室便接到了來自顧瀾的好幾個譴責電話。
顧瀾為閨鳴不平,更惱怒他辦事兒不靠譜, 倆人拌了幾句之后塵埃落定——之后幾天進家門是不可能了, 辦公室的沙發他紀大爺得被迫包場一周。
這懲罰實在是太過慘烈,以紀悠之睚 眥必報的格,怎麼可能罷休?他恨恨地想, 這虧可不能讓他自個兒一個人吃了, 得他媽找個人跟他一起苦。
他思來想去,打電話問莊孰要了謝昳的手機號碼,撒氣般發了兩條短信。
【是謝昳嗎?我是紀悠之, 好久不見, 哪天要不要出來聊一聊?】
【聊一聊關于江澤予的眼睛,我想他大概沒有告訴過你, 他為什麼了傷。】
謝昳收到這兩條短信的時候,著實怔愣了許久。
在的印象里紀悠之一直是個吵鬧又不正經的人,和莊孰兩個人就是他們一眾發小圈子里的一對活寶, 都是科打諢、油舌的紈绔子弟。所以在收到紀爺規規矩矩的兩句完全不帶臟話、語氣相當客氣的短信的時候, 便是還沒有看完全不容,也察覺出了事的嚴重程度來。
嚴重到手機從微抖的手指里溜出去,掉在司機座椅下面, 費了好大勁才夠到。
手頭沒有紙巾,把蹭臟了的手機屏幕用邊胡了,看了一眼時間,正好下午一點鐘,離和周導約好的試鏡還有一個小時——哪怕再是迫切地想知道事的全部原委,現下也來不及了。
Advertisement
沒有太多考慮的時間,手機忽然鈴聲炸耳。
謝昳接起來,對面是著國混上海口音蹩腳漢語的林景鑠。
“喂,Sunny嗎?周子揚把一會兒的試鏡取消了,定了今晚的飛機飛溫哥華。這傻拍的廣告是還可以,但本人就是個瘋子。他之前定了廣告的主題是星河和極,不知道聽誰預測了今年黃刀鎮的極就這兩周最佳,非要劇組有加簽的馬上飛過去,Sunny,你有加簽吧?”
七八糟的事接踵而至,謝昳按了按太,穩了下心神,語氣很有些疲憊:“嗯,有是有,不過……什麼時候出發?”
林景鑠那邊正在焦頭爛額地打包行李,聞言靠腦袋和肩膀夾住手機:“晚上八點的飛機,我也過去。他周家爺發瘋我們也只能跟著兜底。你要是去的話,趕回家收拾行李,我讓書給你訂票。”
謝昳聽到他開頭的時間,算了一下,離現在還有七個小時。恍惚間沒有注意到林景鑠的后半句,只點頭道:“好,到時候機場見。”
掛完電話,想了一會兒,給剛剛那個陌生的號碼回了條短信,帶了些許與風格不符的示弱。
【紀悠之?你現在有空嗎,我晚上八點的飛機去加拿大出差,要是有空,我請你喝酒。】
那邊消息回得很快,好像專門守在手機旁邊等的回復,但語氣實在算不上友善:【喝酒就算了,我沒那閑。擇優總部十七樓,我的辦公室,不見不散。】
謝昳鎖上手機,力般靠在汽車后座的靠墊上,好半天才想起來讓司機掉頭去擇優。
車子行駛的時候,的心臟跳得越來越快,約約地覺得,江澤予的傷或許和有關系,或者說,和當年的離開有關系。不然他沒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瞞,不然紀悠之也不會給發這樣的短信。
Advertisement
難道當年,真的是做錯了嗎?
可是如果不那麼做,周子駿栽贓給他的無端指控就不能洗清。他一輩子都會被人看不起,永遠都得背著見不得的案底,艱辛又毫無希地活在黑暗里。
保不上研,拿不到大企業的offer,進不了制,甚至就連創業他都不可能拿到銀行的貸款。
似乎最好的結局就是不管周家的事,不幫他翻案,逃離謝家后執意和他在一起,兩個人做一對平凡又貧窮的夫妻。
可是那樣的話,他真的會甘心嗎?怎麼可能呢?
他當年可是北京城的理科狀元;大學四年,他除了陪就是泡在圖書館;他夜以繼日挑燈夜讀,四年里修了自化、金融的雙學位。
這樣勤又上進的年人,怎麼可能甘愿平凡呢?
在謝昳的價值觀里,和自由、財富與尊嚴比起來,實在是飄渺又可有可無的東西。
不說別的,的媽媽當年便飛蛾撲火般投奔所謂的,東窗事發后,出軌的對象一走了之,而和謝昳則被趕出謝家,過了幾年相當苦困的生活。
就連娘家為了臉面對置之不理,于是這位出生名門的上海小姐不得不為了生計在北京城郊外擺了個早點店,最后去世也是因為心有積郁再加上勞累過度。
死的時候告訴過謝昳,不能當飯吃,連個屁都不是。
謝昳很小的時候就銘記于心。
多年后,自以為做出理智選擇的在北京城繁華的市中心的車水馬龍里頭疼裂、幾窒息。
百思不得其解,恰好聽到的車司機吐槽了句:“今兒個天氣真是怪,您看啊,咱背后是太,前方又是大片兒的烏云,特像我前兩天擱電影院看的災難片。”
Advertisement
謝昳恍恍惚惚地抬起頭。
車窗外晴朗依舊,的小臂被暖橙照耀,然而車前方不遠的天空烏云蓋頂,狂風大作,梧桐葉子被風卷起來幾米高,還真像是電影《2012》里渲染得極其真的世界末日。
忽然想起當初在S大旁邊的公寓里,和江澤予一起看了這部電影。
電影里,末日來臨的特效迫人,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們忙著哭泣、逃生、告別,但所有的一切在驟然來臨的災難面前顯得那樣脆弱。無法阻止的地震、海嘯、火山發,在一切人類賴以生存的質基礎崩潰之后,這世界上像一座巨大的墳墓,所有的人類文明被毀滅,人類的意志也被擊垮。
謝昳還記得那個時候,寬大的沙發上蓋著條灰毯裹住兩個人,靠在他上,咽下一顆他喂的小番茄,被酸得牙疼又困倦非常:“嘖,末日,如果地球都毀滅這樣,那世界上真是什麼都不剩了。”
彼時的年低下頭,輕輕的發,很久之后在額上親吻了一下:“不啊,還剩很多東西。”
謝昳實在是困極,丟了句含含糊糊的“剩了什麼啊”,便沉沉睡去。
沒有聽到答案。
幾年后依舊是北京城,朝區的出租車里,謝昳看著車前翻涌的烏云和云里頭偶爾亮起的閃電,雖然還是不知道他當時的回答,但腦海里忽然冒出了一個與從前截然不同的想法。
如果,如果真的末日來臨,房子毀了、公路不再、世界上的一切都消失殆盡。什麼喜馬拉雅鱷魚皮,什麼布拉迪跑車,什麼昂貴的香檳晚宴,什麼尊嚴什麼自由什麼貧賤或是富貴,統統在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下全都了齏灰飛煙滅。
Advertisement
那還是會著他的吧。
謝昳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狠狠嚇了一跳,心臟錯跳間,額角出了滿頭的冷汗。
這五年來的每一天,都好像在演一部沒有觀眾的諜戰片,孤獨、想念、害怕像是活埋過程的一抔抔泥土,下一秒就要把垮。自己都想不明白,是何等信念讓獨自一人支撐到現在的呢?
如果那信念崩塌,那又該怎麼辦呢?
謝昳腦袋突突得疼,只覺得太的管快要崩開,幸好這時候的車司機好心提醒:“小姐,車子到了,麻煩給個好評?”
市中心,寫字樓十七層,秋風一直從香山吹到這里,好像把紅葉的紅也帶來半分。富麗堂皇的CFO辦公室里擺著一張躺五個人都綽綽有余的浮夸沙發,紀大爺翹著二郎一臉酸爽地等著人來。
要問頭鐵的紀悠之怕不怕?
那肯定還是有點怕的,他絕對清楚,這件事兒被江澤予捂得死死的,五年來不再提起一個字,要是被他知道他告訴了謝昳,那他這小命難保。
可痛失城池的紀爺又恨恨地想,跟媳婦兒的被窩比起來,小命算什麼?憑什麼他得睡“冰冷狹窄”的沙發,而謝大小姐這個始作俑者就能高枕無憂地飛加拿大?
何況,這人五年前一個屁都不放一走了之,他看不爽很久了好吧?
幾分鐘后,辦公室門被敲響,書小劉恭敬道:“紀總,有位謝小姐說和您有預約,我把人帶上來了。”
紀悠之沒有想到人來得這麼快,立馬正襟危坐,提了提氣勢這才“嗯”了一聲,讓人進來。
窗外灑進來,謝昳跟著劉書走進辦公室,摘了口罩和墨鏡,銀灰長發在頭頂綁了個高馬尾,鬢角邊茸茸的碎發蜷曲。掌大的臉未施黛,額角青筋畢,看著神很差。
大概是來得很匆忙,微微息,口起伏劇烈著,一雙平底鞋白的鞋幫發灰,黑的邊竟然也有些醒目的污漬。
很狼狽的模樣。
五年不見,紀悠之忽然覺得眼前這個人和他記憶里的那個謝昳,似乎有些不同。當年他們這幾個人里,最讓人看不的就是謝大小姐,自信、驕傲、目中無人,每次出門必須打扮致。
從妝容、首飾、服裝到香水,每每都是最講究的人,哪里有過像今天這樣的狼狽模樣?
紀爺一向是吃不吃的主,到邊的找碴立馬下去,他咳了兩聲,有點心虛地不敢看:“謝昳,你來了?”
“紀悠之,好久不見。”謝昳走到沙發近前,短暫和他寒暄,“抱歉,今兒時間迫,我一會兒還得去機場,咱們就切主題吧。江澤予五年前的傷,到底是怎麼回事?”
紀悠之聽到這里,迫自己把方才下去的心腸起來,板著張臉走到奢華酒柜旁邊一個小的碼箱里,輸了幾個數字后從里面翻出來一個U盤。
“跟我來。”
他的辦公室比起隔壁江澤予的那一間,實在豪華得不像樣,書桌后那扇門推進去,竟然是個完全閉的私人影院。
紀悠之把幕布降下來,點開U盤里的視頻文件,頓了會兒又有一點不忍心,大發慈悲道:“你要是很急,也可以從加拿大回來再看。”
謝昳有些疲憊地坐在沙發上,搖搖頭,本來沒有想說話。
但想起來這幾年,紀悠之對江澤予真的算夠意思。于是沖他禮貌地點了點頭,帶著謝意道:“不用了,你今天能讓我過來告訴我事的原委,我已經十分激。”
紀悠之便不再多說,走出去的時候還給帶上門。
房間里唯一一點線隨著門關嚴實消失殆盡了,那投影儀開始運作。
視頻的前幾秒,白幕布上還沒有什麼容,投影儀運轉的聲音“嗚嗚”作響,詭異冷像是臨刑前來自鬼門關的風聲。
謝昳的心臟“怦怦”跳起來,死死盯著那屏幕,手指頭抓了沙發上隨意搭著的毯。
十七秒的沉默之后,屏幕一閃有了畫面。那畫質不算清晰,背景是個審訊室模樣的房間,一胖一瘦兩個戴了手銬的黑人坐在桌子對面,沒有什麼表。
屏幕左下角的細小英文標注顯示,這是單獨審訊之后的第二審訊。
猜你喜歡
-
完結428 章

年代甜炸了:寡婦她男人回來啦
(全文架空)【空間+年代+甜爽】一覺醒來,白玖穿越到了爺爺奶奶小時候講的那個缺衣少食,物資稀缺的年代。好在白玖在穿越前得了一個空間,她雖不知空間為何而來,但得到空間的第一時間她就開始囤貨,手有余糧心不慌嘛,空間里她可沒少往里囤放東西。穿越后…
97.7萬字8 285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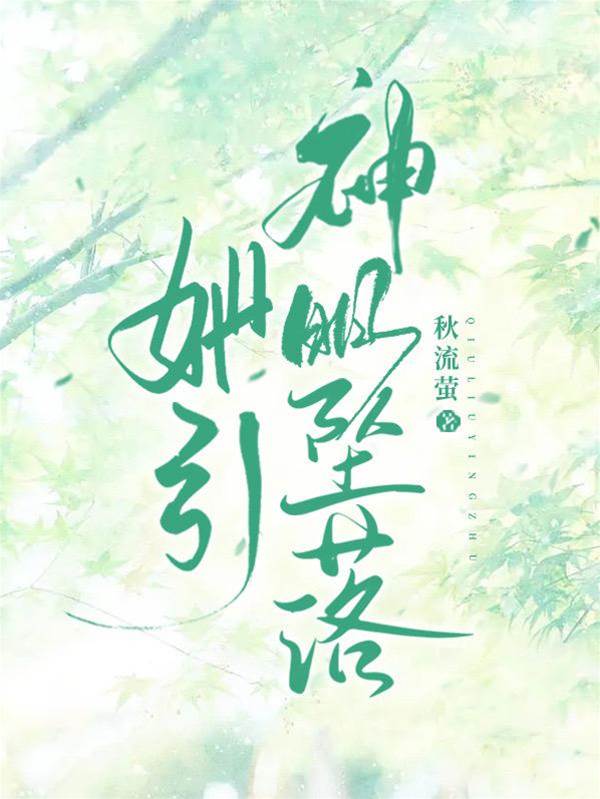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221 章

春意入我懷
【大學校園 男二上位 浪子回頭 男追女 單向救贖】【痞壞浪拽vs倔強清冷】虞惜從中學開始就是遠近聞名的冰美人,向來孤僻,沒什麼朋友,對前仆後繼的追求者更是不屑一顧。直到大學,她碰上個硬茬,一個花名在外的紈絝公子哥———靳灼霄。靳灼霄這人,家世好、長得帥,唯二的缺點就是性格極壞和浪得沒邊。兩人在一起如同冰火,勢必馴服一方。*“寶貝,按照現在的遊戲規則,進來的人可得先親我一口。”男人眉眼桀驁,聲音跟長相一樣,帶著濃重的荷爾蒙和侵略性,讓人無法忽視。初見,虞惜便知道靳灼霄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魅力十足又危險,像個玩弄人心的惡魔,躲不過隻能妥協。*兩廂情願的曖昧無關愛情,隻有各取所需,可關係如履薄冰,一觸就碎。放假後,虞惜單方麵斷絕所有聯係,消失的無影無蹤。再次碰麵,靳灼霄把她抵在牆邊,低沉的嗓音像在醞釀一場風暴:“看見我就跑?”*虞惜是凜冬的獨行客,她在等有人破寒而來,對她說:“虞惜,春天來了。”
39.6萬字8.18 62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