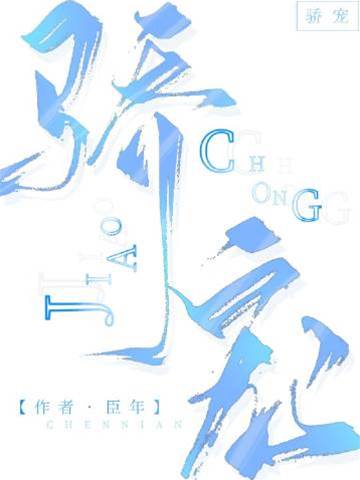《上心》 第57章
57
十九歲的沈恕,蒼白而瘦削。扶著樓梯低頭看人的模樣,高傲地讓人不敢靠近。
這樣的沈恕,一開始郁松年僅僅只是覺得好看。
對于藝生來說,見到繆斯能夠激發無限的靈。郁松年放學后經常去畫室學習,那段時間里,他總是覺得大腦中有不形的畫面,繪于紙上,只是些漫無目的的線條。
那天他戴著耳機,趴在窗戶里聽歌。已經下課了,傍晚時分。冥冥之中仿佛早有預兆,他在那時抬了眼。
目穿過了距離與樹蔭,落在了斜上方的窗口。
曾經見過的漂亮又傲慢的學長,坐在窗后低垂著腦袋,不知看到了什麼,他笑了。
的弧度只有些許,卻和了所有。
郁松年仰著頭,腦海里一團麻的線條,終于在這時形了完整的廓。
耳機里的男音,恰好唱著一句:全部世事亦淪落陪襯,眼中只得邊這個人。
手里的筆在發呆中落了下去,郁松年本能地去抓,卻落了個空。
就像被落筆所驚嚇,又像是因為現在的心。他扶著窗口,愣愣地著樓下,又慢慢抬起頭。
窗后的沈恕像是覺到了什麼,轉過頭來。
郁松年背對著拉上窗簾的窗戶,按住了口,那里咚咚地悶響著,就像現在。
沈恕乖巧地背對著他,窩在他懷里。背上的窗戶與鹿角,被水潤得愈發鮮亮。
“無論怎麼想,”郁松年的掌心按上去,將那整片帶有紋的皮了:“都實在猜不到,你上的鹿是我。”
分明是陳述句,也說的是事實,可能是因為才結束那過于激烈的事,沈恕莫名覺得這句話曖昧又過火。
他忍不住悄悄往前挪,想要離“鹿角”更遠些,再遠點才好。
Advertisement
郁松年笑著追了上去,將人按在浴缸邊親了好一會,才放過了他。
洗過澡,沈恕穿上浴袍,腳步遲緩,堅強地回到了主臥的床邊。雖然如郁松年所說,這里已經被清理過了。
但是只要一看那張床,想到剛才這里究竟發生了什麼,沈恕還是覺得不住。
他轉過,繼續艱難地往外挪。從浴室里出來的郁松年,正好捕捉到了準備逃出主臥的沈恕:“你去哪?”
沈恕遲疑地道:“去客房。”
他本來以為郁松年會笑他,又或者勸他留在這里。但郁松年卻只是道:“你是不是忘了帶上一件東西?”
“什麼?”沈恕不認床,也沒有什麼一定要帶上才能睡覺的品。
郁松年走過來,將他攬腰抱起。并不是公主抱,而是像抱小孩一樣,托著他往外走:“你的丈夫。”郁松年又道:“目前他還沒有獨守空房的打算。”
沈恕啞然半晌,繼而雙臂摟住了郁松年,將臉埋到對方鬢角:“沒打算不帶你。”
如果郁松年不跟著來,他也會半夜悄悄回來,躺到郁松年邊。
明明應該困了,夜很深,疲憊,神卻仍然活躍著。可能是一整天得知的信息太多,又有許多想問的。
沈恕裹著被子,他被郁松年用薄被裹了春卷,摟在了懷里。
別墅里裝了地暖,常年保持恒溫。但這幾日明顯降溫,質燥熱的郁松年不覺得,沈恕卻覺冷了。
大概是察覺到這一點,郁松年給他裹得嚴嚴實實,自己腰上只蓋了一方被角。
“你睡了嗎?”沈恕輕聲地說,他不能確定閉著雙眼許久的郁松年醒沒醒著,所以試探地喊了一聲。
郁松年仍然閉著眼,卻還是回道:“沒有。”
Advertisement
“你當年……平安夜那晚是來找過我嗎?”沈恕低聲道。
他也是通過這一點,才確認了郁松年求的人是他。那時郁松年十九歲,母親剛去世,他獨自一人去了x國。他說想為一個人留下來,于是有了那一年的平安夜,那條紅的圍巾與那被拿走的書。
哪怕知道早知道這三個字,是最無能為力的,沈恕卻忍不住去想,如果那天晚上,他沒有與學長牽手,那麼一切會不會都與現在不同。
郁松年睫了,緩緩睜開眼:“你說什麼?”
“你出國前,是不是來找過我。”沈恕說了一個更準確的時間,在哪一年的平安夜,他宿舍樓下,讓阿姨轉的白紙袋。
他能夠想到,郁松年是獨自一人回到這座城市,滿懷希,帶著向神祈禱的勇氣,來到了他的學校。
又無法想象,郁松年是怎樣的心看見他和另一個人牽手。
郁松年安靜了一會,才坐起來,打開了床頭邊的小燈。他低頭看著床上的沈恕,似乎現在才發現,這個人知道得遠比他想象中要多。
“你為什麼會……”郁松年不明白沈恕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當初他并未留下任何書信。
以他對沈恕的了解,這人不會收不明來源的禮。
沈恕在被子里艱難地了,郁松年把他裹得太了:“因為聽舍友和阿姨的描述,覺那個人像你,所以留下來了。”
“今天回去找了一下,發現上面有lev。”
不知道是不是被子裹得太熱,沈恕臉上有些紅了:“你給自己起lev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嗎?他只是約有猜到,通過那副名為《上心》的畫。
所以他猜測,他是郁松年的“心”,又不能完全肯定,也許只是他想得太多,自作多。
Advertisement
郁松年卻坦然地說:“確實是因為你。”
沈恕愣了半晌,將下往被子里埋了埋,好像這樣就能把臉藏進去:“哦。”
郁松年沒想到會得來這麼一聲,他還以為沈恕應該會有更多其他的想:“哦是什麼意思?”
沈恕想了想,認真答道:“就是我知道了的意思。”
郁松年又好氣又好笑,他重新躺下來,翻了個,暫時不想抱沈恕了。
他不抱沈恕,沈恕卻挪了過來,住了他:“我的肚子好像還有點疼,能不能像剛才在浴室里那樣給我一。”
想到造沈恕肚子疼的罪魁禍首是自己,郁松年還是轉了回去,掌心住了沈恕,按著那薄薄的肚皮,好像因為前段時間消瘦而流失了許多,難怪容易被弄得肚子痛。
郁松年這麼想著,卻完全沒想過,沈恕之所以會肚子痛,完全是他的問題更“大”。
給沈恕著肚子,懷里的人不知好歹,還要問他:“你是不是撞到我和學長牽手了,才沒敢自己把禮給我?”
有些事其實就該當它過去了,不該提起。郁松年也沒想要提,卻不料竟是沈恕主提起。
“你明天要上班吧,該睡了。”郁松年試圖轉移話題。
沈恕卻很固執,追問道:“是嗎?”
郁松年無奈地嘆了口氣:“嗯,是。”
沈恕沉默了一會,呼吸聲變得有些重,郁松年發覺不對,低下頭去時,沈恕的表看起來雖然沒有哭,但也沒好到哪里去。
郁松年趕手把人抱住,輕輕拍著他的背心:“別想了,快睡吧。”主要是過去的事,想了也沒用,只是自尋苦惱。
“對不起。”沈恕低聲道,為了當初的自己,也為了那時的郁松年。
Advertisement
“這有什麼好抱歉的。”郁松年的聲音很啞,在濃重的夜中,沉沉地落在了沈恕的耳邊:“當年本來就是我來遲了,所以你有了別的選擇,這很正常。”
沈恕明白郁松年的意思,卻沒辦法釋然。
心臟甚至因此而到無比苦,如果可以,他愿他不是郁松年的初,那麼那些傷害就不會發生。
如同猜到了他在想什麼,郁松年抬手掐他的臉頰:“知不知道當著現任的面提前任是大忌,乖乖睡覺!”
沈恕沒有如郁松年所愿,聽話閉眼,而是輕聲地說:“我當初說討厭你的原因,不是因為我真的討厭你。”
郁松年好像真的困了,聲音也低了很多,聽起來極為敷衍地嗯了聲。
沈恕有些郁悶,因為就他一個人在激,想要弄清楚當年所有事,想要表白很多次,心起伏,緒涌,恨不得抓著郁松年把當年的一切都說個一清二楚。
但是郁松年一直哄他睡覺,好像本不在乎當年的事。就在郁松年即將進睡眠時,沈恕的聲音幽幽響起。
“我以為你和我弟弟沈元談,所以我說討厭你。”
郁松年猛地睜開眼,困意消散,是被嚇的:“什麼?!”
沈恕翻了個,背對著郁松年:“時間不早了,該睡了。”
郁松年睡不著了,他按著沈恕的肩膀,企圖把人翻過來:“你說我和誰談?沈元?!這是誰說的?!誰他媽造謠!”他甚至說了臟話。
沈恕學著郁松年的語氣,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沒事,都過去了。現在我知道了,你們之間什麼也沒有。”
“我跟他本來就什麼都沒有!”郁松年急了,他坐起:“不是,你為什麼會覺得我跟沈元談過?我們當初也沒有做什麼令人誤會的事啊?”
郁松年錯愕許久,忽地明白過來:“所以你之前一直以為我喜歡你弟?”
沈恕打了個哈欠,面無表地說:“你明天還要去學校,早點睡吧。”
最后四個字,他說得一字一頓,刻意極了。
--------------------
全部世事亦淪落陪襯,眼中只得邊這個人。這句歌詞來源于《靈魂相認》by張敬軒
猜你喜歡
-
完結1387 章

重生九九:嬌妻又甜又撩
重生前,顧悅歡又黑又胖,腦子還不好使。 重生后,顧悅歡一夜之間回到了80年代,還好,一切都可以重來! 她雙商在線,收拾極品家人,虐渣打臉不手軟! 花式逆襲,廣開工廠店鋪,勵志成為白富美。 結果一不小心撩倒各路男神,閃瞎眾人的眼! 唯獨面對上輩子被她辜負的男人,小心翼翼。 計劃了寵夫36招,剛要嘗試第一招撒嬌打滾,誰知……霍清越主動躺床,「媳婦兒,我躺好了,你可以寵我了」 顧悅歡:「……」 這人,怎麼就不按劇情發展呢?
133.5萬字8 32773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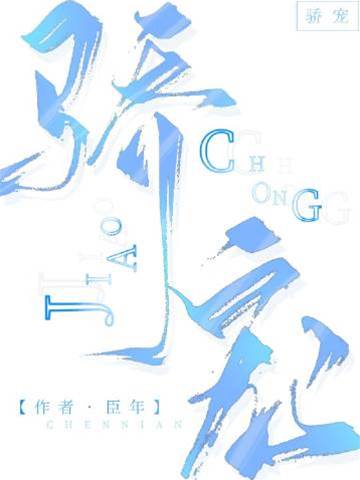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3856 -
完結968 章

霍先生乖乖寵我
溫蔓一直知道,霍紹霆沒那麼愛她,她有求于他,他貪圖她年輕身材好。當他的白月光歸來,他漸漸不再回家,溫蔓守著空房,度過無數個沒有他的夜晚,后來,她等到一張支票和他的一聲再見。……再次重逢,她身邊有了旁人,他紅著眼睛說:“溫蔓,明明是我先跟你好的。”溫蔓笑顏淡淡:“霍律師,先說分開的也是你!如果你想跟我約會,可能要排隊……”次日,她收到千億存款附加一枚鉆戒,霍律師單膝下跪:“溫小姐,我想插隊。”
217.8萬字8.46 885245 -
完結155 章

重生淪陷:她甜誘撩人
重生前,時星瑤暗戀周沉六年,誤以為周沉不愛她,隻把她當成白月光的替身。重生後,時星瑤才知道,周沉暗戀了她九年,他心裏的白月光一直是自己。重來一世,她才讀懂了周沉隱忍的深情,嗜她如命。隻是這個膽小鬼一直不敢承認,她決定主動出擊,撩他寵他,給他所有溫暖。周沉在泥濘中生活了二十幾年,從沒想到有一束光會心甘情願照在他身上。感受過溫暖後,他不願再回到黑暗,陰鷙威脅道:“寶貝,是你主動招惹我的,永遠不準離開我。”
18.2萬字8.18 23210 -
連載308 章

廢墟有神明
[暗戀x甜寵xhex男二上位][可鹽可甜x港區小霸王]那年七月,馮蕪爬到合歡樹上抓貓,許星池路過,拽開T恤衣擺:“阿蕪,把貓扔下來,哥哥幫你接著。”一轉眼,長大後的許星池噙著冷笑:“馮蕪,你幫她把芒果吃了,我答應跟你訂婚。”眾目睽睽下,馮蕪一口一口將芒果吃掉,她摸著手背因過敏迅速躥起的疙瘩,輕聲:“星池哥哥,咱們兩清了。”許星池哂笑:“可以,待會我就跟伯父商量訂婚事宜。”然而他沒想到,馮蕪的“兩清”,是真的兩清。喝到吐血那天,許星池在電話裏求她:“阿蕪,你來看我一眼好不好?”-傅司九忝為港區傅家最為紈絝的老幺,眼睜睜看著馮蕪小尾巴似的跟在許星池身後多年。他多少次都險些被氣笑了。這臭丫頭耳聾眼花就算了,連心都瞎了。那天夜晚,馮蕪喝多了,將柔軟的身子埋進他懷裏,傅司九舌尖抵腮,十分矯情:“你這是做什麽,老子不是隨便的人。”馮蕪抬頭,可憐巴巴還未說話,傅司九膝蓋瞬間軟了:“得,抱吧抱吧。”馮蕪捧住他長相風流的臉,“能不能親一口?”傅司九:“......”初吻被“奪走”的第二天,傅司九懶著調:“外麵天兒熱,小阿蕪可千萬別出門,九哥給你送冰咖啡,順便,把名分定了~
51.9萬字8.18 69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