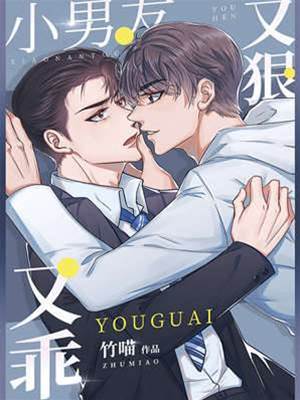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白月光回來后替身離開了》 第九十五章 無法原諒當初他選擇先救安澄
窗外下著大雨。
“我要走了。”
傅時聞沉靜的目落在季柯臉上,用視線細細地描繪著季柯臉上每一寸。
他想了這個人五年。
明明現在林榆就在眼前,卻又像是隔著好幾億年一樣遠,似乎永遠也夠不著了。
傅時聞沙啞的開口,問道:“訂酒店了嗎?我讓老吳送你。”
季柯搖頭:“沒有,不用麻煩吳叔,我打車去機場就行。”
傅時聞緩了緩,說道:“讓他送你吧,他也很想見見你。”
季柯腦海里回想起了吳叔,吳叔臉上帶著幾分憨厚,眼神里又著幾分通達,一直待他不錯。
季柯點了點頭。
傅時聞拿起手機,給吳叔打電話。
掛斷電話,傅時聞說:“他二十分鐘之后到。”
季柯目看向窗外,夜一點點的彌漫上來,需要再等二十分鐘,他不知道該和傅時聞說點什麼。
傅時聞看著季柯的側臉,鏡片下有著一雙很漂亮的眼睛,烏黑明亮,這讓他想起了那天在沙灘上看到的小孩。
他的眼睛和林榆,幾乎一模一樣。
傅時聞低低地笑了一聲:“阿榆,那個孩子是我們的,對嗎?”
傅時問突然提到季,讓季柯有些心驚,他一直都害怕傅時聞知道季的存在,害怕這個孩子生理學上的父親會搶走季。
“季是我的。”季柯警惕地說。
“你不用擔心,我不會和你搶他,”
傅時聞笑了笑,說道,“我知道那是我們的孩子,他很像你,很可。”
季柯不想再繼續聊下去。
和傅時聞多待一分鐘,似乎心里就會多一分的變化,季柯起:“我該下去了。”
“還有,以后我們不要在見面了。”
看著季柯決然的背影,不知道為什麼,傅時聞心里突然產生了一種難以描述的恐懼。
Advertisement
他有種不好的預,這次和林榆分開,或許他們以后真的就沒有以后了。
傅時聞顧不得其它,抓住了季柯的手,終究還是忍不住將挽留的話說出了口:“阿榆,不要走好不好?”
傅時聞的手很涼,像是冰塊一樣,卻很用力,抓得季柯的手生疼。
季柯閉上了眼睛,緩緩地睜開,呼出一口氣:“傅時聞,放開我。”
然而,傅時聞的手沒有松開,反而抓得更了。
“傅時聞,你有意思嗎?”季柯冷冷地看著他。
“阿榆,我們能不能重頭再來一次。”
傅時聞仰頭看著他,眼角發紅,語氣里盡是哀求,仿佛卑微到了塵埃里。
季柯難以描述此刻心里的震撼。
半響,季柯推開了傅時聞的手,轉過頭,故作鎮定冷聲道:“我已經買好了票了。”
他原本打算,過來看一眼傅時聞,然后就回去。
畢竟,傅時聞救了他。
如果不來,他不會心安。
“傅時聞,就這樣吧,到此為止,對你,對我都好。”
傅時聞眼底的漸漸地黯淡下去,他垂下了眼睫:“阿榆,不管你信不信我,我都想對你說一句話,我你。”
“我相信你我,只是,傅時聞,你的太廉價了。”
季柯永遠也無法忘記,在爛尾樓的時候,他選擇了安澄。
說完,季柯轉下了樓。
季柯沒有等太長時間,沒一會兒,老吳開著車出現在了醫院門口。
吳叔和以前一樣,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吳叔,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老吳沒想到還能看到林榆,他們都以為林榆死了。
林榆現在看上去比以前氣神要好很多。
上了車,老吳問:“去機場是嗎?”
“嗯。”季柯點頭。
Advertisement
老吳笑著說:“小榆,你這趟是特意來看傅總的嗎?”
季柯沉默了兩秒,“算是吧。”
“傅總應該會很高興,他很想你。”
車子在路上行駛,雨水嘩啦啦往下潑灑,兩邊的路燈籠罩在雨霧中,紛紛往后迅速消失在視野里。
老吳開口道:“你離開這幾年,傅總其實過得很不好,他總是會出現幻覺,總說經常能看到你,把我們都嚇壞了。”
季柯靜靜地看著車窗外的雨,沒有說話。
老吳看得出來季柯并不想聽這些,他嘆了一句:“哎,人老了總是多。”
到了機場。
老吳拿起傘下車,幫林榆拉開車門。
臨走的時候,老吳忍不住再多了一句:“小榆,年輕人的那些事吳叔不懂,但是這些年吳叔看得很清楚,傅總他對你是真的。”
“吳叔,有些事錯過了就錯過了,不用再說了。”季柯搖頭。
吳叔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好吧,再見。”
“再見吳叔。”季柯目送吳叔離開。
他看了一眼下著大雨的天空,忽然想起了傅時聞捧著戒指痛哭的畫面。
風將雨水吹到了季柯臉上,冰冰涼涼的,好像淚水。
“雨真大。”
季柯低聲喃了一句。
…
傅時聞再次睜開眼的時候,外面天氣沉沉,下著雨。
天氣預報播報著一則臺風即將登錄的消息。
傅時聞忽然想起,季柯現在這會兒正要去坐飛機。
“老吳。”傅時聞撥通了老吳的手機。
“飛機沒有臺風取消航班嗎?”
老吳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難怪這幾天一直下雨,原來是臺風要來了。
傅時聞說:“他應該還在機場,把他接回來。”
季柯被攔在了機場安檢通道口,才知道航班因為臺風取消了。
Advertisement
和他一樣被攔在安檢通道口的人不,下一次航班不知道什麼時候有。
季柯走出機場,打算找個附近的酒店先住下,等消息。
這時,一個小孩走到他跟前。
“叔叔,你看到我爸爸了嗎?”
小孩七八歲大,穿著一件的裳,臉蛋圓圓的,很可。
季柯搖頭,“沒有,小朋友,你爸爸去哪里了?”
小孩抓了抓頭,“爸爸說他去退票,但是我找不到。”
季柯怕小孩一個人不安全,“我帶你去找工作人員吧,當他們幫你找好不好?”
“好。”
季柯帶著小孩走進了機場,迎面走過來一個中年男子。
“茵茵,你怎麼隨便跟著人跑?”
男子張地抱起小孩,看上去應該是小孩的爸爸。
小孩說:“叔叔說帶我過來找你。”
季柯看到這中年男子,莫名的覺得眼,像是在哪里見過。
他盯著中年男子的臉。
中年男人五礦,看上去不是善類,他瞪了一眼季柯,“看什麼看。”
季柯被如同雷電擊中:“是你……”
中年男人仔細一看季柯,也認出了季柯,他慌張地抱起小孩就往外跑。
季柯跟了上去。
“你別跑!”
中年男人站在了機場門口,他沒有帶傘,似乎舍不得小孩淋雨。
他警惕地盯著季柯:“你想怎麼樣?”
季柯微微氣,如果他沒記錯,這個男人的名字王棟。
當年綁架他的人之一。
“爸爸——”小孩也到了父親的緒,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不知所措地著爸爸。
看到男人邊的小孩,季柯猶豫了一下,“你知道孫鵬在哪里嗎?”
季柯說道:“你放心,只要你告訴我他的下落,我可以當做沒看見過你。”
Advertisement
當初綁架他的那個人,那個害死他爸媽的富二代,至今沒有被抓到。
這件事在他心里仿佛就像是一刺。
那種人渣,就應該在監獄里度過一生,而不是拿著傅時聞的錢,至今在外面瀟灑。
王棟依舊很是警惕,“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這時一個游客從他們邊經過,手里撐著一把大傘。
王棟忽然搶過游客手里的傘,抱起小丫頭,往外面跑去。
季柯連忙追了出去。
王棟是建筑工人干活力好,但是他抱著小孩,又撐著大傘,一時間季柯沒有落下多。
季柯對他喊道,“我只要知道孫鵬的下落,你告訴我!”
王棟哪里會回他的話,“你認錯人了,別追我。”
飛機場附近有一片正在修建的建筑,王棟跑似乎對著兒很悉,進去之后,三兩下就不見了人影。
這個時候工地上都接到了臺風通知,所以建筑里幾乎沒什麼人。
季柯在建筑里轉了好幾圈,也沒見半個人影,就這麼把王棟給跟丟了。
正當他有些懊惱的時候,外面響起了雷聲。
風比剛才大了。
大的幾乎能把人給吹跑。
季柯拿出手機,電量剩的不多了,他嘗試著打車。
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見有人接單。
臺風快來了,這會兒滴滴都不跑單了。
他試著冒著雨走回去,誰知一陣大風吹過來,差點把他人給吹歪了。
季柯沒帶傘,上已經。
這會兒,季柯手機上來了個電話。
電話顯示:傅時聞。
季柯猶豫了兩秒,接了電話。
“阿榆,你還在機場嗎?我讓老吳去接你了,他說沒看到你。”
季柯冷得直哆嗦,“我不在機場,在機場附近。”
“你在哪里?我讓他去接你。”傅時聞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的風聲,張地問。
季柯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像是工地。”
說完,電話那頭就沒聲了。
季柯拿起手機一看,原來是沒電了。
猜你喜歡
-
連載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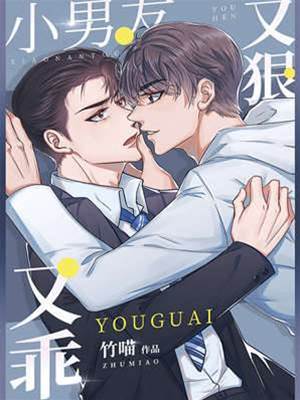
小男友又狠又乖
江別故第一次見到容錯,他坐在車裡,容錯在車外的垃圾桶旁邊翻找,十一月的天氣,那孩子腳上還是一雙破舊的涼鞋,單衣單褲,讓人看著心疼。 江別故給了他幾張紙幣,告訴他要好好上學,容錯似乎說了什麼,江別故沒有聽到,他是個聾子,心情不佳也懶得去看脣語。 第二次見到容錯是在流浪動物救助站,江別故本來想去領養一隻狗,卻看到了正在喂養流浪狗的容錯。 他看著自己,眼睛亮亮的,比那些等待被領養的流浪狗的眼神還要有所期待。 江別故問他:“這麼看著我,是想跟我走嗎?” “可以嗎?”容錯問的小心翼翼。 江別故這次看清了他的話,笑了下,覺得養個小孩兒可能要比養條狗更能排解寂寞,於是當真將他領了回去。 * 後來,人人都知道江別故的身邊有了個狼崽子,誰的話都不聽,什麼人也不認,眼裡心裡都只有一個江別故。 欺負他或許沒事兒,但誰要是說江別故一句不好,狼崽子都是會衝上去咬人的。 再後來,狼崽子有了心事,仗著江別故聽不到,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悄悄說了很多心裡話,左右不過一句‘我喜歡你’。 後來的後來,在容錯又一次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江別故終於沒忍住嘆出一口氣: “我聽到了。” 聽力障礙但卻很有錢的溫文爾
56.5萬字8 6649 -
完結388 章
穿成男頻文裡的惡霸炮灰
《帝業》一書中,男主霍延出身將門,因朝廷腐敗,家破人亡,入慶王府為奴。 慶王世子心狠跋扈,霍延遭受欺辱虐待數年,幾次差點傷重而亡。 直到亂世來臨,他逃出王府,一步一步執掌兵權,霸圖天下。 登基後,將慶王世子五馬分屍。 樓喻好死不死,穿成下場淒慘的慶王世子。 為保小命,他決定—— 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 種糧食,搞建設,拓商路,興兵甲,在亂世中開闢一條生路。 漸漸地,他發現男主的眼神越來越不對勁。 某一天敵軍來犯,男主身披鎧甲,手執利刃,眉目英俊宛若戰神降臨。 擊退敵軍後,他來討要獎勵—— 浮世萬千,惟願與君朝朝暮暮。
81.3萬字8 10097 -
完結253 章

助理建築師
建築系畢業生張思毅回國求職期間,在咖啡館與前女友發生了爭執, 前女友憤怒之下將一杯咖啡潑向他,他敏捷躲閃避過,卻讓恰巧起身離席的隔壁桌帥哥遭了秧。 隔日,張思毅前往一家公司面試,竟然發現面試自己的人正是替自己挨了那杯咖啡的帥哥! 心如死灰的張思毅本以為這工作鐵定沒戲,不料那帥哥「不計前嫌」地錄用了他,還成了他的直屬上司。 當張思毅對帥哥的善良大度感激涕零之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悲慘」的命運這才剛剛開始…… 張思毅:「次奧,老子就害你被潑了一杯咖啡,你特麼至於嘛!TAT」
65.8萬字8 298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