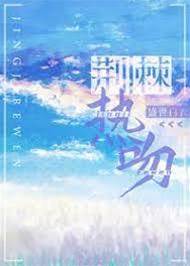《他與愛同罪》 第七章
傅征跟沒聽見一樣,反手關上門,大步邁向駕駛座,有條不紊地下達指令。
一直保持待命狀態的吉普,車微微抖著,那輕鳴的引擎聲像是隨時要出征的士兵。平時從不會在意的聲音,燕綏愣是在此時聽出了幾分安心。
著被抓疼的肩膀,視線忍不住落在傅征上。
年輕男人的肩削薄直,一不茍的作戰服也穿出了正裝的筆。握著方向盤的手,五指修長,著尋常男人鮮有的利落。
燕綏的方向,能看到他小部分的側臉。
他的帽檐得很低,微偏頭注視著戰況,眼神專注,有。微抿起時,部線線條銳利,有一種常年在沙場才會有的堅毅。
冷靜,沉穩。
燕綏很難想象,剛才把命給了這樣一個人——一個如果看臉,未必讓覺得有安全的英俊男人。
——
路黃昏收到傅征讓他營救車人質的任務后,借著隊友掩護,繞到車的背側。
陸嘯那側車門被打開時,他嚇了一跳,還沒看清人,手里唯一的對講機被他下意識擲出。
他驚恐地后退,一米八的年輕男人張起來連條件反的抵抗都跟花拳繡一樣,一腦全部招呼出去。
路黃昏險些被對講機正中砸臉,驚險地避開,出去的手剛著陸嘯的袖就被對方跟甩小強一樣一把揮開。
路黃昏懵了一瞬,有那麼一刻有點懷疑人生。
時間迫,避免耗在陸嘯的不配合上,路黃昏強行登車,單手制住陸嘯踢蹬的雙,一手勾住陸嘯的脖子迫得他彎下腰來,一帶著東北味的普通話撲面而來:“兄弟,睜開眼仔細瞧瞧。”怎麼跟個娘們似的。
后半句話他當然沒有說出口,只是嫌棄之毫不遮掩。
Advertisement
他往車巡視了一圈,看見瞪著雙眼和他對視的辛芽,問:“車里就你們兩人了吧?”
辛芽還在哭鼻子,噎著點點頭。
狙擊手的火力覆蓋下,已經失了頭領的索馬里人跑的跑散的散,早就不氣候了。
如今車外還有一位特戰隊隊員,正和雇傭兵車隊僵持著,想不造更大的沖突,就必須抓時間趕撤離。
路黃昏毫不客氣地拎著陸嘯后頸把他拉下車,邊上辛芽:“你趕也出來。”
辛芽卻急了,雙手還鎖著司機,本不敢松開,眼看著路黃昏把陸嘯帶走了,又哭起來。
路黃昏被哭得一張,又探回來,還沒問呢,辛芽啞著聲音先開口了:“我松手了他怎麼辦啊……”
路黃昏沉默。
他憋著勁,好半晌才下那難言的暴躁,面無表道:“要不我把椅子給你拆下來,你帶著一塊走?”
車熄火多時,車空氣流滯,有與車外涼爽不同的悶熱。
辛芽是用力哭都憋出了一汗,此刻和路黃昏大眼瞪小眼數秒,腦子終于恢復正常運轉,沒敢再接話,飛快松了手,拎起后座上的雙肩包,推門下車。
一腳剛落地,又想起什麼,飛快爬回去,從陸嘯座位上撿走了那把燕綏花了三百金買下的槍塞進包里,手腳并用的下了車。
路黃昏一手拎一個,跟拎小仔一樣立馬把兩人拎上車,回頭接應隊友。
——
空間寬闊的吉普車后座,一下子坐下三個人,瞬間變得擁。
不過此時,車外槍聲不斷,劫后余生的三個人誰也沒先開口說話,安靜地坐在后座。
眼看著局面被控制,傅征啟車輛,后退式倒了一段路,剛停下,后備箱被掀開,兩位從戰場撤離的戰士飛快跳上車,一把下后備箱的車蓋。
Advertisement
燕綏只聽子彈落在車上,數聲槍響后,吉普的油門轟鳴,瞬間提速,飛快穿過難民區的牌坊,后加速地面揚起的煙塵洋洋灑灑,把整個視野遮擋得只有難以穿的沙土。
最后的槍響也停了。
四驅的吉普從蜿蜒的土坑爬上土堆,車起起落落數次后終于駛上公路,一路坦途。
張的氣氛沒未散去,車里依舊安靜著,沒人先起話頭。
一直到車穿進巷道,彎彎繞繞地開了小段路后,停在路邊,穿著作戰服抱著步槍的特戰隊員上了車,所有人員到齊,辛芽死命憋了一路的打嗝聲終于從指中出。
漲紅了臉,另一只手也牢牢地捂住,驚惶地和轉頭看的狙擊手對視一眼。
胡橋年紀小,又是娃娃臉,看著跟還沒長的瓜一樣,著幾分青。他見辛芽不好意思,笑了笑,安:“已經安全了。”
辛芽幾不可聞的“嗯”了聲,默默地把捂得更嚴實。
燕綏在商圈,出了名的商高,會來事。
這種了別人救命之恩才死里逃生的時候,哪怕只是口頭謝都能真誠到讓人無法拒絕。可這會,心里裝著事,連說話的心思也沒有,眉頭皺得的。
想了半天,還是沒想明白在答應五十萬金過路費之后,為什麼武裝頭目會反口讓他手下拿槍抵著,甚至一言不合令手下打死了可以算是同伙的雇傭兵頭子?
著眉心,在腦子里回放著從下車后發生的每一個節點,仔細到連悄悄看了幾次手表都沒有掉……直到回想起在被槍口抵住背脊時,那武裝頭領抬頭看陸嘯的畫面,挑眉,轉頭問坐在最外側的陸嘯:“那個頭領,想讓你告訴我什麼?”
Advertisement
陸嘯的神經剛放松了一會,突然被提問,臉上的表還沒來得及管理,呆萌地和對燕綏對視了幾秒,才道:“他說知道你深夜趕路要去索馬里海域贖金。”
燕綏若有所思地了下。
雇傭兵和武裝頭領是一伙的這事是沒跑了,按照正常邏輯推斷,應該是雇傭兵頭子在聽到武裝頭領這句暴他們合作事實的話被燕綏聽懂,擔心不止尾款收不到,很有可能整筆易都會被取消,所以一時沒忍住,氣急敗壞地和他理論起來。
結果武裝頭領暴脾氣直接干掉了雇傭兵頭子……
如果當時沒有發現兩隊人馬互相勾連,沒有第一時間選擇向自己的國家求援,事糟糕些可能這會已經死在兩隊的火拼中,又或者自己孤犯險,被榨干剩余價值,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實在不敢高估人。
索馬里海域的強盜在索取贖金后還會“誠信”地放船放人,那也是因為對于他們而言,劫持船只索要贖金是一筆生意,生意就要講誠信,如果收到巨額贖金卻不放人,此后再遇到劫持事件,不會有人相信他們拿到贖金后還能安全釋放人質。
但在索馬里,遇到今晚的況,真的不敢想,如果沒有中國公民的份,是不是……嗯?
這種后怕的緒讓心口像是堵了一塊石頭,沉得不上氣來。
燕綏忍不住了自己的脖子,總覺得涼涼的,項上人頭早已落地了一樣……
嗓子干的,不出一句話來。
抬眼,過車后視鏡只能看到傅征的帽檐,盯著看了幾秒,清了清嗓子:“謝謝你們……”
很久沒說話的嗓音有些沙啞,輕咳了一聲,繼續:“要不是你們及時趕到,今晚就要待了。”
Advertisement
路黃昏盤坐在后備箱,聞言,掀了掀眼皮子,也不知道要婉轉些,直腸子道:“這種危險的地方,你不帶個三五個保鏢就算了,還帶了兩個保姆出門拖后。”
燕綏:“……”
胡橋趁轉頭瞥窩在角落還怡然自得的路黃昏,怕尷尬,善解人意地轉移話題:“燕小姐,你學過擊嗎?”
他還一直記得耳麥里突然出的那一聲槍響,雖沒親眼看到燕綏開槍,但在當時,對已經把燕綏定位手無縛之力又養尊優總裁形象的他而言,著實驚艷。
“學過。”燕綏沒否認:“我外公是朗譽林,他教的我。”
車頓時一片寂靜。
陸嘯和辛芽還不知所以,車里海軍特戰隊的幾位隊員不自覺的就肅然起敬,就連傅征,也過后視鏡側目看了一眼。
朗譽林年輕時曾任533驅逐艦第一任艦長,級中將,是赫赫有名的將軍,也因他和海軍的因緣深厚,海軍部隊無人不知。
——
胡橋一時不知道該接什麼話,可不說話又顯得他有些淺,哪有聽到人家外公是將軍就不說話了……于是絞盡腦,憋出一句:“燕小姐,你的衛星電話是放哪了才沒被他們發現?”
話音剛落,后腦勺就被招呼了一下。
胡橋吃痛,捂著腦袋轉頭去看面無表好像什麼都沒發生的傅征,委屈兮兮地了聲:“隊長……”
傅征頭也沒回,斥道:“問什麼問,哪那麼多廢話。”
聲音得極低,卻一字一字,盡數落燕綏耳中。
抿,借著偏頭看窗外的作,悄悄遮了遮忍不住彎起的角。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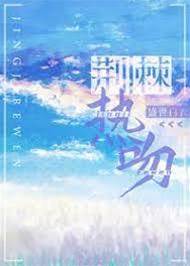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542 章

總裁寵妻無上限
結婚剛一年,老公挽著她閨蜜的手一腳踢掉她肚子里的孩子。噩夢醒來,一個天神般的男人捏著一張支票說要買她,離婚當日,他扯著她的手就去領了證。從此她葉以念成了申城人人羨慕的陸太太。他寵她,寵的無法無天,她卻不知這不過是她劫難的開始………
96.3萬字8 114463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