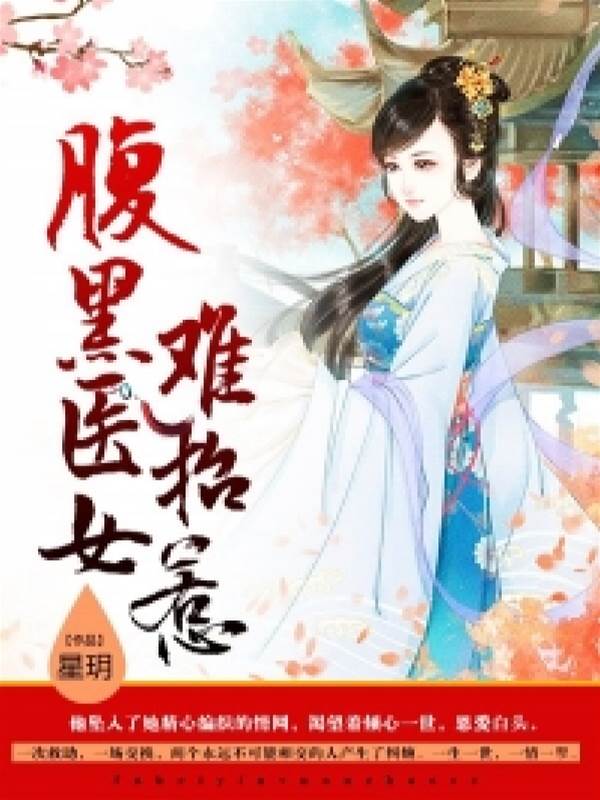《貼身丫鬟》 第63章
傅慎時在鏡子前面整理儀容。
殷紅豆專注著燒炭, 沒太注意傅慎時舉, 只是又聽他說要換服, 便凈了手去給他找。
找來找去,試了三件傅慎時都不滿意。
殷紅豆翻箱倒柜, 也不知道傅慎時到底想穿什麼服, 臂彎里搭著一件藍的羽緞, 道:“六爺要出門見人嗎?”
傅慎時淡淡道:“一會兒去莊子外面看看。”
殷紅豆撇撇,外面白茫茫一片, 去了也看不見什麼, 穿那麼挑剔做什麼?還是將手里的羽緞遞了過去。
傅慎時忽扭頭看著,漫不經心地問道:“這件羽緞怎麼樣?”
殷紅豆眨了眨眼,驀然想起薛長穿的狐大氅,漸漸明白過來,傅慎時這廝不會是在跟人家比吧?!
這又是……吃醋了?
殷紅豆笑了笑,連忙湊過去替他披上, 兩手在他鎖骨前面,指頭翻著, 系著帶子, 道:“這羽緞有八分,不過穿在六爺份, 就有十分了。”
傅慎時睨一眼,沒有說話。
殷紅豆繼續道:“您這一, 比流云公子昨兒穿得還好看。”
傅慎時皺了皺眉, 冷聲道:“我又沒問你這個。”
殷紅豆腹誹:是啊, 你沒問,可我不能不說啊。
傅慎時果然臉緩和了幾分,語氣也愉悅些許,道:“好了,就這件吧。”
殷紅豆瞇眼一笑,轉去準備暖手爐等隨件。
時硯扶著傅慎時站起來,整理好裳,復又坐上椅,往門外去了。
殷紅豆穿著耦合中襖,穿著厚厚的靴子,從上到下,帶著昭君套、圍脖、手套,懷抱一把傘,半張臉都埋在圍脖里,就一對漆黑的眼睛和飽滿潔的額頭在外面。
Advertisement
主仆三人出了房門,庭院里,王武正在練拳,幾人相互打了招呼,殷紅豆他們便從前門到院子外邊去。
廖媽媽和兒子媳婦,還有小孫子在倒座房里烤火,聽到靜,跟了出來,手里也抱著個暖爐,追上來問:“六爺要去哪里?天兒太冷了,外邊沒有幾個佃戶,您別走遠了,遠了迷路了就麻煩了。”
傅慎時羽緞上還有一圈兒蓬松的兔,圍著他瓷白致的臉,在冰天雪地里顯出幾分稚和青,他淡聲道:“只去附近看一看就回來,外邊冷,您回去吧。”
廖媽媽點了點頭,代了殷紅豆兩句,便轉回去了。
主仆三人行走在疏松的雪地上,留下幾個腳印和車轍印。
殷紅豆怕冷,臉頰都凍得繃了,道:“六爺,要不咱們回去吧,這兒一眼去都是遠山,在院子門口不一樣看得見?何必走遠了看?”
傅慎時就是出來氣,看一看雪日的,殷紅豆這個俗丫頭這麼一說,有些掃興致,可他剛出來就回去,豈不是太順著的意思了?
他腦子里轉了好幾道彎兒,才道:“你要冷你就回去。”
殷紅豆低哼一聲,傅慎時沒回去,敢回去嗎?低著頭,用力地踢著腳邊的雪,孩子氣得很。
傅慎時瞧著臉頰氣鼓鼓的,邊抿了個笑。
殷紅豆慢慢地跟在椅后面,左腳踢一下,右腳踢一下,玩著玩著上就熱了,也玩出了些樂趣,將傘塞給時硯拿著,在雪地里了幾個雪球放在腳邊。
朝著傅慎時那邊喊:“時硯,你回頭。”
椅正好停下了,時硯和傅慎時一起回頭,雪球糊滿了他倆的臉,跟唱戲的丑角兒鼻子中間那塊兒的彩一樣,殷紅豆樂不可支,捧腹大笑。
Advertisement
傅慎時抹掉臉上的雪,角落了些純白的雪屑,化在他的角,冰冰涼涼的,邊竟又發了熱,他黑著臉看向殷紅豆,道:“過來。”
殷紅豆離得遠,聽不見聲音,只是遠遠地看見他的口型,好像在喊。
走過去嘟噥道:“我又沒喊您,您自己回頭的。”
傅慎時正要教訓殷紅豆,哪知一腳踩進雪里,不知道踢到了什麼,一跟頭栽地上了,整個臉都埋進了雪堆里。
他不由自主地往前一傾,出手臂要去拉,過一會子又反應過來,瞬間收回手,兩手抄在袖子里,冷淡地掃了殷紅豆一眼,角卻翹了翹。
殷紅豆撐著子起來,抬起頭,額前的墨發上都沾了碎瓊玉,像是撒了些細碎的玉石在頭上,瑩亮彩,將的臉頰也襯得愈發可。吃了一的雪,皺著臉“呸”了幾聲,道:“就說不該出來,吃了一的灰,膝蓋也磕疼了。”
了膝蓋。
傅慎時沉著角,沒好氣地看著。他正要說回去,王武跑過來了,手里拿著一封信,一邊跑一邊喊。
王武一直住在院子里,他偶爾會出去打些野味兒,秦氏來的那天,他就正好出去了。今天天太冷,他就待在院子里。
這邊的主仆三人都向王武。
王武從院子大步跑過來也不帶氣的,哈了一口熱氣,同傅慎時道:“六爺,汪先生派人來傳信了。”
他將信雙手遞給了傅慎時。
傅慎時拆開信,一抖,快速瀏覽了一遍,看向王武道:“備馬車,進城。”
殷紅豆也打起神,隨便掃掉了臉頰上的雪,跟著椅后邊回了院。
出門了好幾趟,殷紅豆收拾東西都駕輕就了,快速地收拾好包袱,帶上了賬冊和傅慎時雕刻好的章子,跟廖媽媽悄悄地打過招呼,瞞著廖媽媽的兒子媳婦,從后門上馬車,趕到城里去。
Advertisement
車上,殷紅豆坐在傅慎時腳邊的小杌子上,抱著傅六的手爐,問道:“六爺,什麼事兒呀?”
傅慎時道:“孫七來找我了。”
殷紅豆蹙著眉,道:“怎麼流云公子才走,孫七就來了?您說流云公子是平白無故來的嗎?”
傅慎時略加思索,道:“應該只是巧合,孫七使喚不他,若是二殿下要試探,不會派他來,而且二殿下謹慎,輕易不會用不悉的人,還未到要打聽我份的地步。”
殷紅豆“哦”了一聲沒再問了,其實二皇子遲早會知道,只要他跟六皇子通個氣,這事就瞞不住了。
瞞不瞞得住,沒什麼要,要的是,要讓二皇子覺得傅慎時是可用之人。
馬車午時之前到了發財坊附近的巷子,王武出去探路,見沒人從巷子經過,就帶著傅慎時他們從后門上了二樓。
汪先生正在雅間里等著。
傅慎時等人進了雅間,椅在厚實的絨毯上,靜默無聲,房間放了兩個銅盆,燒著銀屑碳,一煙火也沒有,室溫暖如春。
殷紅豆放下手爐和包袱,泡了幾杯茶水。
傅慎時與汪先生一起坐在桌邊議事,他問:“先生信中敘述不詳,到底是怎麼回事?”
汪先生將孫七告訴他的,以及他自己打聽來的,都告訴了傅慎時。
原是二皇子的人已經將沉船之上的活口抓住了,不過抓住了,也還沒敢將他放出來當人證。
因為此案件涉及京師員。
雖然刑部掌京中笞罪以上的案件,沉船之事涉事重大,此案件要是開始審理,未必落得到刑部尚書的手上。
京中督察院一貫負責京師職犯罪案件,或者是別省巡按史、各省提刑按察司轉達過去的登聞鼓冤案件。
Advertisement
督察院史乃大皇子的黨羽。
簡而言之,督察院一定會咬死此案乃京師職案件,定會將此人回督察院大牢待審。
如若這般,孫七所為,功虧一簣,依他的子,費這麼大勁兒,熬著夜吃了風吹雪打的苦頭才抓住的人,就這樣放給督察院查辦,還不得氣瘋了。
孫七的父兄也有意刁難他,又問他抓住了此人,可有法子再保住此人不落大皇子的手里。
他之前牛皮都吹出去了,這回要是難住了,便是父兄面前下不臺,自然著頭皮答應了,轉臉就求到汪先生這兒來了。
汪先生擅長結朋友,理事務也有自己的一套準則,不過謀略急智,還是不如傅慎時,他心中有個主意,卻不大拿得準,便請傅慎時一同來商議。
傅慎時先問汪先生:“您的主意是什麼?”
汪先生道:“督察院要以‘審理京師案件’為由審理此案,可此人卻是揚州員,若是以此相辯,可否一試?”
傅慎時搖頭,道:“有些站不住腳,何況揚州那邊隨便派個人民人擊鼓登聞鳴冤,說此人貪贓枉法,不就又回到了督察院手里?”
汪先生一臉為難之。
殷紅豆大概聽懂了一些,也嘗試去想,有沒有法子解決這問題,可惜本就對大業朝廷制不,至于場上的彎彎繞繞,就更不清楚了。
一抬眸看見傅慎時氣定神閑的樣子,就知道他又有主意了。
汪先生微微欠道:“六爺可有主意?”
傅慎時“嗯”了一聲,隨即就看了殷紅豆一眼,才繼續同汪先生道:“其實二殿下手里未必沒有能人,說不定法子已經想出來了,只不過是故意為難孫七而已。不過我也的確有法子。”
殷紅豆眸漸盛,笑地看著傅慎時。
就知道他有辦法。
天生的謀謀家。
猜你喜歡
-
完結1601 章

邪王寵妻:廢材狂妃要逆天
一朝穿越,她成了被人丟青樓的大學士嫡長女。親爹為前途廢嫡立庶,夠狠;姨娘貪材私吞她嫁妝,夠貪;庶妹虛偽奪她未婚夫,夠賤;比狠,火燒太子府;講貪,一夜搬空國庫;論賤,當街強搶美男。若論三者誰之最,當數司徒大小姐第一。某天,司徒大小姐滿腔怨怒:「左擎宇,你真狠!」「多謝愛妃誇獎。」靠近她的所有男性一個不留。「你太貪!」「必須的。」一天三餐還不飽,半夜還要加宵夜。「你真賤!」
286.3萬字8 33284 -
完結713 章

逃荒不慌,全家大佬種田忙
徐月穿越了! 穿越的第一天,她爹垂死病中驚坐起:吾乃堂堂金丹真人! 穿越的第二天,任勞任怨的娘親,沖她爹甩手就是一巴掌:你要是我艦船上的兵我早特麼一槍斃了你! 第三天,憨厚內向的大哥忽然暴起,力大無窮,喉嚨裡發出吼吼的非人吼叫,見人就咬! 第四天,不小心腦袋磕在桌角上昏死過去的姐姐醒來之後就喜歡撿棍子蹲灶房裡“咻咻”的比劃著什麼,嘴裡念念有詞,似乎是某種古老的咒語…… 就在徐月覺得自己已經夠慘時,隔壁快嗝屁的大爺告訴她:“自董興入京以來,天下群雄並起,佔據州、郡者多不勝數,又逢天災,民不聊生,餓殍遍野......” 徐月看看屋內面目全非的家人,又看看外頭屍橫遍野的慘像……她不活了行不行! PS:無CP
129.8萬字8 43436 -
連載426 章
我在廢土世界掃垃圾
正在末日帶頭打喪尸的祝寧穿越了,這次她穿越到了廢土世界。這個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被荒廢,人類建立起高墻抵御外界襲擊。這里有怪物、有污染物、有超能力、有超級人工智能、甚至有邪神。祝寧綁定了一個凈化系統,系統頒布主線任務:凈化被污染的土地,拯救家園。祝寧:哈?怎麼不直接送她去死呢?這大餅愛誰吃誰吃。她想當咸魚,但條件不允許。面對污染物,經歷過末日求生的祝寧很快脫穎而出,她身手好膽子大,重點是精
123.1萬字8.18 262992 -
完結2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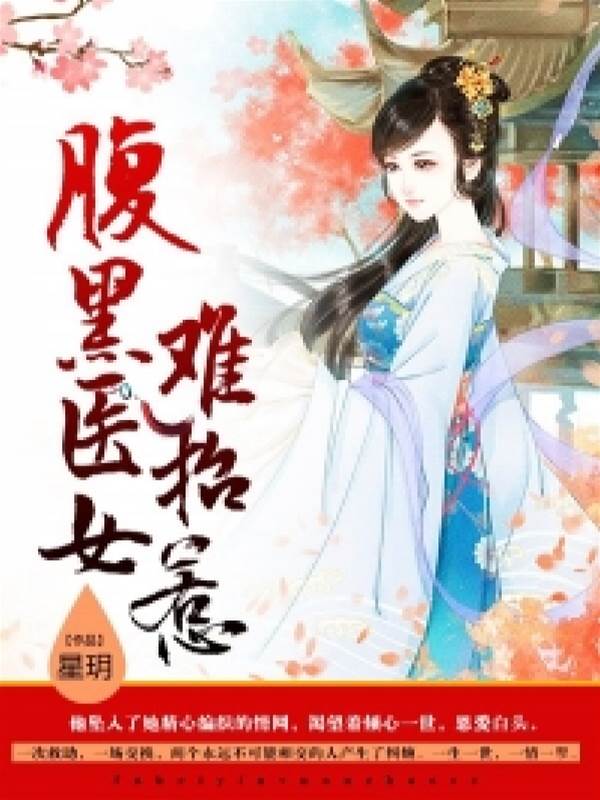
腹黑醫女難招惹
她本是現代世界的醫學天才,一場意外將她帶至異世,變成了位“名醫圣手”。 他是眾人皆羨的天之驕子,一次救助,一場交換,兩個永遠不可能相交的人產生了糾纏。 一生一世,一情一孼。 他墜入了她精心編織的情網,渴望著傾心一世,恩愛白頭。 已變身高手的某女卻一聲冷哼,“先追得上我再說!”
42.7萬字8 116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