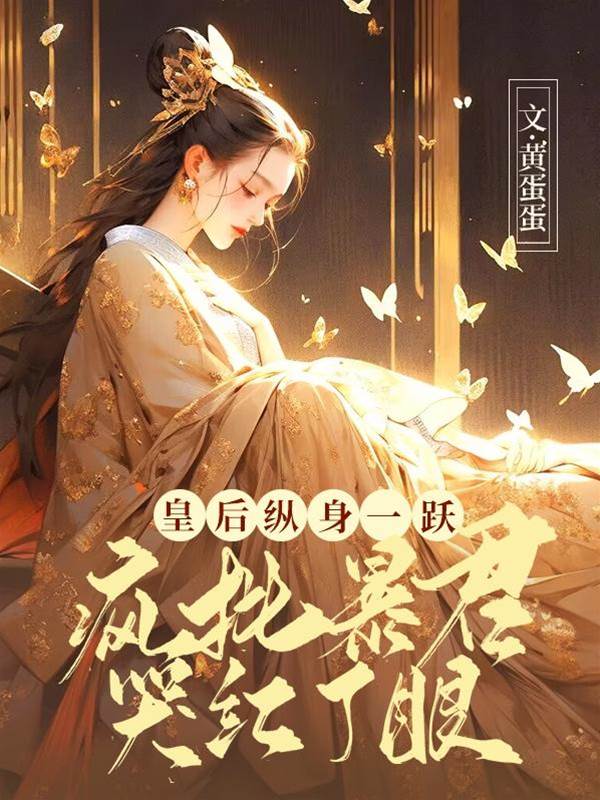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小狼狗飼養守則》 第三十九章
“去山里收藥?”蕭祁文略有興味的看著林羨,“路途迢迢,你倒是不怕累。”
倒是沒有一句話就將事否了。
然后得不到林羨再開口,就答應了下來,“那到時候我從蘭城回來,再看來回時間的安排。”
“蘭城那邊,”林羨忍不住開口追問,心里已經據自己見過的種種現實而有一些猜測,雖然已經有了六七分的把握,但是還不能確定,需要一個知道的人給一個合適的答案。
“蘭城那邊近來不會有大變,”蕭祁文說話直爽,并不對林羨有什麼瞞,“起碼近一兩年里不會有什麼變,但是上面的意思已經有了,那邊的海運是要通的。”
這種幾乎會震一方的話,蕭祁文隨口也就說了。林羨不由得懷疑起他的份,目狐疑的落在蕭祁文的上。
蕭祁文本盯著吃干草的馬,到林羨落在自己上的目,忽的回頭過來,與的目撞在一起,渾不在意的笑問,“做什麼這樣盯著我?”
林羨挪開自己的目,想了想開口道,“我看過書上記載,曾經的蘭城非常繁茂,都是因為海運的緣故,如若以后開了海運,蘭城不日就能重回昔日的盛景吧。”
“哪里只有這樣呢,”蕭祁文輕輕搖了搖頭,“圍繞著蘭城周圍的許多城鎮都會益,特別是清溪鎮,去往蘭城的道就是從這兒過的,后頭好事還多著呢。”
“那是很好的,”林羨的眼睛亮起來,似乎有話要往下說,但還是只偏過頭去邁開步子往廚房走,“我去準備午飯,一會兒阿靖也要回來吃飯的。”
“那小子……”蕭祁文輕嗤一聲。
他擺明了不喜歡林靖,林靖對他也只有不對付。
Advertisement
如果不是因為蕭祁文因緣巧合讓他遇見了林羨,并留在這了這里,林靖還恨不得找準時機將蕭祁文也弄死呢。
一大一小再見面,大眼瞪小眼的互相看了一會兒,后大的那個先開口。
“不過幾個月不見,你倒是大變了模樣。”
林靖冷測測的看著蕭祁文,沒說話。
蕭祁文便跟著沉默下去,目懶散散的從林靖的肩頭落到他的腳上。他的扎在子里,是個很利落的打扮。
蕭祁文趁著林靖不注意,忽然出一只腳,用了七分力道踢去。原本預計著是要橫掃到林靖的骨上,不過還不等到林靖的邊角,就給他往后一,順勢步履靈活的往旁邊跳去,躲開了蕭祁文早有預備的下一招。
“不錯,武功倒是長進不小。”蕭祁文收起手上的作。
“總有一天會比你的好。”林靖道。等到時候,要怎麼收拾蕭祁文就由他定奪了。
蕭祁文饒有興味的看著林靖,“到時候你還能宰了我?”
他笑瞇瞇的湊近林靖,將手按在他的腦袋上,低聲像是提醒,“我是阿羨唯一的表哥。”
是了,林靖的眸子里因此閃過一猶豫也遲疑,他拍開蕭祁文的手,扭頭看向廚房里正忙碌的影,讓阿羨難過得事他不想做。
林靖自己也覺得震驚不解。
他在最苦最難的時候曾經對自己發過誓,就算拼去自己的命也要從泥地里爬起來,那以后連皇帝老子都算是旁人,旁人的喜怒哀樂與他何干?
可現在林羨明顯牽了他的緒,就連蕭祁文也看的清清楚楚,并以之為林靖的肋。
隔天蕭祁文就啟程去了蘭城,林羨則特意請鄭家娘子去全府帶了話。
全家大媳婦本來就急沖沖的等著這脂膏過來,現在一聽有耽擱,問鄭家娘子是為了什麼,鄭家娘子也說不太清楚,便又差了阿茹親自去林羨哪里問。
Advertisement
“娘子那邊很急,說阿羨你若是有什麼難,只管和說就是了,”/>
林羨搖頭,將話說的很圓,“只是藥材上短了幾味,又不好直接用那劣等的來充數,”頓了頓,問阿茹,“不知道娘子那邊,這些天停了脂膏,臉有沒有變回去?”
阿茹笑道,“這個倒是沒有的,的確白了,幾天不用也還是那個樣子,就是因為這個所以娘子才急著讓我來催促,也是看準了你做出來的東西真心的有用呢。”
一聽如此,林羨心里的一點憂也就放了下來,只告訴阿茹找好了藥材就馬上送過去。
下午不知怎麼毫無預兆的下起雨來。
林羨再家里放心不下,等到時間差不多,自己撐了傘去書院接人。青哥兒與江哥兒家里長輩都做活不開,林羨便幫著一一帶了雨傘去。
剛好靖哥兒昨天晚上說先生說了書單讓他們買,林羨就又多帶了點錢在上,準備一會兒陪著林靖一塊兒到書店里看看。
到了書院門口恰好是下學的時間,只是這雨勢磅礴又來的突然,大部分學生都沒有帶傘,有狼狽往雨里面沖的,不過許多人還是站在廊下等著自己家人來接。
林羨來的算是早的。
青哥兒與江哥兒還有幾個低齡的孩簇擁著林靖往外走,嘰嘰喳喳的不知道說的什麼,林靖只間或一兩句,旁邊的那些孩子無一不是羨慕的神。
“阿靖。”林羨往前走了兩步,聲音不高不低。
林靖馬上聞聲轉頭過來,一見到林羨,原本木然的臉上立刻閃出笑來,也不管下雨了,撒就往林羨這邊跑。
好在兩人沒差幾步路,林羨見狀就加快腳步迎了上去,將傘罩在了林靖的頭上。
Advertisement
林靖長高的很快,幾乎和嬰孩一樣一天換一個模樣,本來差不多林羨肩頭那麼高的,此刻已經只和差了半個腦袋了。
“這兩把傘是給青哥兒和江哥兒的,”林羨與林靖靠著肩膀,免得雨落到兩人的肩頭,上前將雨傘遞給另外兩個孩子。
邊上家里人還沒有來的孩子,都目艷羨的看著林靖。
又因為林靖在書院的孩子中間很有聲,其他人見了林羨也不敢怠慢,一個個客客氣氣規規矩矩的照著禮數給了尊稱,而后也不知道是不是默契,一個個又都低下頭去不敢多看林羨半眼。
江哥兒與青哥兒兩人傘大,順路便還捎帶了另外兩個家里住的近的孩子。
“你昨天說有書要買,現在剛好,咱們去書店里看看。”
“不用的,”林靖搖頭,“青哥兒昨天已經買了,我和他說好借來讓我抄一本。”
一套書買下來要一兩銀子,林靖怎麼算都舍不得。更何況家里的錢現在都是林羨一點點掙回來的,他還只會花錢而已。
“抄一本書多費心力,”林羨卻不贊同,“且現在家里也不是拿不出來,在這些地方不用這般輕省。”
林靖在別人面前都是說一不二的主,到了林羨這里卻總是能給三言兩語說的搖起來。林羨也不管他低著頭沒說話,只拉著他的手腕往前去了書店里。
傘上面滴滴答答的全是水珠子,便直接先留在了書店門口。
一說要買什麼書,書店里的伙計立刻就拿了出來。
“趕巧了,最后一套,小娘子若是遲來一步就要再等半個月了。”
林羨點頭干脆道,“幫我包起來。”
外頭雨下得大,小伙計特意在書的外頭包裹了兩層油紙,風雨再大書也不怕淋。
Advertisement
包好以后徑直遞給了林靖。林靖抱著那沉甸甸的書,角忍不住往上揚。
他一手抱著書,一手拉著林羨的手不肯松了。
林羨低頭笑看他一眼,由得他去了。
兩人一前一后,正要往書店外面走。正要拿傘,卻半路出一只手來,“鄭兄,這兒還有一把傘呢,不如你拿去用就是了。”
那傘的一邊已經被那人拿在了手里,眼看著就要整個拿過去。
林靖出手如電,飛快的用兩指在那人的手腕上打了一下,不知道中了哪一寸麻筋,那人只覺得自己的手上霎時力,原本已經在手里的傘又給個小孩搶了回去,穩穩的握在了手里。
林靖拿著傘,目不善的回頭看,鄭郁文果然赫然在列,剛才的那聲鄭兄是他的。
他的盯了鄭郁文一會兒,直讓對方后背生寒,這才收回目,將視線落在了出手搶傘的人上。
那人打扮的富麗,料穿著都很上乘,不知是哪一家的郎君。
“你竟敢打我?”眾目睽睽之下給一個小孩兒將傘奪了去,他難免惱怒,上來就要與林靖手。
林靖哪里會怕他,回一腳踢在對方的骨上,一陣鉆心的痛,差點兒讓人就地跪下去。
鄭郁文見狀臉也白了,匆匆忙忙的上前道,“林小娘子,你可知道這是全家的郎君,你還敢縱著你弟弟行兇嗎?”
林羨本來也皺著眉頭在打量全家的小郎君,琢磨著他是哪一家人以便衡量輕重。鄭郁文的話一出來,反而一下釋懷了。
全家的?那正好了。
“他奪傘在先,還想對阿靖手,兩樁都是他錯在先,全家人如何,全家人就能在鎮上隨心所了?”林羨看都懶得看鄭郁文一眼,只講目放在全家郎君上,“若是這個道理,我是想去問問全家大娘子,全家是不是認這個道理。”
全家人口簡單,年紀這麼大的郎君只一個,全家大娘子生的。
全睿聽見自己娘被林羨提起,一時有些氣短。他娘對他的管教一向很嚴格,規矩上的事是沒有別的話好說的。
他一開始也不過是想要將那傘拿過來塞到鄭郁文的手里,再看看他和林家娘子的熱鬧罷了。如果說針對誰,其實也是奔著鄭郁文去的。
只是這會兒如若服未免太過跌面。
全睿咬牙指著林靖道,“明天起你就不用來上學了!我讓書院開了你。”
林羨不慌不忙的拉著林靖,面上半點不怵,道,“隨郎君高興,我們先告辭。”
活就是半點兒沒有將全睿的威脅看在眼里。
等到第二天,林靖也就不去上學了,去梁家練了功以后,和梁鴻義說,“師傅,我今天不去上學,您陪著子圭去書院吧。”
梁鴻義正坐在石頭上吃早飯,見林靖一套拳打下來行云流水,正覺滿意,聽到這一句愣了愣,問,“怎麼不去上學了?”
“就今天不去,”林靖也是老神在在,只搖頭也不說明白。
梁鴻義放下碗筷,“反正你不上學了,那幫我陪著阿旬去書院里也無礙。”
他現在將梁旬的托給林靖是十個放心,一個多月下來已經清閑慣了,哪里愿意將這差事重新挑回自己肩上?
倒是梁馮氏從屋里走出來聽見這話問了其中詳細。
再等聽完林靖的話,梁鴻義卻是笑了,“有意思。”
梁馮氏擰著眉頭,“那全家郎君未免太張狂了些。”
“這是丟了臉面要找回來,”梁鴻義搖頭,咕嘟嘟的喝下了最后一口粥,“不過只怕這臉面最后不僅找不回來,反而要丟了去。”
的確是這樣。
青哥兒與江哥兒早上一來書院就去見了先生,告訴他靖哥兒以后不來書院了。
書院的先生昨晚上就聽了上頭人囑咐下來說全家人開口,要將林靖給開出書院。老先生當下就發了脾氣,話說的頗不給臉,“那個全家的木魚我是教過的,讀書沒有多聰明氣就罷了,現在還想作這樣的怪?實在枉為讀書人!”
林靖是他教了這麼多年里數得出來讓他喜歡看重的學生,因為一個紈绔開口就能將人給開了?
老先生左思右想,覺得恐怕是林家兩個孤苦的姐弟懼怕全家的勢力,于是當下課都先不上了,親自要去林家將學生請回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163 章

云鬢亂:惹上奸臣逃不掉
守寡三十年,卻發現自己的老公沒死,躲在外面又養了一個!婆婆、叔嬸都知道,可為了逼她當年做馬,獨獨瞞著她!到死,她都沒有享過一天福!再次睜眼,柳云湘重生到嫁進靖安侯府的第三年。既然侯府對她不公,她便顛覆這一切,要背叛她的渣男付出代價!成為天下第一女商賈,權傾朝野!只是,上輩子那個把她當替身的奸臣嚴暮,怎麼黏上來了?不是應該為了扶持白月光的兒子登基,甘愿犧牲嗎?
198.3萬字8.46 397189 -
完結399 章
穿越后我在四爺后院當團寵
都說四爺是個高冷不好女色的人,為什麼她遇見的這貨夜夜找她纏綿,纏的她腰酸腿軟還要被他其他小老婆算計。好不容易熬到宮里升了官還是沒有一天安生的日子。...
90.2萬字8 10230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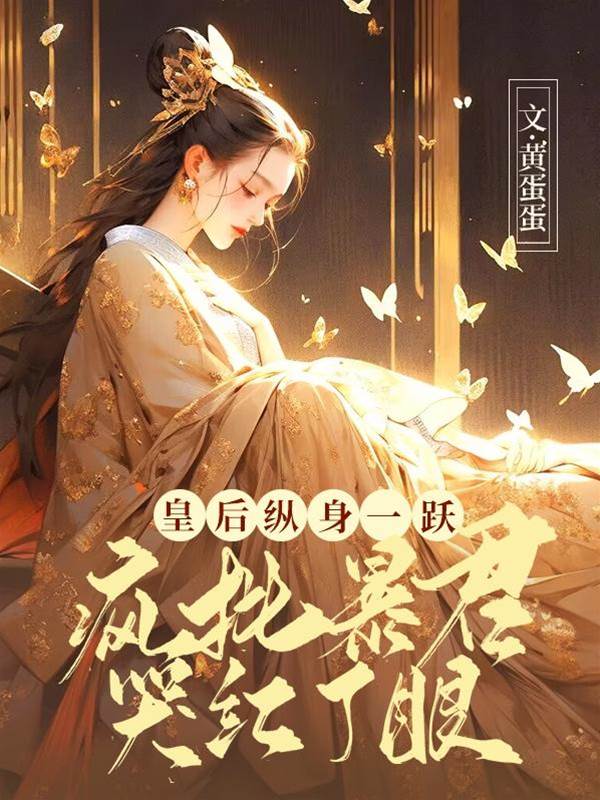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631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49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