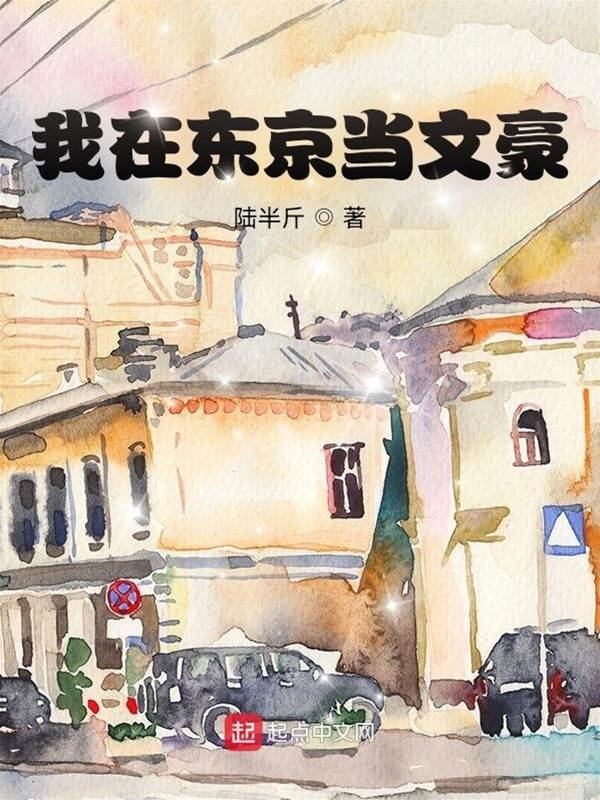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一路高升》 第一百零七章 回家
一聲巨響,裂聲在森林裡迴盪著,可吳放歌並沒有應聲倒下,反倒是葛軍手裡的槍炸開了,數十片金屬片瞬間打進了他的面部和肩頭。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自我保護機制,他在一兩秒鐘之並沒有到疼痛,甚至還地攥著幾乎已經被炸兩截的獵槍發呆,似乎還不敢相信這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然而劇痛還是傳來了,他跌倒在地,痛苦地哀號著,兩用力蹬著,扭著,卻依舊不能把那痛苦減輕分毫。
阿梅和葛學隨後趕來,撲向倒在地上的兒子。阿梅回頭對著正在趕來的珍妮喊道:“快回房裡去,看好孩子,報警救護車啊。”
“救護車已經喊了。”吳放歌舉著手機說“他會活下來的。”
“吳!放!歌!”葛學很快從最初的錯愕中清醒過來,他站起來一步步走向吳放歌,一把揪住他的襟,怒吼道:“你到底想幹什麼!~你到底想幹什麼!”
吳放歌不不慢地說:“我只是來告訴你們,不要再來惹我,只要你們不來惹我,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活下去。”
葛學回頭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兒子,咬著牙說:“你管這也平安?他和這事沒關係,全是我的錯,你要幹什麼就衝我來吧!”
吳放歌說:“他只要不向我開槍就沒事,現在你可以鬆開我了。”他說著,用手彈彈葛學的肩頭,就好像那裡有灰塵一樣,後者扭頭一看,發現那裡有一個紅點兒,這是遠程步槍上的瞄準裝,他心裡一冷,無奈地鬆開吳放歌說:“你會遭報應的。”
吳放歌笑了笑說:“你說了不算。”說著整理了一下領,扭頭就走。
Advertisement
葛學在後面問道:“你去哪兒?”
吳放歌站住腳步,卻沒有回頭地說:“回家。以後我們都不會再見面了,除非你們還不肯放過我。”他說著,又往前走去,很快就消失在樹林裡了。
吳放歌快速來到第一個接應點,那裡有一輛車一直在等著,開車的是阿竹。吳放歌上了車說:“行了,我們去接一靈吧。另外,你真不去看看咱們老同學?”
阿竹一邊發車子一邊笑著說:“想去啊,可現在是徹頭徹尾的葛家的人了,和我不搭界啊。”
車開到第二個接應點,穿著戰鬥服的任一靈也上了車,一上車就笑著說:“哎呀,還真冷。”邊說,邊把槍拆了,放回到槍箱裡,然後開始服,正著,卻覺得有些異樣,再一看原來是吳放歌正直勾勾看著,就罵道:“看什麼看!跟你說啊,現在不比當年,我們可是有各自生活的人!”說完,彷彿是爲了佐證,就對開著的阿竹說:“阿竹你說是不是?”
阿竹笑著說:“是啊,我們現在只能算是生意夥伴了,別的事來打我們主意。”
吳放歌也笑著說:“你們還真是越來越值錢了。”
任一靈頭一仰說:“當然,以前我們是年無知才上了你的當。”
“那好吧。”吳放歌嘆了一口氣,把臉扭了過去。
“嘻嘻。”任一靈見他扭過了臉,就笑著開始換服,等換完了,才鬆了一口氣說:“唉……我現在果然已經不適合穿那些東西了啊。”又見阿竹一直壞壞地笑著,就說:“你笑什麼笑?懷了什麼鬼胎?”
阿竹說:“沒什麼啊,我就是再想,你不讓放歌看你換服,是不是怕他看見你的小肚腩啊……不是我說你,你近年來運了,以前六塊腹現在變一塊年糕……”
Advertisement
任一靈聽了張地朝吳放歌那兒看了一眼,說:“哎呦我的姑,住吧。”
阿竹於是得意地笑了起來。
任一靈張過去,忽然又覺得有些不對勁,因爲不管怎麼說:“剛纔阿竹說的那番話,吳放歌怎麼也得有些反應纔是啊,不可能悄沒聲的就過去了。於是又說:“放歌,你可別聽阿竹胡說八道……放歌,放歌……”連喊了幾聲,吳放歌都不答應,這才慌了,忙喊道:“阿竹啊,放歌會不會是又犯病了啊。”
這一嗓子,把阿竹也嚇著了,一個急剎車後爬到後座來抓起他的胳膊,覺得的,這才鬆了一口氣,打了任一靈一下說:“你嚇鬼啊,他睡著了。”
任一靈著口說:“有這麼快嘛。”說著又搖晃了一下吳放歌問:“放歌,你要睡著了就說聲啊,我害怕……”
阿竹一把把任一靈推開說:“你白癡啊,睡著了能說話嘛,讓他睡吧,他這幾年都沒睡好過。”說著鼻子有點發酸了,爲了掩飾這一點,又責怪任一靈說:“你咋搞的嘛,堂堂好萊塢大牌作設計,剛剛還信誓旦旦的說要開槍打幾個人玩玩,怎麼一下子變的跟個小人似的一驚一乍的。”
任一靈委屈地說:“你還不知道我啊,我一到他面前,就是小人嘛。”
阿竹一邊往駕駛座上爬一邊說:“都四十多歲的人了,還小……哼。”
不過總算是虛驚一場,阿竹和任一靈又開車到了下兩個接應點,先後換了三輛車,總算在天亮後不久順利的出了加拿大邊境,進了國境。
在國,他們最後換了一輛車,這是一輛小型的房車,用做長途旅行那是想當的舒適。不過多虧了有任一靈在,的力氣很大,因爲吳放歌睡的跟個死人一樣,幾次換車多虧了任一靈扛著。都說不如新人不如故,要是沒有這兩個故友,吳放歌縱有天大的本事,還真的有點玩不轉呢。
Advertisement
吳放歌醒來時,見窗簾外大亮,知道已經是白天,舒適的牀鋪微微著,從前面還傳來發機的聲音。
“原來我在房車上啊。”他試著了一下,覺得全綿綿的,用不上半分力氣,可這時他有兩急,一個是他真的很想上廁所,二一個是他真的好,要命的是一油煎罐頭的味道隨著刺啦刺啦的煎炒聲從隔簾外傳來。於是他力爬了起來,打開隔簾,卻看見阿竹正在廚臺上做飯,做的飯算是中西合璧了,有紅的罐頭,翠綠的蔬菜,白生生米飯上撒著剁碎的紅辣椒,讓人看著就有食慾。
阿竹一回頭看見吳放歌笑道:“我的老大啊,你整整睡了……”說到這裡,看了一下表“整整三十二個小時啊,我還以爲你會就此與世長辭了呢。”
吳放歌往前面一看,開車是任一靈,於是也不說話,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後著就想往阿竹的臉上親,阿竹一把推開他說:“去去去去!你忘了,咱們現在可是各有各的生活啊,順便提醒你,我們這次豁出名譽地位幫你,可不是白幫呢,回去就給我們把權證明給簽了。”
吳放歌沒親著,可也不生氣,轉頭進了廁所,這一進去就是足足的二十分鐘,這才全清理乾淨了。出來時見阿竹已經把牀鋪重新收拾了沙發客廳,飯菜已經擺好了。
見吳放歌出來,阿竹又笑著說:“這麼久啊,我還以爲你在裡頭又睡著了呢,一靈都想破門而了呢。”
“哼,我才懶得管他了呢。”開車的任一靈說。
吳放歌坐在沙發上,見面前只有一個餐盤一副刀叉,就問:“怎麼?不一起吃嗎?”
Advertisement
阿竹說:“開始是我開車,一靈看見你在翻了,就猜出你要醒了,我這纔過來做飯的。我們吃飯的時間還沒到呢,你吃吧,都是你的。”
吳放歌確實了,也不再客氣,馬上就來了個風捲殘雲,連吃了兩盤後才著肚子說:“哎喲,活過來了。”
阿竹笑著說:“活過來了就去洗碗。”
吳放歌眼睛瞪的老大:“還得洗碗啊。”
阿竹說:“當然了,我們倆伺候了你這麼久,你也該自己做點事了。再說了,你吃了這麼多,不得活活啊。”
吳放歌沒轍,只得去洗盤子,洗完了以後又了個懶腰說:“哎呀,要是能洗個熱水澡就好了。”
阿竹嗔道:“不知足!不過再往前,晚一點我們就能到房車營地,那裡有公共浴室的。我們可以在那兒休整一兩天,然後就可以回家了。”
吳放歌往沙發上一躺,四肢的長長的,又出了一口長氣說:“是啊,可以回家了。”
當晚到了房車營地,先去公共衛生間把房車的廁所清理了,回來時正好遇到一羣快活的國人在搞燒烤會,其中有個認出了任一靈,喊道:“嗨,那不是《功夫監獄》的作導演嗎?”
吳放歌笑道:“一靈,你可是大明星啊。”
阿竹撅著說:“國人真好糊弄,一部三流功夫電影的作導演居然也有……&”
可不管三流還是四流,那羣國人很熱地邀請他們參加燒烤,有道是人在旅途,盛難卻,而且順便把晚飯也解決了。不過吳放歌也確實看出了阿竹和任一靈的本事,不到一兩個小時,阿竹就和一個看上去大約只有二十三四歲的金髮國小夥打得火熱,而任一靈也開始和一個栗頭髮,滿臉雀斑的孩子勾肩搭背的跳那種很親的面舞。
“看來真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啊。”吳放歌自言自語地說著,就在這時,一個材高大的黑人小夥子遞給他一瓶打開的啤酒說:“嗨,夥計,你也是拍電影的嗎?你的頭髮可真酷啊。”
吳放歌笑著接過啤酒,到聲謝謝,然後指著自己的腦袋說:“原來是黑的,我希還能變回去。”邊說邊和那個黑人酒瓶相,仰頭猛喝了幾大口,頓時覺得爽快極了。
不過吳放歌之後沒多久就悄悄離開了,因爲儘管之前已經睡了三十多個小時,他還是覺得十分疲憊,於是他回到房車裡,找了些洗漱的東西,去營地的公共浴室舒舒服服的洗了一個熱水澡,出來時,見燒烤那邊還在又唱又跳的,於是笑了笑,在自己回到房車,把牀鋪都鋪好了,自言自語地說:“看來今晚我是可以獨佔這張牀了。”說著,就睡了。
睡到半夜想翻,卻翻不,兩邊都不行,才發現阿竹和任一靈不知道什麼時候都回來了,一的酒味著他睡。吳放歌暗笑,正想起來去趟廁所卻被兩隻手一左一右又給按回去了,就笑著說:“拜託,我上廁所。”
阿竹嘟囔著說:“不準去。”
任一靈也說:“就是,不準去。”
吳放歌說:“拜託,這可是水火不留的事兒,能說不去就不去嘛。”
阿竹說:“就是不準去。”
任一靈沒說話,手上的力氣卻使得大。
吳放歌苦著臉說:“哎呀,總得有個道理吧,不準去。”
阿竹說:“我們倆年輕輕的就被你拋棄到國,一熬就是二十年,從小姑娘熬老太婆,還自帶乾糧給你養兒育,給你做長工,這些債不用還的啊。所以要上廁所,先還債。”
任一靈也說:“就是,別想賴賬。”
吳放歌說:“開頭不是說好了,都有各自的生活嘛。”
阿竹說:“有各自的生活也不能欠債不還啊。”
任一靈說:“是啊,這段時間見你一門心思琢磨著害人,我們才忍著你的,現在事都完了,欠債不還是癩子。”
吳放歌說:“可還是不對啊,你們剛纔不都找著……”
阿竹說:“人命苦啊,其實就是想試試你吃不吃醋,可你這個沒良心,還笑,笑也就罷了,還和黑小子喝酒,我們還以爲你口味變了呢。”
任一靈對阿竹說:“你和他囉唆什麼。”說著手往下一,抓了一個正著說:“還不還?不然就把你銀行戶頭給註銷了。”
吳放歌笑了一下,手,把兩人都摟過來,一人臉上吻了一下說:“我還還不行嗎?不過我正想先去趟廁所了,不然會有嚴重後果的。”
就這樣,吳放歌自打這一夜開始,腳總是覺得綿綿,走路就像是踩了棉花,好在這一路上阿竹和任一靈倒是神煥發,流開車,一路向南,笙歌不斷。隨著越來越靠近南方,天氣也越來越暖和,好像是一個新的季節又來到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64 章
我在古代日本當劍豪
穿越到了公元1789年的古代日本,時值承平日久的江戶時代。開局只有一個下級武士的身份、佩刀、以及一個只要擊敗或擊殺敵人便能提升個人等級與劍技等級的系統。……“遇到強敵時我會怎麼辦?我會拔出第二把刀,改換成我真正拿手的劍術——二刀流。”“如果還是打不過怎麼辦?”“那我會掏出我的左輪手槍,朝敵人的腦袋狠狠來一槍。”緒方逸勢——擁有“人斬逸勢”、“劊子手一刀齋”等稱號的“大劍豪”如此對答道。
331.6萬字8 17550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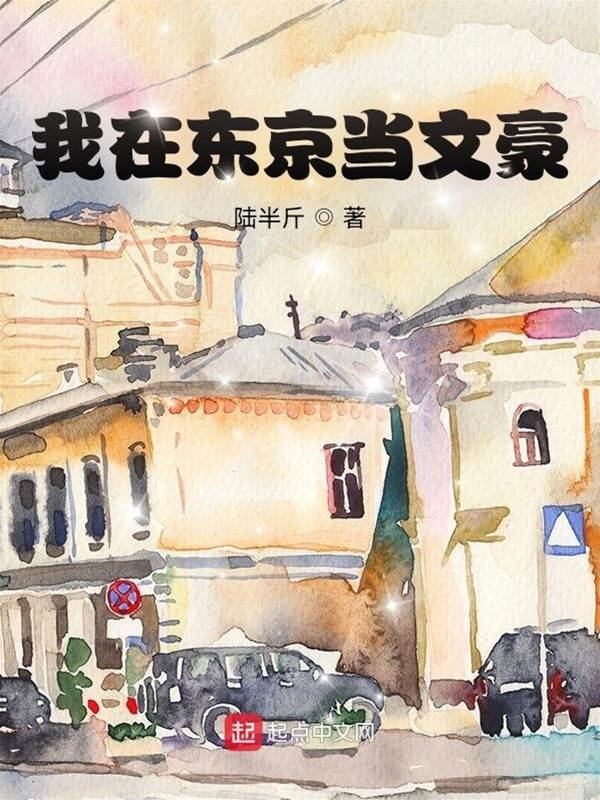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