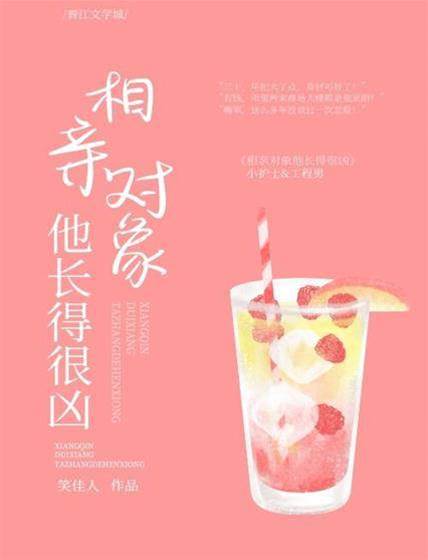《穿到大佬黑化前》 第80章
七月酷暑,烈熾烤大地,路上沙土閃爍地生,酷熱和滿空氣之中,路上行人像是生在巨大蒸籠里的螞蟻一樣,擁又匆忙。
無人愿在這樣的午后停留下步伐,除了時暮。
對時暮來說,暑假是賺錢的好機會。
在夏航一和周植坐上前往老家的火車時,正在街邊擺攤給人算命,看得人很多,都是妹子。
“小哥,你能看出我們之間的姻緣嗎?”
“小哥你看我的眼里是什麼?都是你。”
“一百塊,約會一次要不要?”
“加我微信,給你快樂!”
人是很多,可都不是正經算命的,不得已,時暮重寫了牌子——“賣藝不賣,非誠勿擾”。
人群一哄而散。
時暮旁邊蹲了個要飯的,和坐了一上午,破碗里堆滿了十塊二十的零錢,還有好心人送過的飲料和漢堡。
流浪漢低頭數錢還不忘嘲:“我一個討飯的都知道這套不實行了,你還不如牽個猴兒耍猴戲呢。”
時暮坐的麻,換了個姿勢,“耍猴靠的是技,我靠的是智慧,那不一樣。”
流浪漢呵笑聲,把錢揣回口袋里,“那你有本事給我算算唄,你要是全算準了,我碗里這些錢全歸你。”
時暮勾一笑,“,但我們要找個作證的。”
“那還不好辦呀。”流浪漢上了當,敲敲碗讓眾人視線落了過來,“旁邊小哥要給我算個命,要是準了我的錢給他,要是不準上服給我穿,好心人都過來幫忙做個證啊!”
乞丐和神打賭?
這倒是稀奇了。
一時間商業街的行人圍過一半。
時暮看著乞丐,直接便道:“你死過一個兒。”
簡單幾字,瞬間讓老乞丐變了臉。
Advertisement
時暮又說:“你殺的。”
四周靜寂,接著便一片嘩然。
笑意深了深,“不過還是要恭喜你,以后你都不用再逃亡了。”
話音落下,三名警察開包圍圈,朝老乞丐亮出證件,“我們懷疑你和三年前一起謀殺案有關,請和我們走一趟。”
幾乎沒給老乞丐反應的機會,就被架著離開。
人群之中很是沉默。
時暮盤而坐,雙眼微闔,頗有副世外高人的俗之氣。
很快,反應過來的人群開始爭吵推搡起來,“大師大師給我算一下啊,我今年能考上大學嗎?”
“大師,我人啥時候離婚!”
“大師,我婆婆啥時候死!”
“大師,你能治病嗎!”
“……”
晚七點,在眾人不舍的目下,時暮收攤離開,背著書包低頭數錢,今天收獲盛,現金共賺了兩千,微信轉賬三千不到,四舍五五千有了,照這個速度下去,月十萬不是做夢。假如,是說假如,假如無法完任務,無法離開這個世界,也可以靠著這門手藝賺取買房和上大學的費用。
小心將現金收好后,電話鈴傳來,傅云深的。
猶豫幾秒,時暮接通電話。
“你在哪兒呢?”隔著話筒,年的聲音磁好聽。
時暮說:“步行街呢,正準備坐車回去。”
傅云深語氣停頓,道:“晚上我派人去接你,記得穿我給你帶的那套服。”
還沒來得及問出心中困,電話那頭的傅云深就掛斷了電話。
莫名其妙的。
時暮重新把手機塞回到口袋里后,乘上了剛過來的公車。
到了家門口,遠遠就看到一個黑人在前等候,時暮瞇瞇眼,覺得此人眼,心里一合計,可不就是傅爺家的司機,心里放松,疾步走去。
Advertisement
司機畢恭畢敬把手上袋子送到時暮手上:“這個給您,換好后我送您過去。”
過去?
時暮眨眨眼:“去哪兒?”
司機面無表道:“這個不便。”
傅云深竟搞這些神神的,時暮努努,拿著袋子進了里屋。
他給帶的是一套昂貴的白西裝,面料順,手細膩,時暮皺皺眉,心里有些懷疑,但也沒太多想,畢竟和大佬深厚,犯不著害。
想著,時暮換上了那套服。
這套西裝是為時暮量打造的,裁剪合,袖口別致,襯著那暖白如玉的,如同油畫中俊朗清雋的貴族年。
最后穿上皮鞋,時暮坐上了司機的車。
這段路無比漫長,待天外暮漸進時,兩邊的高樓大廈變了荒野平原,著前方蜿蜒沒有盡頭的公路,時暮總算不淡定了,趴在椅背上問正開車的司機,“還沒到呢?”
司機:“您別急,馬上要到了。”
時暮坐了回去。
半個小時后,天完全黑了,時暮的肚子也了,路面顛簸,有些想吐,按耐不住又問道:“先生,到了嗎?”
司機依舊是棱模兩可的回答:“很快。”
時暮捂著肚子看著車窗荒蕪的景,有些不淡定的想著,傅云深不會是想把帶到墳地埋了吧?
胡思想之時,車子總算停了。
時暮著急就是下車,等看到眼前景時,眼皮子狠狠跳了起來。
無月之夜,不之地,一個個荒廢倒地的破舊墓碑。
這是……
墳地。
了!
傅云深這就是要搞死啊!!
時暮扭頭就要跑,正在此時,沿路的蠟燭亮起來,在殘風中搖曳的細小燭似是鬼火一般,充滿詭異邪氣,蠟燭一直通往小路里頭,時暮看的頭皮發麻,突然聽到后面引擎發,司機竟趁著發愣的功夫揚長跑了!
Advertisement
荒郊,野外,枯墳。
只有一個人的時暮弱小可憐又無助,還很。
咬咬牙,著頭皮向里面走去。
穿過鬼火小路,時暮看到前面放了一張鋪有白桌布的長桌,上面點燃著三角蠟燭,同時還響起了古典樂,那悠揚的音樂在這種夜里聽起來愈發詭異。
時暮全發麻,牙齒都在打著哆嗦。
忐忑中,一個黑影從黑暗出來。
時暮定神看去。
燭火朦朧之下,穿著黑西裝的年拔如樹,那濃的黑發如數抹在腦后,出的五深邃又英俊,那雙狹長迷人的眼正看著,往日充滿冷漠乖戾的眼神此刻變得溫異常。
時暮愣了下,口而出:“你腦袋上抹得啥玩意,油锃亮的。”
傅云深小心翼翼了發,說:“發蠟。”
時暮:“……你抹這玩意干啥?”
傅云深;“帥。”
“……”帥不帥沒看出來,但時暮看出來傅云深腦子出現了點病。
看看左邊又看看右邊,風聲夾雜著烏凄厲的鳴,愈發顯得環境詭異,時暮哆嗦了下子,不由環住臂膀,“你把我這兒干嘛呀?”
傅云深眸閃爍:“約會。”
靜默。
時暮角,“你……和我來墓地約會?”
傅云深說:“請你吃飯。”
時暮;“……你他媽是想讓我骨灰拌飯嗎?”
傅云深搖頭,一本正經道:“我請你鬼魂下飯。”
說著拉起時暮,來到餐桌前,他指著左邊枯墳說,“那個王二,生前壞事做了不,應該好吃;他旁邊是劉寡婦,水楊花的,口可能會膩味,前面埋著劉麻子,村里一惡霸。來前都調查過了,這邊埋的都不是什麼好人,你可以放心吃,這頓我請。”
Advertisement
傅云深一笑,語氣不甚得意:“比那點小鬼干強多了。”
時暮:“……”
傅云深上前揭開了餐蓋,盤子里的牛排看起來鮮香可口,“這是我特意找大廚烹飪的,你應該不喜歡,所以只準備了我的一份。”????
傅云深打開了面前那份,孤零零幾個調料碟,點了幾片菜葉子當裝飾,輕聲說:“辣醬麻醬咸鹽全都有,我原本想給你抓幾只鬼的,可他們都怕我,我一來就全躲了,所以……”
時暮接話:“所以你他媽讓我自己抓?”
傅云深點頭,斟酌片刻說:“自助餐。”
時暮低頭扶額,徹底沒脾氣了。
好端端給弄來一昂貴的西裝,好端端讓坐兩個小時車來這片墓地,又好端端說約會,他媽的兩個大男人約個鬼會!
剛巧,時暮看到一只小鬼從墳頭飄出來,像是要躲,瞇了下眼,上去把鬼抓了過來。
這是只男鬼,三十多歲的樣子,死相不算可怕,就是看起來有些猥瑣,上黑氣很濃,看樣子生前做了不惡。
被抓后的鬼有些驚恐,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抗,時暮就練的把鬼魂擰了四四方方一團,小心把鬼團子放在西餐盤中,撒上調料,圍好餐巾,拿起刀叉開始品嘗。
剛咬第一口,時暮眉頭就皺了起來。
傅云深看向:“不好吃?”
“倒不是不好吃,就是……”時暮里咀嚼著,神復雜,“板藍味的,還是過期的板藍。”
傅云深慢條斯理品著牛排,垂眸斂目,“真可惜我會不到。”
本來是隨口一言,在時暮聽來就是赤挑釁了。
肚子里的兩條蠱顯然也不了這個味道,囂著讓停下,報復心作祟,時暮三口兩口把板藍鬼吃了個干凈,聽到那兩條蟲在爭執。
魅蠱:[最后一口我不吃了,給你吃,你不是最喜歡和我搶。]
纏藤蠱:[是的,我意識到了我的錯誤,你好說也是我前輩,晚輩該給前輩吃。]
魅蠱:[不不不,尊老是蠱蟲的傳統德,給你吃。]
纏藤蠱:[你吃……]
魅蠱沒了耐:[你他媽給老子吃!!]
纏藤蠱也跟著暴躁起來:[你再吼我一句試試,信不信我neng死你!]
魅蠱:[來啊來啊!neng死我啊!有本事我們三個都別活!]
系統:[大家都是一家人,和氣點]
魅蠱:[剛才他媽的什麼東西混進來了,老子不吃這個,你吃!]
纏藤蠱:[我他媽怎麼知道誰混進來了,我纏藤蠱就算是死了,從這里排出去,都不會吃這過期鬼一口!]
嘰嘰喳喳,嘰嘰喳喳,那兩條蟲在時暮的里吵作一團,心煩躁,手上刀叉,暗暗警告:[前面有只屎味的鬼,你們信不信我吃了?再吵大家誰都別好過。]
瞬間寂靜。
時暮深吸口氣放下刀叉,起看向傅云深,“夜也深了,飯也吃了,我看我們回吧,這荒郊野外嚇人的,我們倆穿的這麼好,別給打劫了。”
來了鬼倒是不怕,就怕有壞人劫持他們,就算傅云深再厲害,也搞不過亡命徒,何況擺攤一天早就累了,只想快點回家躺下。
傅云深拿起餐巾慢條斯理了角,看向的眸璀璨,年起,高大的近。
在面前站定后,傅云深行了一個標準的貴族禮:“我能邀請你跳一支舞嗎?”
時暮有些懵:“啥?”
他攤開手掌,重復一遍:“跳舞。”
“……”
[叮!傅云深下達任務“與之共舞”,完任務可獲得隨機值,拒絕不得值。]
時暮是有權利拒絕的,可又舍不下那高額的值,抿抿,忍不住說:“兩個大男人跳舞好奇怪啊,你好端端的讓我和你跳什麼舞?”
傅云深神未變,說:“有法律規定兩個男人不能跳舞嗎?你要是覺得奇怪,可以把我帶的。”
聽到這話,時暮的心重重跳了下,看著年寬厚的掌心,時暮嘆了口氣,緩緩把手了上去,他勾,彎眉,瞬間笑的似得到糖果的孩子。
傅云深握住,把人往懷里一帶,隨著音樂邁開步伐。
被年摟住腰的時暮覺得無比怪異,他好像是噴了香水,不知名的味道,與他往日完全不同,能到他的視線,很灼熱,像晌午的太。
時暮莫名耳滾燙,目落向他,不敢看他一眼。
氣氛愈發詭異了,時暮輕咳聲打破寂靜:“深哥,你今天奇怪的……”
傅云深睫輕,年音緩慢低沉:“那你想知道為什麼嗎?”
時暮道:“你要是愿意說的話。”
他眼神幽邃,瓣微張:“那是因為……”
話音未落,突聽咔嚓一聲,時暮腳下踉蹌,臉難看,結結說:“我……踩到斷肢了。”
也不知道是哪個倒霉蛋的骨頭,風吹雨淋中都快風化了,結果就被踩到了。
時暮看了看腳下,默默往后退了一步,“深哥,這就是傳說中的墳頭蹦迪吧?”
傅云深沒說話,時暮直覺他有些不滿,抬頭忙把話題轉移了回去:“你剛才要和我說啥來著?”
傅云深凝視著時暮,目深邃又專注,“我……”
時暮細細聆聽著。
猜你喜歡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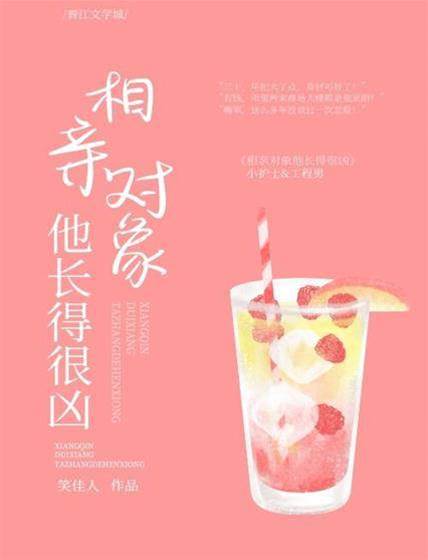
相親對象他長得很兇
江桃皮膚白皙、面相甜美,護士工作穩定,親友們熱衷為她做媒。 護士長也為她介紹了一位。 「三十,年紀大了點,身材可好了」 「有錢,市裡兩家商場大樓都是他家的」 「嘴笨,這麼多年沒談過一次戀愛」 很快,江桃
20.8萬字8.57 43724 -
完結120 章

唯一奢望
桑梨性格溫順如鹿,高三那年,母親去世,孤單無依的她被寄養到鄺家讀書,第一次遇到鄺野。少年野蠻生長,出了名的壞,學校里許多女生愛慕卻不敢靠近。母親叫他多照顧桑梨,少年抬頭掃了眼恬靜的小姑娘,輕嗤:“我懶得管她。”誰知一段時間後,她在校門口遇到麻煩,差點被打,向來冷淡的大少爺卻破天荒擋在她面前。桑梨見過少年各樣的叛逆,後來也見過那晚雨夜,他單單註視著她:“桑梨,我喜歡你,無比認真確定。”他在她面前最壞,也只被她馴服。畢業典禮當天,鄺野當眾給了桑梨一雙舞鞋:“送給我女朋友的。”他高調公佈倆人的關係,全校轟動嘩然,無人的槐樹下,她踮起腳尖吻他左耳,鄺野拉住她,唇角弧度明顯:“追到了,別想賴賬。”
61.3萬字8 26586 -
完結167 章

全娛樂圈都以為我是嗲精
楚皙作爲娛樂圈著名白蓮花,臉是最美的,性子是最嗲的,黑粉是最多的,據說連背後捧她的神祕大佬,都是最有錢的。 直到她收到一張絕症診斷書。 楚皙以爲處了兩年好歹也有感情,眼淚巴巴地去找大佬訴苦。 哪知那人看到她的淚水輕蔑一笑,隨手撕掉她的診斷書:“收起你假惺惺的眼淚,我們從來不談感情。” —— 楚皙背後有人是圈裏衆所周知的事情,可最近楚皙資源一落千丈,形象跟以前大相徑庭,甚至在綜藝節目爲了博出位徒手劈磚,小白花形象瞬間破滅。 於是全娛樂圈拍手稱快楚皙終於被甩了,虛僞白蓮花終於暴露本性被神祕大佬一腳踢開。 直到某次片場,有羣演拍到楚皙的吻戲用的是替身。 而當事人楚皙,正被那個神祕大佬冷着臉從片場拖走,然後掐着腰,按在牆上親。
25.9萬字8 6676 -
完結187 章

惹春舟
【她曾是他的白月光,紅綃帳裏,也終被他揉成了唯一的硃砂痣……】 暮雲舟作爲大魏的亡國公主,被她無恥的父皇送給了那攻入都城的北燕渤陽王做禮物。 可是傳聞中,渤陽王蕭錚,少年掌兵,戰無不勝,是讓人聞風喪膽的殺神,且在大魏做世子時飽受魏帝折辱,對大魏王室恨之入骨。 哪個魏人提起他不恐懼地瑟瑟發抖? 柔弱無助的前朝小公主心懷忐忑的的被送到了渤陽王的寢殿…… 當蕭錚問起時,卻被下人告知:“殿下,那魏女她暈過去了……” “……” * 後來,幽暗的寢殿中,蕭錚身着玄色龍袍縛住她的雙手,他雙目通紅,咬牙切齒:“在別的男人身邊你就不要自由了?” 她氣得毫不猶豫就賞了他一記耳光…… 而那不可一世的渤陽王抹掉嘴角的血,眸色暗沉地冷笑一聲:“暮雲舟,你長本事了。” * 再後來,紅羅帳裏,她被欺得狠了,裹着被子,紅着眼角,露出軟玉似的肩頭,嗚嗚咽咽地嗔道: “我做公主的時候……你一個世子……敢如此褻瀆於我……定要砍了你的腦袋……” 那作亂之人卻低低笑着:“你捨得嗎?我的公主殿下……” * 沒人知道,那權傾天下的帝王心裏有一輪小月亮,那是他暗無天日的世子生涯中唯一一束光亮。 他遣散了所有進獻的美人,只留下她。 可嬌美的月亮想逃,他怎能不將她奪回來? * 天下臣服於君,而君王他臣服石榴裙。
29.2萬字8.18 6999 -
完結311 章

弄薔薇
舒清晚和容隱曾有過一段 但她清楚,他們之間差別太大,不可能有結局 在圈裏盛傳他的白月光回國之時,她放手離開。 - 回國之後,作爲國內熱度正盛的非遺傳承人,又被爆出那段火過很久的旗袍視頻就是她 玉骨軟腰,穠麗清絕,舒清晚的熱度一下子爆到最高 採訪中,在談起曾經的戀情時,她沒有避開,只是笑道:“是他教會我免嗔癡、早悟蘭因。” 那日他就在當場,親眼看着她說出每一個字 她跟在他身邊許多年 可他教的明明是當貪嗔癡,當貪深欲 —— 舒清晚是林家丟失多年的女兒,尋回之後,父母自覺虧欠她良多,待之如珍如寶 他們見兒子一場戀愛接一場地談,女兒卻始終單身,特意給她安排了一場相親 對方能過她父母的眼,自然百裏挑一 她覺得試着談上一場好像也沒什麼 卻在她落定主意的功夫,容隱忽然出現,與她道了一句:“好久不見。” 男人矜貴淡漠,卻氣場迫人。中途攪局,強勢的掠奪感和佔有慾於那一刻盡數顯露 *他親手澆灌的玫瑰,當然只能爲他盛開 【小劇場】 容隱是出了名的禁慾冷淡,他有一處深山別墅,經常往裏一待就是數月,好友皆知 卻是突然有傳聞說他那深山別墅另有玄機 他哪裏是擱那兒修身養性,裏面分明是藏了心頭白月光! 風聲越傳越盛,一衆好友也心癢難耐,終於決定趁他不備一探究竟 計劃十分順利,所有人成功探入 可他們沒想到,這一場夜探挖出來的不是什麼白月光,而是不知爲何消失多日的—— 看見拈裙赤腳跑下樓的人,有人愕然:“清晚?!” - 容隱見過她最愛他時的模樣 也見過她不愛時的那一句:“容先生,我總是要結婚的。” 「我見烈焰,起於孤山」 後來。 她是他的無條件愛人。
46萬字8 312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