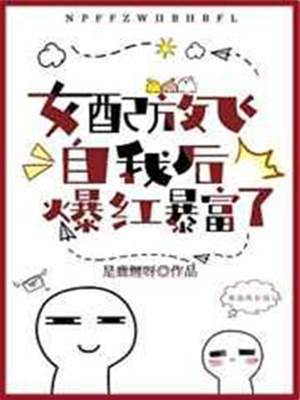《成何體統》 第 71 章節
半,他們可是原作里為你而死的人啊!”
夏侯澹:“端王怎麼找到你的?”
這句話問得沒頭沒尾,庾晚音混之中,過了兩秒才明白他言下之意:“肯定是他的探子在滿城搜尋,不可能是暗衛泄的。暗衛里如果有,端王一早就會知道我們有槍,還有更多更大的,你我早就不戰而敗了!”
夏侯澹不為所:“這種勢下帶你出宮,與何異?”
庾晚音:“……”
庾晚音后知后覺地明白了。夏侯澹這怒火所指,并非那些暗衛,而是自己。
自己忤逆了他,背著他跑出宮去,還險些讓端王打探到己方機,毀了大事。
但他不想殺。
不過,就必須有人替過。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對方連思維模式都如此契合上位者的份了。又或者不是沒有察覺他的轉變,只是在一次次自我安中視而不見罷了。
夏侯澹是悉的那個世界的最后一塊碎片、最后一縷牽念。但世界早已面目全非,沒有人可以一如既往。
庾晚音深吸一口氣,跪了下去。
夏侯澹原本在拖著走路,此時突然一跪,終于讓他放了手。
冬夜的地磚早已凍了,剛一接膝蓋,寒氣就兇殘地侵進了皮。但庾晚音已經覺不到冷了。垂著腦袋,低聲下氣道:“此事因我一人而起,求陛下饒過暗衛,責罰臣妾。”
只能看見夏侯澹站立不穩似的倒退了半步。
漫長的幾息之后,頭頂傳來他的聲音:“可以。”
他吩咐宮人:“將庾妃關進寢殿,落鎖。從今日起,直到朕死的那一天,不得放外出一步。”
庾晚音沒有抬頭,聽著他的腳步漸漸遠去。
Advertisement
宮人俯攙起:“娘娘,請吧。”
如同行在云端,茫茫然被攙進了殿門。落鎖聲在后響起,宮人懼于夏侯澹的雷霆之怒,無人敢跟進來,鎖上門就遠遠避開了。
偌大的寢殿從未顯得如此空曠。庾晚音背靠著門扇,呆呆站著。
腦中千頭萬緒攪一團麻,一時覺出手腕鈍痛,一時擔心暗衛有沒有獲救,一時又想起岑堇天等人,不知道端王會不會回頭去找他們麻煩。
夏侯澹聽說此事后,派人去保護他們了嗎?他會不會認為岑堇天左右都要死,會不會覺得一個失去價值的紙片人,死了也就死了?
以前的不會這樣揣測他,但現在……
庾晚音回敲門:“有人嗎?我有要事!”
喊了半天,毫無回音。
寢殿里燃著地龍,庾晚音卻還是越站越冷。走到床邊,一頭栽倒下去,鴕鳥般將臉埋進了被子底下。
就在今天早些時候,他們兩個還在這里,你一言我一語地吐槽奏折。
口仿佛破開了一個空,所有緒都了出去,以至于能覺到的只有麻木。
不知過了多久,忽然傳來了開門聲。
一驚而起,向門邊:“北叔。”
北舟手中端著木盤:“我來給你送飯。”
庾晚音連忙跑過去揪住他,生怕他放下晚膳就走:“北叔,岑堇……”半途改口,“蕭添采和爾嵐對陛下還有大用,端王或許會找他們麻煩……”
的重音放在“有大用”上。
北舟聽出了對夏侯澹的看法轉變,嘆息一聲:“軍辦事周全,去救你的同時也轉移了岑堇天等人。晚音,今晚的事,是澹兒有錯。你生死未卜那會兒,他差點瘋了。”
庾晚音愣了愣。
Advertisement
北舟:“他當時下令,無論端王的馬車行到哪里,只要你沒有平安下車,就當場誅殺端王。那端王每次行,暗中都不知帶了多人手,軍卻是倉促集結,若真打起來了,勝負都難測。軍領頭的勸了一句,險些也被他埋了。”
庾晚音沉默片刻,問:“北叔,他剛才的樣子,你以前見過麼?”
北舟想了想:“他那頭痛之疾你也知道,發病時痛得狠了,就會有點控制不住。不過他怕嚇著你,這種時候都盡量不見你的……所以他這會兒也沒來。”
庾晚音:“那他這種況,是不是越來越頻繁了?”
晚膳最終一口都沒。庾晚音在床上,起初只是閉眼沉思,不知何時陷了不安的淺眠。
做了一個怪夢。夢中的夏侯澹被開膛破肚,倒在泊里。兇手就站在他的尸旁邊,面帶微笑。
那兇手明明長著與他一模一樣的面容,夢中的卻清楚地知道,那是原作中的暴君。
暴君笑著走向:“晚音,不認得朕了麼?”
說著出手來,將一顆淋淋的心臟捧到面前。
耳邊傳來細微的靜,庾晚音猛然驚醒過來,卻忍住了睜眼的作。剛才夢中的畫面太過清晰,就連那份恐懼都原封不地侵襲進了現實。
除了恐懼,還有一份同等濃烈的緒,一時來不及分辨。
腳步聲漸近。
搖曳的燭過薄薄的眼簾,照出一片緋紅。
緋紅又被人影遮蔽。夏侯澹坐到床邊,低頭看著。
庾晚音雙目閉,越是試圖平復心跳,這顆心就越是掙得震耳聾,似乎打定了主意要出賣。
猜不出對方現在是什麼姿勢、什麼表。他的瘋勁兒過了沒?離得這樣近,如果他再做出什麼驚人之舉,毫無逃的余地——盡管他至今沒有真的傷害,但剛才那狂的殺氣足以隔空撕碎一個人。
Advertisement
庾晚音暗暗咬牙。
不愿醒來,不愿與他四目相對。怕在那張悉的臉上看見一抹妖異而殘暴的笑,怕他眼中投映出夢中的鬼火。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床邊沒有毫聲響傳來。
庾晚音僵持不下去了。就在妥協睜眼之前,腕上一冷,激得眼睫一。
一只泛涼的手托起了的手腕。燈影移近,夏侯澹似乎在查看的皮。
他的指尖拂過腕間某。那地方已經鈍痛很久了,庾晚音反應過來,是端王鉗制時留下了淤青。
夏侯澹可能錯以為是自己傷到了。因為他指尖的作很輕,太輕了,甚至帶來了些許刺。
接著那指尖離去,又落到了的頸側。
那是端王啄過的地方。
庾晚音心中一。那王八羔子居然刻意留下了印記!
夏侯澹的手指慢了下來,仍是若即若離地與相,涼意洇了頸上的。
庾晚音連呼吸都屏住了,完全預料不到對方會是什麼反應。
黑暗籠罩下來,遮蔽了過眼簾的微。夏侯澹捂住了的眼睛。
他的手是冷的,卻還溫熱。
庾晚音在他的掌心下睜開眼。
這回不用刻意回避,也看不見他的臉了。但這一吻中的留之意幾乎滿溢出來,是故人的氣息。
仿佛一場幻戲落幕,白堊制的假面迸裂出蛛網紋,從他臉上一片片地崩落,墜下,碎齏,出其下活人的皮。
夏侯澹吻了片刻,沒得到回應,慢慢朝后退去。
庾晚音一把扣住他的手,用力按著它,在自己眼前。
指節發白,指甲都嵌進了他的手背。
夏侯澹垂眸著,想從出來的半張面龐判斷的表,手心卻到了意。
Advertisement
“……別哭了。”
庾晚音的淚水無聲無息地涌出,狠狠從牙里出一句:“我也——不想——”
恍惚間想起了方才從夢中帶出的另一份緒,原來是憤怒。
明明下了抗爭到最后的決心,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片天地扯開他的膛,刨出他的心肝。
恨他變得太快,也恨自己力不能及。
還恨淚腺不聽使喚。
拼命想將弱的淚水憋回去,憋得臉都漲紅了。
夏侯澹不回手,聲音帶上了一無措:“別哭了,是我理得不對。暗衛沒事,誰都沒事。不會關你的,剛才氣急說了渾話,我轉就后悔了……晚音?”
庾晚音搖搖頭:“不是,是我不該出宮。”
終于松開了他的手,坐起來面對著他:“我錯估了形勢,險些釀大禍,還牽連了別人。”
“也沒有……”
“還害了你。”庾晚音悲從中來,“你剛才好像要撕碎什麼人,又像是自己要被撕碎了。那時候你到底到哪兒去了?我是不是把你又往暴君的方向推了一步?”
夏侯澹:“……”
他的三魂七魄都被這個問題搖撼得晃了幾晃。
是了,看在眼中,原來是這麼回事。
在苦苦阻止一樁早在十年前就發生了的事,如水中撈月,傷心絕地挽留著一抹幻影。
所有妄念如迷障般破除,轉而又織就新的妄念。
夏侯澹毫不猶豫,結結實實地擁抱住:“沒有。我又回來
猜你喜歡
-
完結325 章

攝政王冷妃之鳳御天下
不可能,她要嫁的劉曄是個霸道兇狠的男子,為何會變成一個賣萌的傻子?而她心底的那個人,什麼時候變成了趙國的攝政王?對她相見不相視,是真的不記得她,還是假裝?天殺的,竟然還敢在她眼皮底下娶丞相的妹妹?好,你娶你的美嬌娘,我找我的美男子,從此互不相干。
62.7萬字8 16060 -
完結8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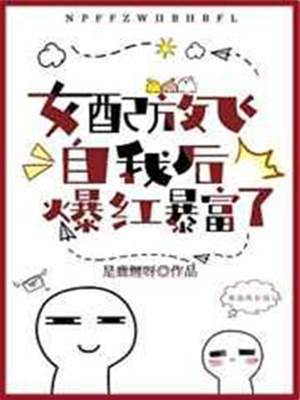
放飛后女配在求生綜藝爆紅了
第五次重生后,作為一本娛樂圈文里的墊腳石女配,白言蹊決定開始擺爛。 為了會被女主剝奪的演技兢兢業業拍戲?為了未來屬于女主的公司勤勤懇懇工作?為了讓女主踩著上位任勞任怨維持人設? 不如放飛自我,直接退圈回家繼承千億家產! 于是…… 當江嬈撞進某影帝懷里,影帝怦然心動時…… 白言蹊拔了顆楊柳,輕松掰成了兩截。 震驚的影帝:……燒火不用愁了? 當江嬈清清嗓子,準備驚艷全場時…… 白言蹊哼著小調,順手按住了蟒蛇七寸。 驚呆的歌手:……午飯有著落了? 當江嬈憤憤離開節目,靠著后臺搶占資源,狂發演技碾壓通稿時…… “白言蹊 最年輕首富”沖上熱搜第一,哥哥弟弟全都悔不當初,路人粉絲紛紛哭嚎認媽。 江嬈咬牙切齒:不可能!她明明將她的氣運都搶走了! 白言蹊欲哭無淚:怎麼不僅沒糊,反倒名聲越來越大,甚至連公司都蒸蒸日上了? 她只想回家躺平,不想白天拍戲晚上兢兢業業當社畜啊! #全文架空,純瑪麗蘇,不喜誤入#
25.2萬字7.91 8498 -
完結167 章

皇家第一廚
一朝穿成大慶朝一枚奶娃娃,云照才剛剛享受一年清閑舒適的日子,當兵的爹爹不寄銀子回來了!他和娘親、哥哥沒有收入了。眼看著米缸一天天地見底了,他決定出手……許久之后,當兵的爹爹看著拔地而起的云家酒樓,驚的說不出來話,好一會兒,看著一群孩子中間的…
43.9萬字8 26856 -
完結354 章

冒牌皇妃:王爺請指教
身穿異世被下套,路邊拽個王爺當解藥;一盒種子一條狗,大街小巷橫著走;冒認首富家的大小姐,乖張不馴;被賜婚給鐵面冷血的王爺,旁人都以為她會稍有收斂,哪知道王爺卻將她寵上了天。洛安安覺得,自己這一生,算是開了掛了,卻沒想到有朝一日,人人都以為已經死了的洛大小姐竟滿血復活!“王爺,正牌回來了,臣妾該讓位了。”某女起身,悻悻穿衣。不料某王一把將她拽回,“本王娶的,從不是什麼洛大小姐。”而是她,洛安安……
83.4萬字8 13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