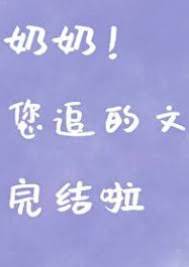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他怎麼可能喜歡我》 第14章 他
孟疏雨和周雋拉扯了個來回,在這場力量懸殊的較量里敗下陣來。
知道周雋是因為還在后才想把戲做完,可他周家的火是滅了,沒見孟家的火越燎越旺了嗎?
兩相對的靜默里,幾步之遙的前方,簡丞白著張臉,死死盯著兩人握的手一不。
孟疏雨眼神飄來飄去沒個落點,覺掌心全是滾燙黏膩的汗,繼續保持這個姿勢下去,的手可能都快融化泥了。
求求了,周雋也行,簡丞也行,誰開個口結束這個場面,行行好救救吧。
度秒如年的十幾秒過去。
周雋扣在孟疏雨掌緣的拇指輕輕挲了兩下,牽著走上前去,和簡丞打招呼:“過來查房?”
簡丞的目終于從兩人的手移開,移到了周雋泰然自若的臉上。
再看了眼偏著頭不看他的孟疏雨,簡丞眼神黯了黯,對周雋僵一笑:“嗯,今晚我在,幫你看著點。”
“謝了,”周雋拎了拎右手的盒飯,“我先吃個飯。”
“好,沒地方可以去我那兒的休息室。”
兩個男人在這簡短的對話里達了默契,一致把孟疏雨當了不存在的明人。
再次邁開的時候,孟疏雨仿佛失去了自主行力,提線木偶似的被周雋一路拖著往電梯走。
直到過了拐角,周雋手一松,也像了力,眼睛一閉,額頭重重靠上了電梯門邊的墻。
像個面壁思過的樣子。
周雋摁了電梯下行鍵,在后看了一會兒,并攏中指和食指點了點的后背。
“你別跟我說話……”孟疏雨低頭定定地盯著自己的鞋面,聲音帶著點哭無淚的腔調。
“抱歉。”
孟疏雨緩緩抬起頭來。
“朋友鬧脾氣,我們坐下一趟吧。”
Advertisement
“……”
孟疏雨眼看著電梯里的乘客不耐煩地摁了關門鍵,才知道周雋剛剛是在提醒,電梯到了。
而那聲讓容抬頭的“抱歉”也不是對道的。
幸好現在這種程度的尷尬對來說本宛如雨,不值一提。
電梯門重新合攏,孟疏雨不太高興地看著他:“戲都演完了就別瞎了好吧。”
周雋抬了下手:“剛才那是和我爺爺同一位主治醫生的病友。”
“……”
那我還要夸你一句嚴謹是不。
孟疏雨泄了氣,眼神空地盯著空氣喃喃:“我上你就沒有過好事。”
周雋回想著點點頭:“好像是。”
“不是好像,就是。”
“那你就沒想過原因?”
“我倒霉我還要反思自己?你這說的是人話嗎?”孟疏雨瞪大了眼看他。
周雋扯了下角:“說不定是你哪時候欠的我。”
是,上輩子一定一時沖殺了這個毫無同理心的男人,欠了條人命債,這輩子才要在他這兒活來又死去,死去又活來。
“周總,我知道您這人緒不多,但這種狀況,”孟疏雨比了個一丁點的手勢,“您可不可以稍微對我有那麼一點愧疚呢?”
“可以,”周雋點頭,“今天是我欠你一次。”
欠一次,果然是凡事按斤兩計算的資本家作態。
孟疏雨沒有從他的表和語氣里會到一一毫的真實意,撇開頭向窗外:“算了,要你的欠條有什麼用,我還是先想想怎麼收場吧。”
“用不著你想,我來收。”
“他打算怎麼收場?”
晚上八點,陳杏在餐廳里追完連續劇最新一集,對著孟疏雨笑了足足兩分鐘,終于問了句正經的。
孟疏雨沒打采地趴在餐桌上,里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蹦:“他說,他去解釋,實話實說。”
Advertisement
“那你還擔心什麼,簡丞作為醫生多理解這種生老病死的事,肯定相信你是在幫忙。”
“嗯,如果周雋沒有在簡丞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過我——”孟疏雨眨了眨眼,“寶、貝、兒的話。”
“簡丞那天肯定沒認出周雋的聲音啊,不然今天看到你們還能這麼驚訝?”
“那現在一回想,不就全對上了嗎?”
“那我也編不出理由安你了,”陳杏給倒了杯水,“多喝熱水吧。”
孟疏雨握過水杯,機械地小口小口喝著。
其實如果今天這個人不是周雋,這事也沒什麼,分手以后找新歡多正常,更何況和簡丞都不算在一起過。
但偏偏一來周雋是簡丞的多年好友,二來周雋和認識的契機還是因為——周雋搭了簡丞的車。
加上當初為了封周雋的口,三番兩次和簡丞打探過報,本來就引起過簡丞的懷疑。
要是把這些事從頭到尾一串連,在簡丞看來,這完全就是個——
準朋友通過自己,認識了自己帥氣多金的好兄弟,火速移別提出分手,和自己好兄弟無銜接的故事。
陳杏也想到了這層,嘆了口氣說:“你要真和周雋談了吧,挨人簡丞一記白眼倒也不冤,可你談還沒談上,鍋先背上了,你說你虧不虧?”
“我可不就是虧死了嘛!”孟疏雨“垂死病中驚坐起”似的直起。
“所以現在不管周雋那邊怎麼理,這疙瘩總歸是留下了,你要想彌補損失呢,只有一條路。”
“什麼路?”
“和周雋走上路。”
“……”
“你別這麼無語地看著我呀,這一不做二不休的,好歹不冤不虧了不是?”
孟疏雨木著臉看:“陳杏,認識你這麼多年,我怎麼才發現你還有搞傳銷拉皮條的天賦?”
Advertisement
“就因為咱倆認識這麼多年,我才敢打包票,如果你和周雋沒那麼多飛狗跳的事,有個正常的邂逅,這男人站你面前,就絕對是你一見鐘的菜。你就說,人家你寶貝兒,你朋友,還有牽你手的時候難道你沒一點心?”
“那,那不都是正常的生理反應。”
“所以當初你聽簡丞講甜言語,或者和他肢接的時候,也有這生理反應咯?”
“。”
“這就對了,”陳杏拍了拍桌,“男人的可能會撒謊,但人的就是要比男人誠實得多。”
孟疏雨拿起公筷,夾了個水晶蝦餃一把塞進陳杏里:“行了行了吃你的吧。”
陳杏被迫閉了,嚼著食嗚哩哇啦了一陣,瞟見孟疏雨手邊的手機屏幕亮了起來。
孟疏雨拿起手機,看到了一條命令式的消息:「過來接我。」
三院附近咖啡店。
周雋和簡丞面對面坐在一張咖啡桌上,從坐下開始已經沉默了整整五分鐘。
像有一形的線在兩人之間拉扯,但誰都不去做那個把線挑明的人。
夜里的咖啡沒那麼俏,店里顧客不多,服務生很快端了兩杯咖啡過來,招呼兩人慢用。
也打斷了這場誰先開口誰就輸的拉鋸戰。
簡丞握起咖啡杯,低頭抿了一口。
酸,讓人生理地皺起眉頭,有些不容易說的話也就順吐了出來:“你跟……”
“還沒在一起。”周雋接了話。
“老人家一直盼著我早點家,今天幫我演了個戲。”
簡丞知道周雋家里復雜的況,也知道他不屑撒這種謊,所以這話應該假不了。
只是——
“‘還沒’在一起的意思是……”
“意思是,我在追。”周雋平靜地看著他。
Advertisement
簡丞沉默片刻,慢慢點了點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以為這種事本來就沒有先來后到,”周雋笑了笑,像是答非所問,又像是正正答到了點子上,“再說,你也不一定是先來的那一個。”
懸在脖頸上的那把刀在漫長的倒數后終于斬落,聽到這個答案,從當初周雋祝他“Goodluck”起就開始在心底滋長的不安跟著塵埃落定,這一刻,簡丞反倒有了一種解的覺。
也是這一刻,他不得不相信,當一個人打定主意想見另一個人,沒有第三人可以阻止。
即使當初,他在第一時間就提高了警惕,努力在孟疏雨和周雋中間筑起銅墻鐵壁,但只要周雋有心,那面墻也不過是一推就倒的殘次品。
時無法倒回,他代替不了周雋,為九年前那個送詩集的人。
或者就算倒回,他能給一個冰淇淋,給一朵花,卻給不了一首詩。
有一瞬間,簡丞差點一沖想告訴周雋,如果是他的話,也許本不用追。
但最后那點私心還是讓簡丞把這句話咽了下去。
夜漸深,天邊濃云翻滾,暗洶涌,一場由夏秋的雨潑墨般傾盆而下。
不過短短兩分鐘,咖啡店的落地窗就打滿了雨水,折出一片片斑駁的影。
簡丞聽著鋪天蓋地的滂沱雨聲,忽然說了句:“我記得你好像很討厭下雨天。”
周雋點點頭著窗外:“以前是。”
話音落下,一聲震響起,周雋看了眼手機,起和簡丞道了別。
簡丞握著手中那杯變冷的咖啡,抬起頭目送他離開。
等周雋走出那扇推拉玻璃門,站定在門外階沿,他忽然猜到什麼,偏過頭往窗外去。
對面的街道上,孟疏雨穿著單薄的襯衫和半,撐了把黑傘穿過馬路,匆匆來到周雋避雨的屋檐下,一臉抱怨地沖他說了什麼。
周雋答了一句,然后朝攤開了手。
孟疏雨沒好氣地把傘柄遞進他掌心。
的臉上全都是簡丞從沒見過的生表。
眼看周雋握過傘柄,和孟疏雨肩捱著肩往對街走去,簡丞一恍惚,好像又回到了周雋和孟疏雨重逢的那個雨夜。
他以為這麼多年過去,周雋早就忘了孟疏雨,所以那天晚上毫無防備地讓周雋搭上了他的車。
那個雨夜,他當著周雋的面帶走了孟疏雨,尚且渾然不知,他們三人當中,除了他以外,還有第二個人知道那是一場重逢。
甚至或許,那本來就是周雋心設計的重逢。
猜你喜歡
-
完結633 章

天價暖婚:司少放肆寵
結婚前夕遭遇退婚,未婚夫不僅帶著女人上門耀武揚威還潑她一身咖啡。池心瑤剛想以眼還眼回去,卻被本市權貴大佬司少遞上一束玫瑰花。捧著花,池心瑤腦子一抽說:「司霆宇,你娶我吧。」「好。」婚後,池心瑤從未想過能從名義上的丈夫身上得來什麼,畢竟那是人稱「霸道無情不近女色」的司少啊!然而,現實——池心瑤搬床弄椅抵住房門,擋住門外的司姓大尾巴狼:是誰說司少不近女色的,騙子!大騙子!!
59.4萬字8 104591 -
完結490 章

嬌妻很大牌:秦先生,你被捕了
夏云蘇懷孕了,卻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誰,她只知道自己的嬸嬸跟別人合謀,要將自己送到其他男人的床上。很快,夏云蘇流產了。她被冠以水性楊花的罵名,卻發現自己的未婚夫搞大了堂妹的肚子。所有人都在奚落她,包括她的母親。直到那個男人出現,用一紙合同逼她…
85.1萬字8 33006 -
完結88 章

般配關係
【先婚後愛 暗戀成真 豪門霸總 白月光 雙潔 HE】【嬌俏傲慢女律師X深情狠厲大老板】為了家族利益,許姿嫁給了自己最討厭的男人俞忌言。在她這位正義感爆棚的大律師眼裏,俞忌言就是一個不擇手段、冷血無情的生意人。何況她心中還藏著一個白月光。婚後俞忌言配合她的無性婚姻要求,兩人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無事。直到許姿白月光回國,許姿開始瘋狂找俞忌言的外遇出軌的證據,想以此為由跟俞忌言離婚。得知俞忌言有個舊情人,許姿本以為勝券在握了,沒想到俞忌言竟將她壓到身下,承認:“是有一個,愛了很多年的人。”“你想要我和她親熱的證據是不是?”俞忌言輕笑,吻住她:“那好,我給你。”
20萬字8 24924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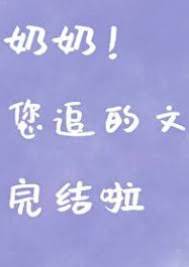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55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