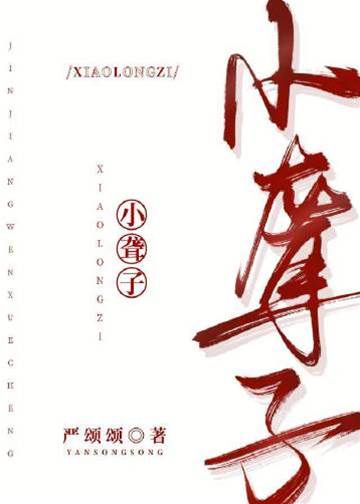《終于不再愛你》 第101章 全文完
邢青鋒做夢了。
他夢到一個火車站,軌道上的火車像是沒有盡頭一樣的長。
火車旁是站臺,站臺上豎立著一個標簽,標注的東西非常模糊,突然他前的車廂門打開,模糊的標簽慢慢變為清晰——1980年。
這節車廂里是個嬰兒,似乎是看到站在外面的他,笑得樂呵,邢青鋒不自覺出手想去,可卻發現有一層擋著,讓他無法逾越一步。
火車啟,又一扇車廂門停在他面前,標簽變為1983年。
這次是一個大概三歲的孩,他趴在門邊眺著什麼,臉上很惶恐,想哭卻又不敢哭,耳邊約聽到男的爭吵聲。
不等邢青鋒做反應,火車又啟了,第三節 車廂打開,標簽是1985年。
這次邢青鋒看到了一大片的海,在海邊的一個小房子里,一個孩子怯生生從窗戶探出半張臉,蒼白的,瘦弱的,突然出現一只手,將那孩子強行拉了回去。
邢青鋒一驚,想去阻止那只手,可車廂門猛的關閉,再次啟。
1987年。
一個男孩穿著短白衫黑背帶,安安靜靜捧著一尾婚紗擺,他隨著這擺一起走上了紅地毯,臉上帶著得的微笑,轉眼到了晚上,他獨自坐在陌生的房間垂淚。
1992年。
男孩和另外兩個孩子一起去上學,另兩個孩子坐在后車座,他坐在副駕駛位,下車時后車座的小男孩狠狠踹了他一腳,并對他做了個鬼臉,比他稍微大一點的另一個孩對他歉意的笑笑,卻什麼話都沒說。
1994年。
男孩變為了青年,很是平凡的樣貌,這天他起晚了點,出房間看到一家人正在餐桌上其樂融融吃飯,誰都沒發現餐桌上了一個人。
Advertisement
他扯出一抹微笑,又折回了房間。
1996年。
年十六歲,他對理科很是沒有天賦,只能天天跑圖書館期待勤能補拙,這天他跟平常一樣出來,上面突然砸下個花盆,眼看就要落他頭上,卻突然被迎面而來的籃球擊飛。
他慌忙抬頭,瞳孔倒映出另一個年的影子。
“小雨……”邢青鋒已經知道這火車代表著什麼,當看到十六歲的簡雨時驀然了眼眶。
他看著車廂里的年想闖進去,卻被這一層明擋著,只能眼睜睜看著火車繼續啟,他跟著那節車廂跑,可不管它跑得再怎麼快,也只能看新的車廂停在他面前。
過去的,他永遠及不到。
1998年。
年眉清目秀,正靦腆跟在救他的年后。半是仰慕半是。
救他的年從懷里掏出一封信給他,對他說了幾句什麼,他便跟被釘子釘在原地一般不敢彈,滿目星辰慢慢黯淡。
2000年。
奢華的別墅院子里,一條鵝卵石小路一直穿過花園鋪到別墅門口,已經是青年的年就跪在那條小路上,天黑了天又亮了,他跪得大汗淋漓滿臉蒼白都不愿意起來,終于別墅大門打開,一個證件袋丟給了他。
青年面喜,重重磕了一個響頭,拿上證件袋跌跌撞撞跑了出去,他跪得太久,凹凸不平的鵝卵石磨破了他膝蓋,里面溢出鮮紅的,染紅了白運,想跑又跑不快。
“小雨……”邢青鋒知道青年要去做什麼,想抓住他:“回來,他不值得你這麼做。”
2001年
同結婚,慘遭退學,青年將自己鎖在房間里足不出戶,外面是大批大批的記者,他抱膝將自己圈起來,可在門開看見他的人時,又立馬換了張臉。
Advertisement
笑臉相迎,所有的苦水自己咽。
2004年。
青年已經變為了一個溫和的男子,他拎著飯盒進了電梯,卻在出電梯的那一刻,從虛掩的門看見人在和別人親熱。
他嚇了一跳,不敢上前,提著飯盒倉皇而逃,至此再不把飯菜送上來。
2010年。
男子在家看著新聞徒然跪倒,淚流滿面,空氣中傳來他空靈的聲音:“對不起媽媽,對不起叔叔。”
同年四月,男子遭綁架,沒有人救他,他只能被迫從四樓跳下,摔斷了肋骨失去了左耳聽力以及右眼的視線。
“啪!”夢里邢青鋒狠狠甩了自己一耳,他質問著自己:“你怎麼忍心?怎麼忍心讓他獨自承這樣的苦?”
火車又啟了,它就是一個時加載,不為任何人停留也不憐憫任何一個人的懺悔。
2012年
男子捂著臉,眼神空,他打了電話人把鎖給撬開,發了瘋似的在路上跑,他跑到目的地,看到一堆,從鏡子中看到他人趕來的影,笑得病態。
2014年
男子撕心裂肺咬了他人心口一塊,人甩手離去后,他跪在地上用手撿著地上飯菜吃。
邊吃邊吐,淚眼模糊,那些他并不喜歡的東西,皆強迫自己咽下。
2015年
男子從病床上醒來,四周空曠,獨自一人,他到找著手機,打了個電話后病服外濺出鮮紅的鮮,有護士進來給他重新包扎,可他臉上至始至終都只是灰敗。
邢青鋒看到他流的地方,那里消失了顆腎臟。
2016年
男子抓著一堆的藥往里塞,指甲抓著心臟,一痕又一痕,對著鏡子嘶吼吶喊,外面明里面森黑暗。
Advertisement
他無助,旁卻無一人相伴。
2017年。
男子站在宏城最高層的辦公室里,滿目疲倦,他對著邊人說:“我不到他任何的意。”
2018年。
男子將一束向日葵送給了孩子,將一朵向日葵送給了心理師,然后轉跳了冰涼的大海。
“不!小雨,小雨!”邢青鋒瘋狂拍著那層明,卻只能看海水將人完全淹沒。
火車又開始走了。
2020年。
這是……今年……
瘦骨嶙峋的男子就站在車廂門口朝他微笑,邢青鋒楞楞的看著他,不敢眨眼。
男子一步步走下來,那層明消失,他抱住了他。
骨頭咯得邢青鋒生疼。
“青鋒,你放過我吧。”
很輕的一句,還未等邢青鋒回應,就已被風吹散。
連帶著簡雨的人,以及那輛火車、軌道、站臺、標簽都變為碎沙。
風一吹,便都散了。
“小雨!小雨!”夢中的邢青鋒瘋狂奔跑著,淚水劃過角,又咸又。
無論怎樣努力,都只是在原地打轉。
夢外的邢青鋒被徹底驚醒。
臉上噠噠的,鼻尖充斥著消毒水的味道。
簡雨依舊安安靜靜躺在病床上,面上帶著氧氣罩。
邢青鋒爬起來看著人好一會兒掩面痛哭:“小雨,我夢到你了,夢到你的一生,怎麼會這樣呢,怎麼會有這樣的一生。”
“小雨,我想抱抱你,想親親你,我想告訴你,我永遠都不會離開你,小雨,小雨……”
“為什麼不醒過來,小雨,為什麼不醒過來,我是真的改正了,小雨……”
“小雨,我、我……”
他不記得自己哭了多久,只是等停頓時手已經放在了簡雨的氧氣罩上:“小雨,真的這麼痛苦嗎?”
Advertisement
“我真的好想好想和你一起白首……”
下雪了,今天的初雪下得格外早,格外熱烈。
深夜值班的醫生突然被頂層響起的警報震得一個激靈。
那里可是住了位大人啊!記院長特地代那里絕不可以出事。
幾乎是同時,各個值班部門人員都往那沖。
他們氣吁吁到達,剛好看見邢青鋒抱著本是植人的人從病房出來。
“呀!他、他頭發唔……”
一個小護士平復住氣息一抬頭就忍不住驚出聲,旁邊一個醫生立馬一把將要出口的話捂住。
對做了個手勢:“噓!”
走廊很長,男人就那麼一步步抱著人踏出,滿目空,雙眼紅腫。
外面很冷,卻兩件大都蓋在手上人上,他就著一件單,路過眾醫生邊時,掀起一陣涼風。
沒有人說話,就這麼看著他一步步走出醫院,跪倒在漫天大雪里。
冬季夜晚的雪,越下越大,紛紛揚揚迷了每個人的眼。
邢青鋒不打算走了,他慢慢拉下一點大,出簡雨的臉。
指尖輕上去,冰涼骨,他輕吻著這過分消瘦的臉頰,從額頭到鬢角,從眼尾到邊。
雪落了兩人一一頭,將黑發染為了白發。
邢青鋒握住一片雪,又緩緩松開,任它掉落在懷中人上。
他就這麼抱著人坐在雪地上,目盯著懷中人,偶爾抬頭看看這紛揚得璀璨的雪。
從夜到明,第一縷天悄悄爬上來,灑在他上,照亮他滿目灰敗的眼,他雙蠕,似在說給懷中人聽又似在說給自己聽:
“霜雪迎滿頭,就當已白首……”
天大起,后突然傳來一聲很輕的嘆息。
“我原諒你了,青鋒。”
邢青鋒猛的回頭,白茫茫一片的世界,后空無一人。
懷中人更為冰涼,無論他多麼用力都捂暖不了分毫,他像是知道了什麼,心痛得無法呼吸。
“小雨……小雨……再見……”
“小雨……”
“我你,我你,你到了嗎?”
“我你……”
小雨,我能給你最后的,能讓你切切實實覺到的——是放手。
小雨
人間一趟
你辛苦了。
【全文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44 章
穿成反派人魚男妻
当红男团主舞夏瑄阳穿进一本狗血小说里,反派大佬严闵珩的新婚男妻,一名容貌艳丽、肤白腰细臀翘腿长、身娇体软的极品尤物,靠脸拿下男团选秀出道位。 原主因为迟迟无法分化成人鱼,家里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选择嫁给双腿残疾的反派大佬冲喜。 他天天盼着重病的老公快点死,还各种不安于室,勾搭小叔子原主角攻。 穿过来的直男夏瑄阳:……卧槽,他不想被主角受算计毁容,最后还被反派老公送去声瑟场所啊! 夏瑄阳求生欲满满,决心远离主角攻受,还有和反派老公和平离婚。 只是,穿过来没多久,他意外分化成了人鱼,还迎来第一次求偶期。 反派老公突然腿好了,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把他抱着亲吻。 夏瑄阳震惊,这人说好的双腿瘸了,还重病快死了呢?! 严闵珩:“你天天变着法子撩我,我这病装不下去了。” 夏瑄阳:“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 突然分化成了能生崽的人鱼,这还让他怎么继续当直男? 更让夏瑄阳崩溃的是,不久的后来,他怀孕了?!?! #论直男主舞穿到搞基生子文是什么样的体验# ·攻受身心一对一,HE。
33.3萬字8 7836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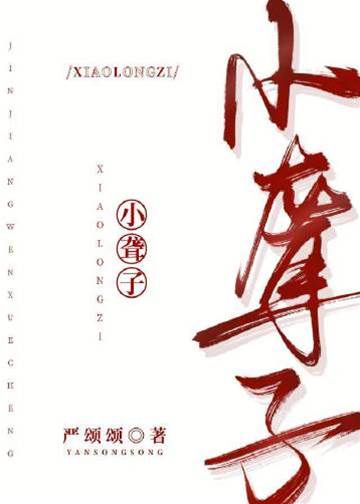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6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