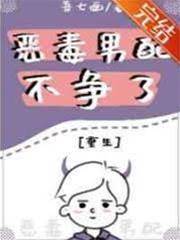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天涯客》 第57章 賭徒
?
周子舒自以爲作已經很輕了,可誰知那屋裡人好像早已經察覺了似,竟就那麼大喇喇地擡起頭來,正好和他目對上。
周子舒愣了一下,只見那人對他一笑,便也不好意思太小家子氣,翻從房頂下來,輕輕地敲了敲窗戶,朗聲道:“不速之客不請自來,主人見諒。”
窗戶便從裡面推開了,一個素男人站在裡面,手裡端著一盞茶,目在周子舒臉上流連一番,又掃了溫客行一眼,笑了笑,輕聲問道:“二位若是想一起看,大可以敲門進來,何必如此?”
他說話聲音好像是虛一樣,特別輕,唯恐聲氣大了驚什麼東西似,人長得斯斯文文,單眼皮,吊膽鼻,倒也十分人模狗樣,單瞧面相,實在看不出他竟是那缺了八輩子大德蠍子頭頭。
周子舒臉皮自然是厚了,聞言一點也不覺得侷促,落落大方地說道:“多謝盛——那倒不必了,實不相瞞,我們來是有事相求。”
這大蠍子掃了他一眼,沉道:“來找我,多半就只有兩件事,要麼是讓我孩子們去殺人放火,要麼是來問,究竟是誰讓我孩子們去殺人放火,以二位手能耐,恐怕是第二種吧?”
周子舒坦然道:“不錯。”
蠍子將茶碗放在一邊,雙手抱在前,玩味地打量著他:“那你能給我什麼?”
周子舒大言不慚地道:“你儘管提。”
蠍子見他豪爽得很,一臉財大氣有恃無恐模樣,便微微一哂——一般來說,像這樣人,要麼是太過自大,自以爲上天地金山銀山,沒有自己辦不事、拿不來東西,要麼……就是打定主意決定賴賬了。
Advertisement
任你漫天要價,我絕不坐地還錢,不給錢就是了。
蠍子慢悠悠地道:“難不你陪我睡一宿,你也答應?”
周子舒挑剔地打量了一下他臉,目又在他腰屁上巡視一圈,這才勉爲其難地答應道:“行啊。”
一邊津津有味地聽著溫客行立刻抗議道:“不行!咱倆同牀共枕了那麼久了,也沒見你答應得那麼痛快!”
周子舒拿眼皮掀了他一下,反問道:“我要問什麼,你知道答案?”
溫客行噎住。
蠍子卻笑起來,脣,目惡狠狠地在兩人之間轉了轉,隨後從懷中拿出一個小罐子,搖了兩下,從中倒出兩枚骰子,攥在手心裡,輕聲道:“不如這樣,你們和我賭一把,贏我一局,我便告訴你們一件事,輸我一局……”
溫客行小聲對周子舒道:“我終於知道爲什麼他急著忙著賺錢了,有這個嗜好,多大家業也不夠他敗,你沒聽說過‘一心贏錢,兩眼熬紅,三餐無味,四肢無力,五業荒廢,六親不認,七竅生煙,八方借債……’”
周子舒踩了他一腳。
蠍子輕笑道:“你這麼說,也有道理,可人這一輩子,不也是一場大豪賭麼,好多人要殺我,我死了,他們就贏了,我不死呢,他們就隨時惴惴不安,不知哪天催命便來了。你說,若一輩子平平順順,豈不是也太沒有趣味了?”
周子舒便截口打斷這倆青年之間關於人生深刻討論,問道:“輸你一局又怎麼樣?”
蠍子斜著眼瞄著他,慢條斯理地道:“不用擔心,我不要你錢,也不要你命,輸一局,你們倆便做一場給我看看,看得我神清氣爽了算——只是二位掂量著來,輸得太多了,可也不好收場。”
Advertisement
周子舒二話不說,斬釘截鐵地道:“後會有期。”
與此同時,溫客行卻求之不得地出來道:“我看這賭注好!”
周子舒裝作不認識他,漠然往外走去,蠍子在他後說道:“這就怕了,剛纔還我隨便開價呢。”
周子舒腳下不停,裡只是輕描淡寫地道:“我都一把年紀人了,激將法就算了。”
溫客行在一邊陪笑道:“那個……蠍子兄見諒哈,我家這位,別什麼都好,就是臉,臉皮太薄……”
他這句話還沒說完,便見周子舒又面無表地轉回來,對蠍子說道:“你說,賭什麼?”
有時候,激將法管用不管,那要看是誰使出來。
蠍子方纔擡起手中骰子小盅,周子舒就冷笑一聲道:“雕蟲小技而已,恐怕我們便是弄上一宿,也分不出什麼勝負。”
蠍子眉頭一皺,想了想,轉往屋裡走去,溫客行和周子舒便從窗戶跳了進去。只見那蠍子翻出了一包細如牛小針,周子舒眉頭皺了皺——他著過這東西道兒。
蠍子捻起一小針,用舌尖輕輕了,說道:“這個是還沒來得及淬毒,不如我們賭賭看,誰吃得比較多,好不好?”
周子舒和溫客行對視一眼,那一瞬間,兩人心有靈犀了,同時想著——爲什麼葉白不在這裡?
蠍子瞇起眼睛,張去咬,那針竟好像麪條一樣,被他咬了一段一段,然後他竟就這麼把針吞下去了,周子舒和溫客行面面相覷,沒想到這大蠍子竟還是個鐵齒銅牙。
蠍子笑問道:“二位是賭,還是寬?”
溫客行看起來非常想選後者,周子舒忽然從桌子上拿起一個酒杯,打開自己酒壺,斟了滿滿一杯,手起兩針,在指尖一撮,那兩小針就變了一堆末,轉眼便融進了酒裡,他擡頭看了蠍子一眼,蠍子倒是頗有風度,舉手示意他先請,周子舒皺著眉將杯中酒飲盡,亮了亮杯底,溫客行冷眼旁觀他臉,覺著那酒水味道多半不會比放了核桃更好喝。
Advertisement
蠍子笑道:“這位兄臺,別怪我沒提醒你,你這樣就著酒吃,可比我幹吃佔肚子裡地方,難不你們二位想一起對付我一個?”
溫客行忙擺手道:“不不不,在下沒這個雅興和牙口,你們自便,自便。”
周子舒忽然一笑,道:“我吃了兩,你吃了一,我看足夠贏你了。”
他話音沒落,便出了賤招,一掌拍在桌子上,那些牛細針四下翻飛而起,寒四溢,蠍子只覺一勁力襲來,下意識地低喝一聲,彎腰閃過,再回頭,只見桌上所有牛針全都著他釘在了牆裡,竟是深數寸,再想拿,是拿不出了。
溫客行忍不住了聲好,心說阿絮這招真是無恥至極,大像自己作風,不愧是那啥唱那啥隨。
蠍子一皺眉,隨即又慢慢展開,仍是不慍不火地問道:“兄臺貴姓?”
周子舒道:“免貴姓周。”
蠍子點點頭:“周兄好功夫,好心思,只是……”
他開手掌,一細針平躺於掌心上,蠍子邊往邊遞去,便笑道:“這回,恐怕是平手。”
周子舒卻不慌不忙地也開手掌,只見他手心不知何時也私藏了一針,他並沒有要吃,只是將那針送到蠍子面前,比了一比——蠍子臉登時變了,這才發現,自己手上這竟然是短上一截,竟不知何時被這人以掌力削去一半。
周子舒將手中細針碾齏,笑道:“兩對一半,怎麼說?”
蠍子狠狠地盯著他,溫客行和周子舒都以爲他要發難,誰知這大蠍子人品不怎麼樣,賭品竟然還不錯,片刻,漠然轉開目,說道:“好,願賭服輸,你們要問什麼?”
Advertisement
周子舒道:“除了孫鼎,是誰出錢要買張嶺命?”
蠍子頓了頓,又看了看他們兩人,似乎明白了什麼,道:“張嶺?哦,我可知道二位是誰了……只是我人在庭便失去了你們蹤跡,想不到竟已經找到了這裡,真是神通廣大——跟我來。”
他說話間掀開牀板,一頭鑽了進去,周子舒和溫客行便隨其後。
兩人隨著這蠍子一路進了一條道——這地方,外面是胭脂黛,裡面卻森異常,十分詭異。蠍子帶著他們兩個彎彎繞繞一路,也不知下了多層臺階,這纔到底,周子舒兩人看去,只見此是一個地牢,一聲聲抑、似人又不像人咆哮四下響起,二人不戒備起來。
蠍子取下牆上火把,在一個囚籠面前站定,似笑非笑地說道:“二位可以來看看這東西,該是老相識了。”
他說話間,可能是被刺激,一道慘白影子猛地衝著蠍子撲過來,又被牢門擋住,便一臉猙獰地衝著他們張牙舞爪。周子舒和溫客行看清了,那裡面竟然關了一個怪,和當年他們在那神地裡遭遇似人非人怪如出一轍!
只見蠍子目溫地著那怪,好像它是個絕世大人一樣,輕聲細語地說道:“這些是我們藥人,週歲以前是人,不過滿週歲開始,便一直用藥灌養,養到如今,生得一銅皮鐵骨,殺氣騰騰,實在是很好孩子……只是不大聽話,可能是用藥傷了腦子,以後還要完善。”
溫客行臉上嬉笑之沒了,沉聲問道:“那地是你佈置,買主是長舌鬼?”
蠍子道:“不錯。”
溫客行截斷他道:“放屁,長舌鬼已經被我宰了,之後在庭追殺張嶺人又是誰?”
蠍子臉上出一個狡猾笑容,說道:“我只說買家是長舌鬼,並沒有說,他背後便沒有人指使。”
周子舒道:“啊,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你意思是,想知道這個答案,還要再賭一次是麼?”
蠍子微微欠,道:“周兄包涵。”
周子舒不耐煩地甩甩袖子:“你說,賭什麼?”
蠍子笑道:“賭那些小玩意,我功夫不及周兄,心思也不及周兄靈巧,恐怕是又要輸了,不如我們聽天由命,從這裡上去,出門到街口,你們二位當中一個人蒙上眼,從此人手到到街口那隻石獅子開始數,看第二十個經過眼前,是男還是,如何?”
溫客行忍不住道:“這賭可無意義得很,我瞧不出對你有什麼好。”
蠍子平聲靜氣地道:“賭什麼無所謂,對我來說,重要就是一個賭字,好比旁人了要吃飯,了要喝水,不讓我賭,我便活不下去……你們說呢?”
溫客行嘆了口氣,只覺得怪事年年有,今年真是多,便手指指周子舒道:“蒙他眼睛,省得他覺著我意圖不軌。”
周子舒看了蠍子一眼,沒有反對,溫客行便從懷中索了半天,出一塊汗巾,蒙在了周子舒眼睛上,抓住他手臂,對蠍子道:“你先請。”
三人就這麼又搗騰到了地面上,一路以這種躲貓貓造型到了花街巷口,蠍子道:“周兄,你擡手便能見那獅子了,客人先請,請下注。”
周子舒和溫客行異口同聲道:“男。”
這裡穿梭雖然有流鶯,可尋歡客流更大,既然這大蠍子頭頭大方,他們倆就卻之不恭了,蠍子臉上閃現出一種說不清興之意,一雙眼睛亮了起來,迫不及待似脣:“好。”
周子舒擡手剎那,蠍子便開始數人——十八,十九……
連溫客行都讓他鬧得有些張,周子舒早已將眼睛上蒙東西摘了下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著,第二十個人經過了,是個穿長袍,長髮冠男人!
周子舒臉上慢慢出一個笑容,纔要開口說話,然而隨著這人走近,他笑容便僵在了臉上,蠍子卻志得意滿地掃了他們二人一眼,忽然上前一步攔住這路人,將路人嚇了一跳,只聽他聲細語地說道:“此乃煙花之地,小姐進去多有不便,姑娘家清譽要,請回吧。”
那“男人”那細膩白皙臉上便奼紫嫣紅起來,蠍子道聲“得罪”,忽然出手如電地扯下了“他”頸子上圍巾,路人短促地驚一聲——“他”嚨竟十分,瞧不出一點凸起。
蠍子笑盈盈地轉過來,雙手攏進袖子,慢條斯理地對周子舒道:“周兄,這又怎麼說?”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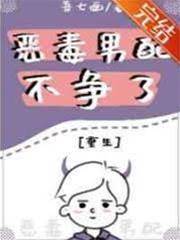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0242 -
完結110 章

我在娛樂圈當最強大腦
全能冷清禁欲系大學教授沈之南意外重生到一個和自己同名同姓、在娛樂圈聲名狼藉的小鮮肉身上。 沈之南剛睜開眼醒來就發現自己全身赤.裸地躺在一張大床上。 那個叫霍淮北的男人站在床尾,嘴角勾起薄涼的弧度,冷冷地看著他:“想爬我的床,你還不夠格。” 沈之南因為這件事淪為了大家的笑柄,在娛樂圈名聲更臭。 * 過了一段時間,人們驚訝地發現,那個叫沈之南的小鮮肉,再也不和別人炒緋聞搭關系了,而是活躍在各大綜藝節目上。 某問答節目上,沈之南一臉淡定,神情慵懶:“該詩出自于《詩·鄘風·載馳》。 某荒野求生節目里,沈之南帶領他們隊成為史上最快完成挑戰的隊伍。 旁觀眾明星全都驚掉了下巴,沈之南一躍成為娛樂圈里的最強大腦。 再后來豪門大佬霍淮北當眾向沈之南表白,沈之南卻拒絕了他,并扶了扶眼鏡,漫不經心道:“對不起,跟我表白,你還不夠格。” 【小劇場】 事后記者采訪沈之南:“您連霍淮北那樣的人都拒絕了,請問您的理想型是什麼樣呢?” 沈之南神情慵懶,雙腿交疊坐在沙發上,漫不經心道:“沒什麼特別的要求,會拉格朗日力學就可以。” 記者哆哆嗦嗦遞話筒:“您..認真的嗎?” 沈之南薄唇微抿,稍加思索:“其實會麥克斯韋方程組也行。” 霍淮北隔著屏幕看著沈之南的采訪錄像,陰惻惻地吩咐秘書:“去,把今天的會全推掉,請個有名的物理學家來給我上課。” #懷疑你根本不想跟我談戀愛,可是我沒證據# 1.本文所用專業知識大家看著樂呵就可,不要深究,作者只做過功課,但并非專業,感謝指正。
29.8萬字8 79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