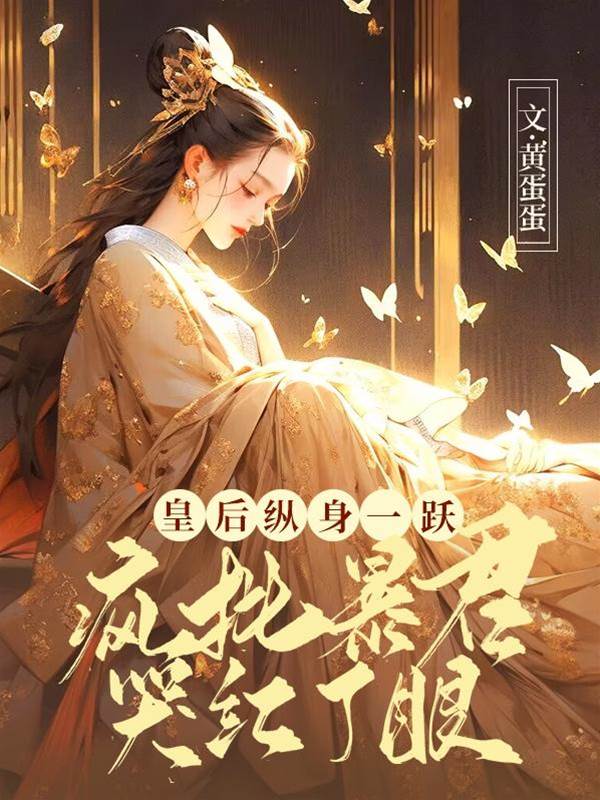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劍尋千山》 第76章 第七十五章
雨聲淅淅瀝瀝, 花向晚有些疲憊,窩在謝長寂懷里,半醒半睡淺眠。
謝長寂攬著懷里的人, 看著窗外細雨, 卻有些睡不著。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覺。
他從未有過這樣的驗, 覺好像有什麼盈滿心, 讓他覺得這世上一切無一不好,無一不讓人容。
他聽著雨聲, 看著雨打玉蘭, 嗅著之氣與子香混合的氣息,靜靜著這一切。
“嗯?”
花向晚迷迷糊糊醒過來,察覺謝長寂還很清醒, 茫然回頭:“你怎麼還不睡?”
聽著這話,謝長寂垂下眼眸, 實話實說:“睡不著。”
花向晚緩了片刻,逐漸醒過來,翻了個, 和謝長寂面對面躺著。
云雨方過,兩個人都不著片縷,綢緞一般的薄被半遮半掩, 花向晚看著面前青年近在咫尺清俊的面容。他神平靜,但帶了幾分平日沒有的溫潤,想了想, 吸了吸鼻子,只道:“睡不著那我陪你聊聊天?”
“你睡吧。”謝長寂搖頭, “我躺一會兒就好。”
“沒人專門陪你聊過天吧?”
花向晚看他反應,有些好奇, 謝長寂認真回想了一下,像是在回答極其鄭重的問題,搖頭道:“除你之外,沒有。”“我以前陪你聊過?”
花向晚一時有些想不起來,謝長寂垂下眼眸,遮住眼中神,目中帶了幾分和:“經常。”
“我怎麼不記得?”
花向晚回想了一下,有些奇怪,謝長寂溫和道:“你以前,話很多。”
是話多,總想找話題同他多幾句,可那時候他幾乎不怎麼回應,這也算得上聊天?
但想想謝長寂的子,說不定當時他回應那幾句“嗯”,已經是他極大的努力了。
Advertisement
花向晚表示理解,琢磨片刻,抬手枕在頭部,看著謝長寂,笑瞇瞇道:“那你不嫌我煩?”
“喜歡的。”
謝長寂看著,沒有半點遮掩:“你和我說每個字,我都很喜歡。”
聽到這話,花向晚心上一跳,莫名竟有些不好意思,知道他大多數時候不會騙人,但越是知道,越覺得高興,想想或許是因為這張臉太俊的緣故,便決定不去看他,翻了個趴在床上,嘀咕著開口:“以前鋸都鋸不開,現在開了一樣,昆虛子是送你去什麼地方專門學的麼?”
“我只是不習慣說想不清楚的話。”
謝長寂說著,抬手替拉好被子,花向晚聽著他的話,側頭看他,有些好奇:“那你現在說的,都是你想清楚的?”
“嗯。”
謝長寂應聲:“想了好多年。”
“你……”花向晚遲疑著,“這兩百年一直在想這些?”
“在想,”謝長寂慢慢說著,“每個片段,一點一點回想。”
所以任何細節,他都不曾忘。
花兩百年歲月,一點一點緩慢確認,抗拒,最終接——他喜歡。
花向晚明白他的意思,看著謝長寂,他和認識的所有人都不同。他修為高深,聰慧非凡,他似乎能參這世上最深奧的道理,但在細微之,他似乎又連稚子都不如。
靜靜看著他,過了一會兒后,輕聲開口:“謝長寂,你小時候都做些什麼?”
聽到這話,謝長寂沒有出聲,花向晚回憶著:“我小時候很皮,每天都在玩,我父親病重,但他很疼我,每天他給我講故事,我娘和師父教我修行,還有很多師兄師姐,他們都會帶我玩……”
說著,花向晚忍不住笑起來:“二師兄會帶我劍在天上飛、放風箏,大師兄會給我折紙鶴,大師姐會給我做好吃的,扔沙包……”
Advertisement
花向晚一面說,一面忍不住轉頭:“你呢?你做什麼?”
“修行。”
謝長寂想著當年,認真說著:“每日卯時起,提水,站樁,揮劍一萬下,之后聽師父講道,念書,亥時睡下。”
“沒了?那你休息時候做什麼?”
花向晚奇怪,謝長寂想想,只道:“看,聽,嗅,嘗,。”
“這是做什麼?”花向晚聽不明白,謝長寂認真解釋。
“看萬事萬,聽聲,嗅各種氣味,嘗各種味道,會各種覺。”
“冷、熱、疼、酸、痛……”
謝長寂描述著:“而后,一一對應,一一明白,一一模仿。”
他無法像常人一樣,自然而然去明白所有詞的含義,疼是什麼,疼過明白;痛什麼,痛過才知曉。
然而也正是如此,他對這世上之事,要麼不懂,要麼,便比常人懂得更深,更徹。
可他不是不會懂,只是懂得比他人慢。
總要遲那麼一些,晚那麼一點。
花向晚聽著他說這些,莫名有些心酸,只道:“你方才睡不著,也是在做這些?”
“嗯。”
謝長寂應聲,花向晚好奇起來:“那你聽到了什麼,看到了什麼,覺到了什麼?”
謝長寂聽著的話,靜默無言,許久后,他緩聲道:“幸福。”
花向晚一愣,謝長寂目溫和,他抬手將頭發繞到耳后,輕聲道:“我聽見雨聲,有如天籟;我嗅到水汽,倍覺清潤;我看見細雨、暖燈、玉蘭、長廊,都覺漂亮好。天地靈,萬可,令人歡喜異常。”
“喜歡這個世界?”
花向晚聽出謝長寂語氣中的溫,忍不住笑。
謝長寂想了想,應聲:“喜歡。”
“那就好好記住這種覺。”花向晚出手,攬住他的脖子,近他。
Advertisement
兩人在暗夜中抵著額頭,聲音下許多:“凡天道認可之道,無一不以為始,以善為終。心有所喜,心有所憫,心有所悲,才會有善有德。”
謝長寂聽著這話,他抬眸看,黑白分明的眼微:“不曾有人說過。”
“那他們怎麼同你說的?”
“生來如此。”
謝長寂平靜說著:“生來應善,生來應以蒼生為己任,生來應懂是非黑白。”
“若這麼簡單,所有一切生來當如是,”花向晚笑起來,“那世上又何來善惡呢?”
謝長寂聽著,沒有出聲,他似在思考。
花向晚看著他的樣子,想了想,抬手抱在他腰上,仰頭看他,打斷他的思緒:“算了,別想這些,想想以后。你這次和昆虛子鬧翻了,咱們回云萊,還能回天劍宗嗎?”
“你到底要償還什麼?”
沒有理會花向晚虛無縹緲的假設,謝長寂抬眼,徑直出聲。
花向晚作一頓,謝長寂盯著:“要以死相求?”
花向晚沒出聲,雨聲漸弱,謝長寂知道或許又想遮掩。
他也習慣,只是終究有那麼幾分失落,他輕嘆一聲,只道:“睡吧。”
“我想讓他們活過來。”
花向晚突然開口,謝長寂沒想到會應答,他抬眼:“誰?”
“他們”不可能只是一個沈逸塵,那必然是許多人。
哪怕心中早有猜測,可還是忍不住確認:“合歡宮已死之人?”
“對。”
花向晚沒有遮掩,謝長寂皺起眉頭:“死而復生本就是逆天而行,這世上所有事都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早就準備好代價了。”
花向晚快速回應,謝長寂心上一。
“什麼代價?”
“門弟子一百零三人,”花向晚挪開目,不敢看謝長寂,快速說著自己的計劃,“當年我母親都給他們打了魂印,我可以順著魂印追回他們的魂魄。找到魂魄,給他們準備好,魂歸位,就能讓他們回來,所以我去天劍宗取了魊靈。”
Advertisement
“你要魊靈,不是為了報仇,是為了復活他們?”
“兩者沒有區別,”花向晚出聲,目極為冷靜,“你說得沒錯,這世上所有事,都有代價。所以,想要一個人生,必須有一個人死。他們欠了合歡宮的,”花向晚抬眼,平靜開口,“得還。”
“之前我沒有足夠能力。”花向晚說著,靠在謝長寂口,“我可以簡單滅了九宗任何一宗,又或者是拼全力和溫容鬧個你死我活,但我沒有能力同時對抗魔主、鳴鸞、清樂、以及九宗幾大宗門。而這些人在合歡宮那件事后,早了一塊鐵板,他們共同敵人,是合歡宮。我有任何妄,都是滅宮之禍。”
“所以,這兩百年我一直在努力得到他們信任,等待魊靈出世,同時在確認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是誰做的什麼事。我想好了,”花向晚笑起來,“魊靈出世,魔主重病,我就打著去天劍宗的名義,將魊靈搶回來。然后殺了溫清,嫁禍冥,挑撥兩宮關系,再找到師兄師姐的蹤跡,把尸首搶回來。等我用魊靈的力量,殺了他們所有人讓師兄師姐復活,我也就走到頭了,我不能真的讓魊靈禍世,也不能真的因一己之私不顧后果。”
花向晚神清明,說得極為坦:“所以,從我去天劍宗開始,我就給自己定好了結局。”
說著,抬眸看他,有些無奈:“只是我沒想到,你會來。”
“那現在呢?”
謝長寂聽的話,便知道,有了新的打算,不然不會告訴他這些。
“現在,”花向晚笑著近他,抬手覆在他臉上,語氣輕佻,“你不是來了麼?”
“鳴鸞宮這一戰之后,九宗肯定有很多宗門投靠,云裳會幫我拿到令,我會順利為魔主。到時候拿到復活逸塵的辦法,我們便能復活逸塵。”
“之后你幫我復活沈逸塵,同我一起殺了他們,”的言語好似妖,蠱著他往地獄一起沉淪而去,“用他們的命換我合歡宮弟子的命,等合歡宮安穩下來,咱們帶著魊靈回死生之界。謝長寂,”看著他,目里滿是期,“我不想死了。”
謝長寂不說話,他垂眸落到口刀疤上。
的話百出。
怎麼知道魔主會在魊靈出世時病重?
既然當年這些人是一塊鐵板,為什麼合歡宮還能生存下來?魔主和換的是什麼?
溯鏡里他們便已經知道魔主是取走秦憫生魄之人,也就意味著,合歡宮之事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魔主,而魔主也是西境真正最強之人,可整個計劃,對如何理魔主卻沒有任何打算,為什麼?
他想問,卻不敢開口,他腦海里劃過一個念頭——
另一半魊靈,在魔主那兒。
猜你喜歡
-
完結617 章
絕色煉丹師
她毒藥無雙,一朝穿越!坐擁煉丹神鼎,修煉逆天!誰還敢嘲笑她廢柴!想要謀奪家財?她就讓他家破人亡;你家爺爺是絕世高手?不好意思,他剛剛做了她的徒弟;你的靈寵舉世難見?不巧,她剛剛收了幾隻神獸;別人求之不得的丹藥,她一練就一大把!她風華絕代,輕狂傾天下,誰欺她辱她,必定十倍奉還!可就有一個腹黑邪魅、手段狠辣的男人跟她情有獨鍾,還問她什麼時候可以生個娃。她橫眉冷對:“滾!我們不熟!”
112.2萬字5 108840 -
連載769 章

嫡女嫁到,侯爺寵上癮
前世為他人鋪路,一場賜婚等來的卻是綠茶渣男成雙對,她滿門被滅葬身亂墳。死後六年浴火重生,昔日仇人各個權貴加身,她很不爽,發誓虐死他們!偏偏有個男人霸道闖入,她怒了,“滾,彆礙著我的路!”寧遠侯輕輕一笑,甚是邪魅張狂,“我知你瞧誰不順眼,不如上榻聊,為夫替你滅了。”不要臉!說好的淡漠孤冷生人勿近,怎麼到她這全變了!
124.1萬字8 85469 -
完結80 章
與兄書
永樂郡主謝寶真身為英國公府唯一的女兒,萬綠叢中一點紅,上有三位叔伯護陣,下有八位哥哥爭寵,可謂是眾星捧月風光無限。直到有一天,家里來了位冰清玉潔從未謀面的九哥,從此平靜的英國公府內暗流涌動。這位九哥什麼都好,就是患有啞疾、身世悲慘。那日初見,小郡主以為九哥是父親背叛母親所生的私生子,故而百般刁難,小野貓似的瞪著他:“以后不許你靠近主院半步,不許出現在我眼前!”謙謙白衣少年發不出聲音,朝著小郡主頷首低笑,只是那笑意從未照入他的眼底。再后來,這個啞巴九哥將某位紈绔堵在深巷中,褪去溫潤如玉的偽裝,露出猙獰的獠牙。他冷眼盯著地上被揍得半死不活的紈绔子弟,一貫緊閉的唇終于開啟,發出嘶啞低沉的聲音:“以后你哪只腳靠近她,我便打斷哪只腳;哪只手觸碰她,我便斷了哪只手;多看一眼,我便挖了一雙眼,多說一句,我便割了你的舌頭!”永樂郡主這才明白,高嶺之花原來是朵不好惹的黑蓮花!閱讀指南1.女主嬌氣略作小可愛,男主裝病大反派,心狠手辣非善類,只對女主一人好;2.男女主無血緣關系。因情節需要朝代架空,勿考據.
27.6萬字8 18973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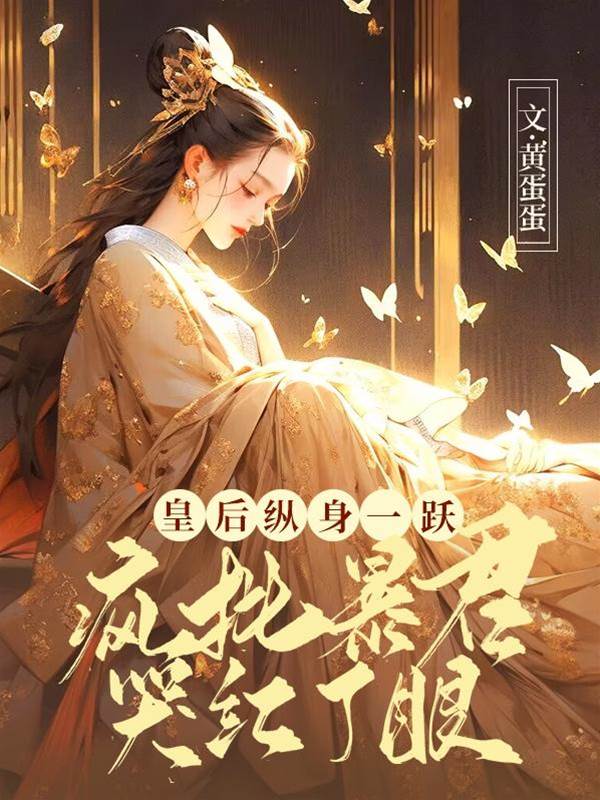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1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