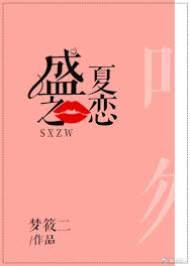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一往情深,傅少的心尖愛妻》 第1173章:定風波(1)
在紀深爵出下一個飛鏢時,簡純忽然慘烈的大著:“不要!”
紀深爵手裏的飛鏢止住,男人麵滿是冰霜,卻又閑暇從容,“你跟那個歹徒之間,究竟做了什麽勾當?就算你不說,待會兒那個人被救醒,一樣會真相大白。”
郝正的手機正在此時響起來。
來電顯示是手下的號碼。
“爵爺,應該是醫院的消息。”
紀深爵黑眸危險的瞇了瞇,“接。”
郝正接起電話,電話裏道:“郝特助,不好了,那人搶救無效死亡了。”
郝正怔了下,卻很快掩飾過去,鎮定的道:“知道了。”
掛掉電話後,郝正麵不驚的對紀深爵說:“爵爺,那人已經離生命危險,很快就會醒過來。”
簡純雙眸裏盛滿了恐懼。
兩年前的事,終究是紙包不住火了。
“說吧,我隻是早一點知道和晚一點知道的區別,可你,我就不敢保證,晚一點你這上會被我的飛鏢出幾個窟窿來了。”
那手腕子上著的飛鏢,讓簡純連脈搏跳一下都是刺痛難熬的。
額頭上,滿是冷汗。
忽然釋懷的哈哈大笑起來,憎恨報複的盯著紀深爵,一字一句咬牙切齒道:“反正你遲早都會知道,不妨我就親口告訴你!我知道你不會放過我,反正我已經被你折磨這副屈辱的樣子,還怕什麽?”
“說。”
男人攥著一個飛鏢,猛地在另一隻手臂上,貫穿骨。
“啊——!”
簡純又是慘了一聲。
痛恨道:“兩年前,言歡跟陸琛茍且的事,是我做的,我派人綁了言歡,給和陸琛注了致幻劑,我知道言歡和陸琛這種自作清高的人,普通春/藥是沒法讓他們乖乖就範的,他們這種人,寧願忍到死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尊嚴和清高,可致幻劑不一樣,就算他們清高的沒有發生關係,也會有強烈真實的混記憶,讓他們以為發生了關係。摧毀像他們這樣故作清高的人,隻要踩碎他們的尊嚴和清白,便是誅心。”
Advertisement
紀深爵的拳頭,漸漸攥,麵,沉的快要滴出水來。
簡純瘋狂笑著:“紀深爵,你沒想到吧,你親手押著言歡給我輸,可這一切,都是我做的!我當初隻是想拆散你跟言歡,讓你跟言歡心裏永遠都記著這份屈辱和影!可我沒想到,紀深爵你也這麽可憐,有那樣一個喪心病狂的母親!”
沈曼?
“這件事,沈曼也參與在其中?”紀深爵的手,猛地卡住簡純的脖子,幾乎要碎。
簡純的臉已經了豬肝,可仍舊得意笑著,“那個要命的致幻劑……是你母親親自從國外帶回來的,如果不是有的幫助,我本沒法對付言歡!哈哈哈哈……”
簡純猖狂的笑意,刺眼誅心。
紀深爵抓著一個飛鏢,用力刺進臉上,,噴在了他臉上,可男人的眼睛,沒有眨一下。
狠到了極致。
已然不將簡純當做一個人去懲罰。
這一刻,紀深爵所有的風度,都化為灰燼,他隻想,將這個歹毒的人,撕碎片。
郝正遞過紙巾,紀深爵接過。
慢條斯理的拭著臉上和手指上每一滴骯髒的。
而後,紀深爵轉朝後走了幾步,走到五米開外,他手裏一把數不盡的飛鏢。
被釘死在大轉盤上的簡純,似乎預到什麽,恐懼的瞳孔瞬間放大。
“不……不……”
可如今,怎麽懇求,都無濟於事了。
紀深爵是修羅,殺人時,不眨眼。
那奪命的飛鏢,一個接著一個,貫徹簡純的骨、眼睛、髒……
那轉盤上的人,七竅流,滿都被紮滿了飛鏢。
Advertisement
紀深爵沒有一次中要害,他隻準無誤的中那些人的痛點。
讓殘存著一口氣,知那一點一點死亡的無盡痛覺。
簡純渾被紮的像個刺蝟,滿是飛鏢。
被鬆綁,從大轉盤上摔在地上。
郝正看了簡純一眼,簡直慘不忍睹,移開眼睛問:“爵爺,接下來怎麽理這個人?”
“把送去非洲黑人的奴隸區,留著一口氣,讓此生盡極致屈辱。”
“是。”
奴隸區。
那是比地獄還可怕的地方。
人命比草芥還要低賤。
瘟疫、艾滋、強/暴……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
去那裏,活著不如死。
簡純掙紮著,匍匐在地上,一步步爬向紀深爵,手,攥住了他的西腳,虛弱無力的求著:“殺了我,殺了我吧……”
紀深爵一腳將踹在了對麵的牆壁上,又重又狠。
簡純已然殘廢,渾癱瘓,流放到奴隸區,也不過是躺著被淩辱罷了。
可紀深爵最痛恨的,不是簡純,是沈曼。
那個跟他有著緣關係的人,兒時拋棄他,現在竟然連他的幸福也舍得摧毀。
到底,有多鐵石心腸?
紀深爵恨得,想殺了這個與自己有緣關係的人。
他握著拳頭,目猩紅滿是戾氣的問:“嘉華地暖是不是還茍延殘著?”
郝正道:“沒錯,嘉華地暖雖然因為資金問題不得不退出中國的市場,但在國還有一定的市場,雖然不景氣,但還能勉強活著。”
紀深爵結滾了滾,咬牙道:“從今晚的開盤後,每隔一小時,就讓嘉華地暖的市值蒸發一千萬,讓它慢慢死。”
Advertisement
沈曼一傲氣,他就挫挫這傲氣,讓清醒明白的死。
他點一把火,慢慢熱著鍋,看著這鍋上的螞蟻,沒有頭緒的焦灼至死,讓知道什麽是一點一點崩潰的覺。
……
紐約,早晨十點半,市場剛開盤不久,市正熱鬧。
許嘉華穿著一正裝,坐在電腦麵前關注市走向。
沒一會兒,便發現了異樣。
嘉華地暖的這支企業票,像是被對家不要命的吃定了,被瘋狂圍著阻擊。
剛開盤,第一個小時,賬麵損失一千萬。
第二個小時,損失兩千萬,依次遞增。
許嘉華握著鼠標的手指,栗起來,一邊盯著電腦屏幕,一邊喊:“阿曼!阿曼!”
沈曼聽到呼喊聲,裹著披肩進了書房,“怎麽了?發生什麽事了這麽慌張?”
“不好了,我們像是被盯上了,我們公司的票漲跌像是被盤了,每個小時都在損失,對家甚至有意要加大杠桿,以這樣蒸發的速度下去,我們公司一定會負債破產。”
沈曼擰眉,連忙看向許嘉華電腦屏幕上的票走勢。
完了。
許嘉華著急的問:“最近你有沒有得罪什麽人?”
“沒有,跟我們接合作的那些公司,絕沒有這樣龐大的資金,何況對家自損八百也要傷我們一千,來勢兇猛……太可怕了,這個人瘋了!”
“我們市值已經憑空蒸發了兩千萬,在下一個小時裏,我不確定會不會再蒸發一千萬,我們耗不起!”
沈曼咬著,在書房電腦麵前來回踱步的思索。
忽然想到一件事。
抓著手機就給簡純打電話。
Advertisement
電話響了很久,最終被接起。
可電話裏傳來的不是簡純的聲音,而是一道冷厲的男聲,“喂。”
這男聲,悉極了。
沈曼甚至不敢往深想,連忙掛掉了電話。
跌坐在椅子上,臉煞白。
“阿曼,阿曼?你怎麽了?”
沈曼看著許嘉華,彷徨無措道:“是……是深爵。要搞垮我們的人,是深爵。”
許嘉華一瞬置絕,亦是跌坐在椅子上。
紀家的產業,對嘉華地暖來說,是龐然大。
紀深爵在歐的資金和票,足以不費吹之力的,將嘉華地暖致命的毀滅。
猜你喜歡
-
完結485 章
萌妻小寶神秘爹地求抱抱
魚的記憶隻有七秒,而我,卻愛了你七年。 ——喬初淺。 喬初淺從冇有想到,在回國的第一天,她會遇到她的前夫----沈北川! 外界傳言:娛樂圈大亨沈北川矜貴冷酷,不近人情,不碰女色。 卻無人知道,他結過婚,還離過婚,甚至還有個兒子! “誰的?”他冰冷開口。 “我……我自己生的!” “哦?不如請喬秘書給我示範一下,如何,自—交?”他一字一頓,步步趨近,將她逼的無路可退。 喬景言小朋友不依了,一口咬住他的大腿,“放開我媽咪!我是媽咪和陸祁叔叔生的,和你無關!” 男人的眼神驟然陰鷙,陸祁叔叔? “……” 喬初淺知道,她,完,蛋,了!
86.5萬字8 13911 -
完結471 章

萌寶尋爹:媽咪太傲嬌
母親去世,父親另娶,昔日閨蜜成繼母。 閨蜜設局,狠心父親將懷孕的我送出國。 五年后,帶娃回國,誓將狠心父親、心機閨蜜踩在腳下。 卻沒想到轉身遇上神秘男人,邪魅一笑,“老婆,你這輩子都逃不掉了……”
83.4萬字8 75541 -
完結84 章

敗給喜歡
多年后,雨夜,書念再次見到謝如鶴。男人坐在輪椅上,半張臉背光,生了對桃花眼,褶皺很深的雙眼皮。明明是多情的容顏,神情卻薄涼如冰。書念捏著傘,不太確定地喊了他一聲,隨后道:“你沒帶傘嗎?要不我——”謝如鶴的眼瞼垂了下來,沒聽完,也不再停留,直接進了雨幕之中。 很久以后,書念抱著牛皮紙袋從面包店里出來。轉眼的功夫,外頭就下起了傾盆大的雨,嘩啦嘩啦砸在水泥地上。謝如鶴不知從哪出現,撐著傘,站在她的旁邊。見她看過來了,他才問:“你有傘嗎?”書念點頭,從包里拿出了一把傘。下一刻,謝如鶴伸手將傘關掉,面無表情地說:“我的壞了。” “……” *久別重逢/雙向治愈 *坐輪椅的陰郁男x有被害妄想癥的小軟妹
24.9萬字5 8280 -
完結501 章

金牌律師Alpha和她的江醫生
ABO題材/雙御姐,CP:高冷禁.欲腹黑醫生omegaVS口嫌體正直悶.騷傲嬌律師alpha!以為得了絕癥的岑清伊“破罐破摔“式”放縱,三天后被告知是誤診!換家醫院檢查卻發現坐診醫生竟是那晚和她春風一度的漂亮女人。岑清伊假裝陌生人全程高冷,1個月后,江知意堵住她家門,面無表情地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我懷孕了。第二句:是你的。第三句:你必須負責。——未來的某一天,江知意堵住她家門......
172.4萬字8 11794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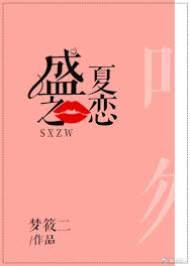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