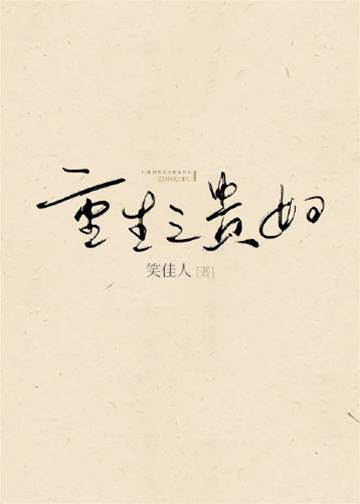《辣手王妃:皇上別惹我》 第12章 :不要辜負朕
左冷函眸子突染寒霜,剝離上的一雙腕,厲道:“你出去就是要去冷宮見那毒婦嗎?你不知道他是害死朕皇兒的兇手嗎?你太讓朕失了!”
“皇上,對不起,姐姐不是故意的,臣妾隻是……隻是想去看看姐姐過得好不好,皇上要怪就怪臣妾不知道保重子,任的去池子喂錦鯉,還請皇上懲罰嗚……嗚嗚!”
左玄羽憐惜的將歐妃扶起來,圈在懷裏,聲安:“好了,妃兒,是朕不好,嚇到你了,朕不是怪你而是不想你在到傷害,看眼睛又哭紅了,來朕給你。”
歐妃哭得更大聲了,手臂抱住左玄羽的脖頸不肯鬆手,噴湧而出的淚水沾了左玄羽前一大片服,如果說之前的淚水是假的,那之後的淚水是真的,不是因為而是因為傷害了他。
左玄羽俯下頭,吻去歐妃眼角的淚珠,慢慢遊移到嫣紅的瓣忘的糾纏,在歐妃以為要昏過去的時候,他放開了,深的對視著歐妃迷離的雙眸:“妃兒,朕決定要封你為後,朕把所有都給你了,隻求你一直陪在朕邊好嗎?”說著將歐妃的右手按在心口。
Advertisement
點了點頭,再次擁住左玄羽將頭靠在他的臂彎裏,眼眸輕闔貪婪著吸食此刻左玄羽的氣息,心裏反複念叨一句話:到真相大白的那天,玄羽你一定不會願意再見到我,那就讓我記住現在吧!
左玄羽笑了笑,手環上歐妃的小蠻腰,“謝上蒼讓朕遇到了你,父皇曾說帝王不該有,會讓帝王丟掉皇位,可是朕即便失去皇位,也不能失去妃兒的,所以朕希妃兒不要辜負朕。”
覺到無邊的寒氣侵蝕著的,寒冷的遊走全肢僵的不能彈。
“妃兒,你怎麽了?臉怎麽這麽難看?”
“我有點冷,玄羽你抱我到床上躺一下吧!”
“恩。”抱起走到室,溫的將放到床上,拉過被褥,手無意到歐妃的手指,冰涼的讓左冷函眉心皺一團,朝外大喊:“小路子……去把張太醫宣過來!”責備的看著,繼續講到:“妃兒,你手這麽涼怎麽都不吭聲呢?”寬厚的手掌包裹住冰涼的小手,不停的著。
“玄羽對不起,讓你擔心了,下次不會了,我真的沒什麽不用太醫。”
Advertisement
“妃兒,你的臉這麽蒼白怎麽能不宣太醫,再者你剛剛小產不足數日,怎麽能不好好看看?妃兒你的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它是朕的,也是羽國的。”
歐妃了嚨,能說什麽呢?難道要說自己沒有小產嗎?
月黑,人靜,慢如一塊石頭的風化。
陳墨兒跌坐在地上靠著一堵破敗的牆壁,臉蒼白,慘白如紙。
蓮兒從外用一隻殘破的碗盛著半碗水走過來,輕聲低喚:“娘娘,喝口水吧!”
陳墨兒恍如沒有聽到,眼神一如既往般的死灰一片,若不是依稀看到口拂,隻怕很難不認為是一死。
蓮兒將碗放到一邊的地上,紅腫的雙眼焦急地看著陳墨兒,了好似什麽東西梗住了嚨,一個字也沒有說出,晶瑩璀璨的兩清流澆灌著紅腫的麵頰,落了一地哀傷,碎了寂寞的塵埃。
陳墨兒在等,在等無緣的孩子離開的,的心裏早已經是一片絞痛,不知道的腹中的胎兒是否已經死亡,但是的心是死的徹底,好似覺不到痛,又好似痛不生,一遍一遍的著自己還沒有凸起的小腹,卻不見一滴淚滴下,自從歐妃離開冷宮,就一直任由著奴才拖來拖去,最後坐在這件敞天的破房子裏,看著冷漠幽寒的夜不言不語。
Advertisement
二人一哭一靜,一坐一蹲,世界此刻安靜異常,針落也聞聲。
又過了半個時辰,蓮兒止住了哭泣,猛的站立起,大概是由於蹲的時間太長子搖了幾搖,剛定下子,蓮兒就拔下自己發髻的一銀長簪對著自己的脖子,自責的看向陳墨兒說:“娘娘,是蓮兒對不起您,蓮兒自知一條賤命死不足惜,娘娘求你正坐起來,小皇子在間不會寂寞的,蓮兒馬上就下去伺候小皇子。”
蓮兒的話就像冬天裏的一陣寒風,將失魂的陳墨兒喚醒過來,陳墨兒臉蒼白之態,看著悲慟的蓮兒,厲聲道:“你幹什麽?即便沒有你,孩子也不可能活,蓮兒你這麽做是想讓我這一刻就死在你前頭嗎?”
“娘娘,不是的,蓮兒不是這個意思。不是的!”蓮兒舉著簪子的手怵起來,話還沒有說完簪子就手掉在空哇的地麵。
“娘娘!嗚嗚上天為什麽要這麽對待娘娘?”蓮兒抱住陳墨兒,抬頭看著黑雲下月亮的虛影哭喊嘶吼。
皇宮中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後麵探出一個紅影。
從形上可以判斷是一名子,紅子奔行的極迅速,專挑那僻靜的地方躍而去,不過卻並沒遮掩的完,後有一道黑人隨其後,小心的保持這距離。
猜你喜歡
-
完結82 章
三生三世枕上書
如果執著終歸於徒然,誰會將此生用盡,只爲守候一段觸摸不得的緣戀?如果兩千多年的執念,就此放下、隔斷,是否會有眼淚傾灑,以爲祭奠?縱然貴爲神尊,東華也會羽化而湮滅。雖是青丘女君,鳳九亦會消逝在時光悠然間。只是不知
36.6萬字8 17279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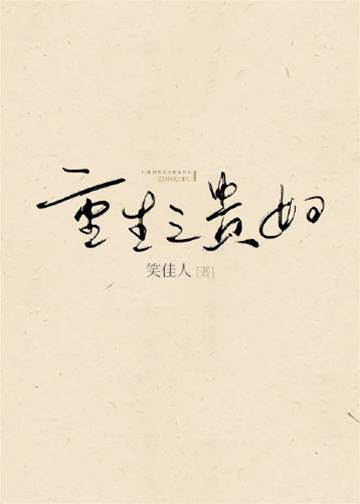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95765 -
完結250 章

邪王狂寵:紈绔小毒妃
一朝穿越被抓去睡了王爺 卻沒有想到,回到家里面居然要被退婚 沒關系,反正她已經睡了前任的王叔了 算起來,前任要叫她王妃嬸嬸哦…… 大半夜的王爺來襲,床榻之間,女主跪地求饒 “王爺,我錯了……”
45.5萬字8 26152 -
完結791 章

齊歡
她可以陪著他從一介白衣到開國皇帝,雖然因此身死也算大義,足以被後世稱讚。 可如果她不樂意了呢?隻想帶著惹禍的哥哥,小白花娘親,口炮的父親,做一回真正的麻煩精,胡天胡地活一輩子。 等等,那誰誰,你來湊什麼熱鬧。
153.4萬字8 96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