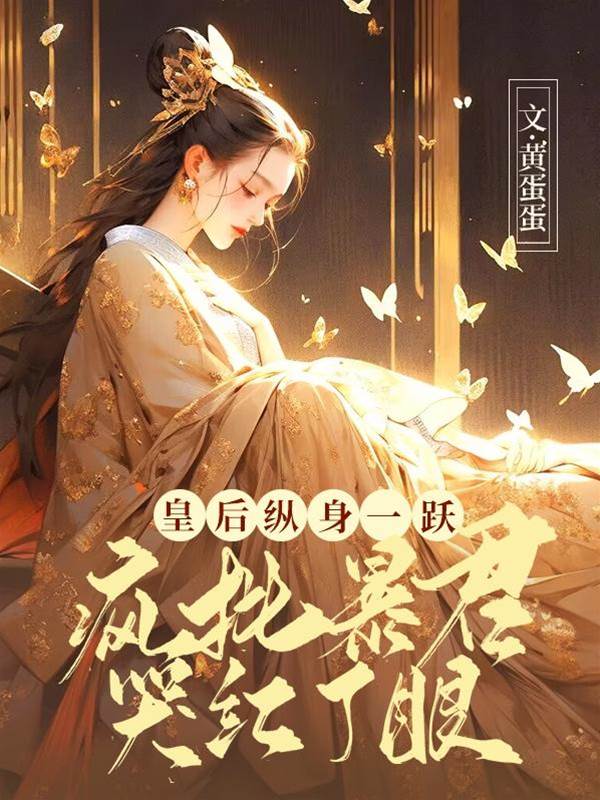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嫡女無憂》 第107章 一山豈能容二虎
泰和殿中靜的就好像沒有人般,但實際上宮裡的人很多,卻只是眼觀鼻,鼻觀心,無一人敢一,因爲太后娘娘此刻正面沉如水,整個人都散發出犀利之氣。無憂不敢擡頭,此刻只是微著,泰和殿的窗子全都打開,也沒有注意過一共打開了多扇的窗子,只覺得就是二皇子的室也毫沒有熱氣,好冷,明明剛剛沐浴過,可是覺到渾溼的難,殿裡的穿堂風吹過,覺得這點著薰香的室比殿外還有冷上三分。良久太后娘娘一聲嘆息:“你這孩子……”無憂心頭一,太后這話似乎有點妥協之意,不過心裡的懷疑更多:爲何太后娘娘會同意二皇子的要求,要知道皇子的正妃可是非同尋常的,不該是這個商賈之,以的出,莫說是正妃,就是側妃都是高攀,爲何太后娘娘不訓斥二皇子,反而有妥協之意,這很不尋常!無憂只管著低著頭,耳邊又響起太后的聲音:“先讓至宗事府司儀監接命婦廷禮儀訓練半個月,再觀後效吧!”“皇……”二皇子顯然一怔,還想說些什麼。“翼兒,蘇姑娘出民間,學些宮廷禮儀是必要的,免得日後失禮。”太后的語氣不容辯駁,但在其中也了些許鬆開的意思,隨即話題一轉:“你還沒有告訴皇,爲何傷了?”二皇子目閃了閃:“不過是不流的刺客,皇,你莫要爲翼兒擔心了。”太后又是一聲嘆息,也不再理會二皇子行刺之事,終於屈尊降貴的將目放在無憂的上。太后終於開口了,聲音聽著就是不悅:“你就是翼兒裡的無憂姑娘?”無憂心中一凜,老老實實的回答:“回太后娘娘的話,民正是。”說完話,還恭恭敬敬的給太后叩了三個頭,也就乖乖的閉上,因爲還真的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什麼,只能跪在地上也不。無憂明白太后的意思,是個商賈之,雖然母親是相府的千金,但的父親依然不折不扣是個商人!莫說皇室了,就是正常的宦之家,最講究也是門第了,誰願意娶商賈之。所以只能跪著,即使膝蓋已經微微發麻,也不能有任何表現。太后輕輕地說了一句話來:“倒是個懂規矩的。”無憂聽了這話,心下一沉:太后這是在訓吧?無憂不敢開口說什麼,只是又乖巧的叩了三個頭:“謝太后誇獎。”然後繼續跪在地上不。太后這時卻深看了無憂一眼,想起那日在慈寧宮的鎮定,心頭倒是有了主意,太后再度淡淡開口:“李嬤嬤,帶回慈寧宮,你先教教禮儀。”
Advertisement
“是。”李嬤嬤恭敬的。無憂的嗓子發乾,“謝太后恩典。”從頭到尾,無憂沒有看二皇子一眼:不敢,就怕太后又會多想什麼。誰知道二皇子卻住了,目閃,語氣淡淡地說:“記得每天來幫本宮換藥!”“是!”無憂的臉上不由自主的冒出熱氣,卻總算是肯擡頭來看他一眼了,目一,那深幽的目似乎穿墨黑的瞳孔,折進的心裡,心跳微浮,無憂眨了眨眼睛,似乎要將心頭的紛掃出。“記得好好學禮儀,莫辜負了皇的恩典。”見一雙澄若秋水般的眼眸著他,只是目裡的淡然冷漠卻如一把刀,將他一刀一刀剮開凌遲著。他幾乎是本能般要逃開這目了,他無法和這般的相視。“是!”無憂低頭,然後爬起來很自覺的跟著那李嬤嬤倒退出去,步伐卻略顯凌,範閒越和二皇子相,就越發的不能看他,人對無法看,無法掌握的東西,自然都有著不知名的恐懼。不可否認,無憂怕他,很怕他。因爲這人是所見過的所有人中最能藏緒,讓看不的男子,更駭人的是他有連都自嘆不如的聰慧,兩世爲人卻發現這人的一舉一都在佈局,而且那局布的環環相扣,毫沒有破綻。無憂再次對二皇子產生一種極其強烈的抗拒。待到無憂退出後,室有恢復了沉默。片刻之後,二皇子抿脣看向太后:“皇,蘇小姐醫高超,很有些手段,或許遇見,是翼兒之幸。”太后眼倏然亮了起來:“翼兒是說……”二皇子淡淡的道:“現在說還早,只是蘇小姐似乎有點眉,所以翼兒還請皇全!”太后微微沉凝:“待哀家好好想想!”皇子正妃,非同小可,即使他貴爲太后,也需慎重。當然了,以太后之尊,若是非要堅持,也不是不可,憑著太后的脾氣,真要想了此事,皇帝也無法可想,不過倒黴的人肯定不,估計人頭要掉了一地:太子之怒,伏百萬,皇帝不敢拿他老孃怎樣,自然要找些人出氣了。二皇子聽了太后的話後,掙扎著起,卻因爲作過大,而拉扯道上的傷口,鮮就那樣滲出來,驚得太后臉瞬間白了起來,怒聲:“翼兒,你這是幹什麼?”“皇,翼兒未曾求過你什麼,但這次翼兒求皇隨了翼兒的心願,善待蘇小姐。”說著,二皇子又咳嗽了幾聲,虛弱的子,越發顯得虛弱,臉面上蒼白一片。“正妃?”太后眼底閃過一掙扎,直視著眼前青年年輕卻蒼白的側臉上:“側妃還是可以商量的,只是正妃,你父皇已經有了屬意的人選?”
Advertisement
“皇,翼兒這子骨別人不知道,您還不知道,何苦再害人了,就蘇小姐吧!”窗外竄的夕,打在俊逸的青年的上,折出異常的飄忽氣息,太后尊貴的目中飛快的閃過一無奈之,帶著無人能解的沉痛,卻轉瞬間恢復正常。太后沉思片刻,輕輕皺眉,長長一嘆:“商賈之若想爲正妃,是需要點助力的,雖說那蘇小姐是相府的客,會點醫,但子貴嫺,若是能有什麼出的才華,哀家都也可以在你父皇面前說得起來。”二皇子心下一喜,面上卻未表毫,想也不想便低聲答道:“皇,您的賞雪宴會不是要舉行了嗎?若是趁著此次的機會讓父皇和衆人知道蘇姑娘雖然出商賈之家,卻纔華洋溢,琴棋書畫樣樣通,您到時在賞個恩典,是不是就不需要皇再多費神了。”太后目微閃,眉頭展平,輕聲道:“你倒是對有信心。”太后停頓了一下:“若是真能技羣芳,皇倒是就腆著這張老臉,與你父皇說道,說道。”二皇子這次彎著子,規規矩矩給太后行禮:“翼兒謝皇全。”他越是慎重,太后就越清楚他對無憂的上心,他不說,不言,因爲他清楚的知道,他的皇不是一個喜歡別人多話的人,更別說是爲了一個人而吵鬧不休,他強調的不是他對無憂的喜,而是無憂對他的作用——可以爲他治病。在太后的心中怕也只有這一點纔是看重的,或許爲了這一點,太后可以退上一退,而提起無憂的才氣,也不過是爲了太后找一個臺階下,既然需要找一個理由向皇帝開口,他自然要爲太后準備好,倒不是二皇子對無憂的才氣有多瞭解,而是他知道太后的賞雪宴,誰好誰壞,還不是太后的一句話,所以他纔出了這麼個主意。這就是皇家,什麼都要看看對方有什麼用,值不值那個價,皇家的每一個位子都是有價的,能出的起價錢才能上那個位子,不過他的這一刀應該也能付出那個價了吧:從清華殿帶出無憂倒還不需要他自殘,他不過是藉此機會定下婚事,順便留在宮裡養傷,解解心中的疑:清華殿裡的似乎不。太后和二皇子閒聊了幾句,見他眉眼之間漸漸的顯出疲憊之,心知他需要休息了,所以帶著一干的宮離開。二皇子靜靜地看著的背影,目中流出淡淡的思索,直到太后的影消失在二道殿門的屏風後面,才慢慢地收回自己的視線,閉上雙目,默默轉著思緒,臉上逐漸變得莫測起來。既不是太后面前鎮定中帶些憂慮的模樣,也沒有面對無憂時出的多變淡然,一雙清亮的眼睛此時卻深不見底。
Advertisement
他微微勾起脣角,輕輕的幾乎呢喃:“總算是等到這一天了,母妃,欠我們的,翼兒會一點一滴的討回來,害過您的人,害過我的人,翼兒一個都不會放過,即使拖著這殘破的子,我也要爲你討回公道……母妃……這只是開始……誰也不能阻擋我復仇的腳步……就是頭上的那位也不可以……”一種無奈和淒涼從他的上散發出來:“只是累了無憂!”想到無憂,想到最後他們或許要經歷的痛,腔裡像是有柄最尖利的尖刀在那裡緩緩剜著,汩汩流出滾燙的,生生得他仿若落進無的深淵,客戶四他不想就這樣放棄,他已經置冰冷的深淵太久了,一點落在他上的時候,就想要地抓住,再也不想放手。他想起記憶中的那份溫暖,眼中掠過一抹清晰可見的,隨即又恢復了那仿若大海般深不見底的。他對自己想要什麼,從來都很清楚,即使最後,那結果或許是他不能承,但是他卻還是要和老天爭一爭。清華殿“可惡!”宮貴妃手中的茶盞落在地上,片片的碎片閃著熒。宮裡靜悄悄的,沒有任何氣息,即使到都是伺候的宮,太監,卻無人開口勸上一句:因爲太多的經驗告訴他們,誰開口了,宮貴妃的怒火就會波及到誰,他們還惜項上的腦袋,誰也不想做那個不長眼的人。衆人跪了一地,屏住氣低著頭,這時二道的屏風外傳來低沉的男聲:“母妃。”機靈的宮,立刻收拾殿上的碎片,沒有發出毫的聲響,慢慢地推出殿外。宮貴妃吸了吸氣,揮手讓衆人退了下去:“謙兒,你來了。”三皇子瞧了宮貴妃一眼,語氣有些埋怨:“母妃,你今日何必招惹那蘇無憂?”三皇子想到蘇無憂三個字,頭就作痛。“招惹?一個商賈之,還需要本宮招惹?”宮貴妃一聲冷笑:“謙兒,若是這蘇無憂不除,我怕傲天的心就散了。”宮貴妃想到宮傲天,就有種恨鐵不鋼的味道,天下何無芳草,何必單一枝花,那個不材的侄子竟然爲了這麼個人,至海深仇不顧,爲耗盡了心神,上次爲了唆使無恨對付蘇無憂之事,竟然和大吵了一架。那個從來對著千依百順的傲天竟然拂袖而去,這對爲貴妃的是極大的侮辱,但是怪傲天,都是那個人的錯,迷了傲天的心智,這樣的狐蹄子,自然容不下了。宮貴妃宮出聲,了尊貴的貴妃之後,最惱恨別人忤逆的心意,不重視的意思,因爲已經上了這種一呼百應,別人對唯唯諾諾的覺,可是沒有想到傲天會忤逆的意思,這讓很惱怒,這讓想起那種還是宮時候不被人重視的覺。
Advertisement
所以宮傲天的忤逆讓生出了要除去蘇無憂這個狐蹄子的決定,巧在皇上正在惱怒蘇無憂:三皇子竟然要將溫泉借給蘇無憂的母親。皇帝是真的不痛快,他氣得牙酸酸的,他這個皇帝都沒蘇無憂的面子大,他怎麼能不氣?天子的氣,從來都是要用來消的,蘇無憂如此讓他沒臉,自然也就不必要活下去了。宮貴妃了皇帝的心意,趁此機會,進言,想要一舉除去蘇無憂,誰知道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竟被二皇子攪了局。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此鬆手。蘇無憂真的不能留,不說宮傲天,就是謙兒也對這個人頗爲欣賞,絕不能容許這樣的事發生,傲天和謙兒的心智決不能毫搖。眼下蘇家一時半刻還不能,無恨還要穩住,要助蘇啓明重掌蘇家,只有蘇啓明重掌蘇家,纔有能力和劉家鬥上一鬥,宮家雖然是皇商,不過這些年重頭戲都是劉家在把持著,宮家雖然說是天下第一首富,但是劉家百年基業哪裡是一個宮家十幾年來的這點基就可以搖的。真正的有錢人,是不會說有錢的,比起劉家,宮家差的不是一點兩點。只有蘇無憂死了,蘇啓明重掌蘇家,他們才能藉助蘇啓明和劉四爺的關係,和劉家搭上關係,這些年,他們試了很多門路,奈何劉家滴水不進,倒是聽聞蘇啓明和劉家在溫州城的合作一直很好,他們一定要藉助蘇啓明和劉家的關係,這也是宮傲天娶蘇家的目的。“母妃,你打草驚蛇了,只怕蘇無憂對我們已經設防,日後再想手,可就難了!”三皇子看了宮貴妃一眼:“若是母妃今天得手了也就 罷了,可是偏偏……”他是欣賞無憂的,但也只是欣賞,比起他的目標,比起他的萬丈雄心,比起他的海深仇,比起這大好山河,這點欣賞是微不足道的。他怒是因爲宮貴妃做事太過缺乏手段,那子七竅玲瓏心,只怕蛛馬跡中會探得一半的痕跡,這對他的大計來說,是極爲不利的。“知道我們和宮家的所圖謀之事。”宮貴妃對自己今日的行爲也是大爲不滿,對蘇無憂低估了。“哪一件事?”三皇子面沉了沉,他們和宮家所圖謀的時候可不是一件兩件,只是不知道蘇無憂說的是哪一件。宮貴妃整個人一怔,咬牙,惱怒:“沒說!”人本來潛意識當中在聽到對方模糊的話後,總是會很不自覺的向自己心中最害怕,最擔心,最介意的事上靠。宮貴妃當時只是以爲無憂知道和宮家,這麼些年來的謀報仇和謀奪皇位之事,現在聽聞三皇子這般說,才知道本就不清楚蘇無憂所說的是何事。這蘇無憂委實聰明,卻更是可惡,竟敢下套子個鑽,還真的非出除去不可。宮貴妃越想越是嘆無憂的聰明,實在是太過聰明瞭,居然能把人的心思看得如此,就是這個置皇宮這樣大宅院裡的人,都未能防的了,這讓他後背都爬滿了冷汗,這樣人既然不能爲所有,就不可以留在世上,免得日後養虎爲患,定要想個法子除去纔是——一山豈能容二虎呀。三皇子沒有再問無憂的事,宮貴妃也沒有再說無憂的事。蘇無憂這個人不能留,二人的心中都打定個主意,只是二人現在的心思除了在無憂上,還多加的一個二皇子,他今天的遇刺也太巧了點!宮貴妃和三皇子對了一眼,都看出對方眼底的深意。“母妃,謙先告退了。”三皇子站起:“二哥遇刺傷,我這個做弟弟的自然要去探一番。”三皇子說完之後,對宮貴妃行了一禮,他走了兩步,瞧見宮貴妃還微垂著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這些年養尊優,獨寵後宮,已經將母妃的玲瓏心漸漸的矇蔽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17 章
絕色煉丹師
她毒藥無雙,一朝穿越!坐擁煉丹神鼎,修煉逆天!誰還敢嘲笑她廢柴!想要謀奪家財?她就讓他家破人亡;你家爺爺是絕世高手?不好意思,他剛剛做了她的徒弟;你的靈寵舉世難見?不巧,她剛剛收了幾隻神獸;別人求之不得的丹藥,她一練就一大把!她風華絕代,輕狂傾天下,誰欺她辱她,必定十倍奉還!可就有一個腹黑邪魅、手段狠辣的男人跟她情有獨鍾,還問她什麼時候可以生個娃。她橫眉冷對:“滾!我們不熟!”
112.2萬字5 108844 -
連載769 章

嫡女嫁到,侯爺寵上癮
前世為他人鋪路,一場賜婚等來的卻是綠茶渣男成雙對,她滿門被滅葬身亂墳。死後六年浴火重生,昔日仇人各個權貴加身,她很不爽,發誓虐死他們!偏偏有個男人霸道闖入,她怒了,“滾,彆礙著我的路!”寧遠侯輕輕一笑,甚是邪魅張狂,“我知你瞧誰不順眼,不如上榻聊,為夫替你滅了。”不要臉!說好的淡漠孤冷生人勿近,怎麼到她這全變了!
124.1萬字8 86518 -
完結80 章
與兄書
永樂郡主謝寶真身為英國公府唯一的女兒,萬綠叢中一點紅,上有三位叔伯護陣,下有八位哥哥爭寵,可謂是眾星捧月風光無限。直到有一天,家里來了位冰清玉潔從未謀面的九哥,從此平靜的英國公府內暗流涌動。這位九哥什麼都好,就是患有啞疾、身世悲慘。那日初見,小郡主以為九哥是父親背叛母親所生的私生子,故而百般刁難,小野貓似的瞪著他:“以后不許你靠近主院半步,不許出現在我眼前!”謙謙白衣少年發不出聲音,朝著小郡主頷首低笑,只是那笑意從未照入他的眼底。再后來,這個啞巴九哥將某位紈绔堵在深巷中,褪去溫潤如玉的偽裝,露出猙獰的獠牙。他冷眼盯著地上被揍得半死不活的紈绔子弟,一貫緊閉的唇終于開啟,發出嘶啞低沉的聲音:“以后你哪只腳靠近她,我便打斷哪只腳;哪只手觸碰她,我便斷了哪只手;多看一眼,我便挖了一雙眼,多說一句,我便割了你的舌頭!”永樂郡主這才明白,高嶺之花原來是朵不好惹的黑蓮花!閱讀指南1.女主嬌氣略作小可愛,男主裝病大反派,心狠手辣非善類,只對女主一人好;2.男女主無血緣關系。因情節需要朝代架空,勿考據.
27.6萬字8 18986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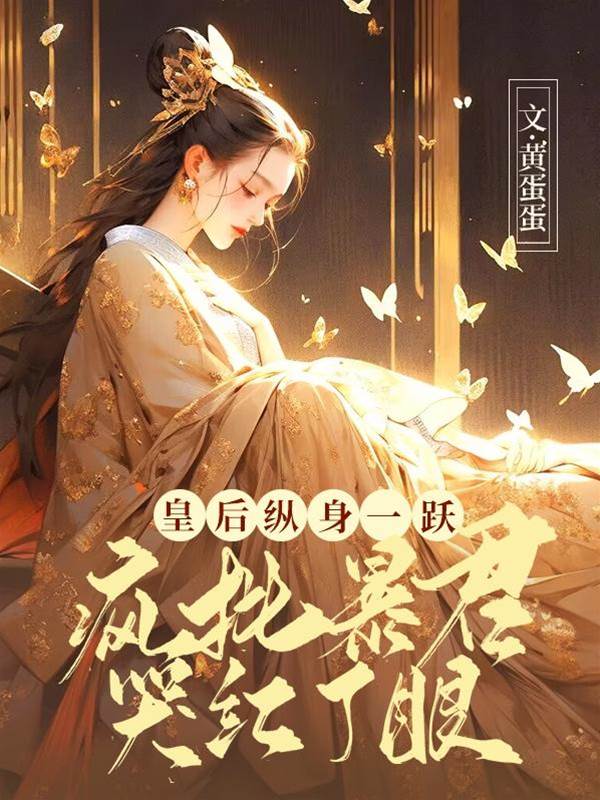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6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