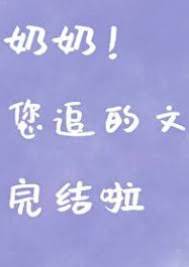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撩到你心動》 第71章 第 71 章
了夏, 外面的空氣每天像個大蒸籠,熱得人不過氣。
由于室外溫度太高,楊舒最近很出門, 平時工作人員會把一些要修的圖發來給。
養胎之余, 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寶寶已經四個多月了, 肚子有明顯的隆起。
一個人在家姜沛不放心, 白天做飯的阿姨在邊上陪著。
方姨是姜沛專門請來給楊舒做飯的阿姨, 之前照顧過不孕期的婦人, 在這方面很有經驗。
平時話不多,但勤快又, 楊舒本就是好相的, 幾個月下來兩人便絡起來。
這天傍晚, 楊舒在書房里忙工作, 方姨敲門進來,給端了些水果:“太太, 你在電腦前坐了快兩個小時了, 歇會兒吧, 吃點東西。”
楊舒捻了顆葡萄:“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吃葡萄, 生下來的寶寶眼睛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方姨笑:“葡萄哪有那麼大的作用,主要還是看傳的。不過你和先生眼睛都大,將來生下來的寶寶,肯定也是漂漂亮亮的大眼睛。”
“對了。”方姨問, “今天先生是不是就出差回來了, 晚上做飯的時候我多做點。”
楊舒點頭:“應該是今天。”
自從楊舒懷孕,姜沛很出差,但有時候還是不可避免要到跑。
前幾天, 他出差去了H市,說是今天回來。
方姨看時間也不早了,便道:“那太太休息一會兒,我去準備晚飯的食材。”
方姨出去后,楊舒又吃了點水果,撈起手機打算問姜沛什麼時候回來。
下面似乎約傳來方姨的聲音:“先生回來了。”
楊舒眸中閃過一抹喜,起朝外面走。
Advertisement
扶著欄桿從樓梯上下來,看到姜沛在門口換了拖鞋。
他一剪裁得的西裝,材拔高大,抬眉看過來時,眼中淬著一笑意,吊兒郎當道:“看來家里有人盼著我回來呢。”
楊舒淡定走過來,指指自己的肚子:“那大概是寶寶,反正不是我。”
“是嗎?”姜沛笑著單手攬過的腰,在肚子上了把,“我還以為,是寶寶的媽媽想我。”
楊舒臉頰紅了些,看到他額頭有汗,抬手幫他了下,這才注意到他穿著西裝外套。
楊舒道:“大夏天你穿那麼厚干嘛,趕掉吧。”
說著要幫他外套,姜沛握住的手,低聲音道:“干嘛呢,我剛回來就迫不及待手腳?”
方姨還在廚房呢,也不怕被聽見,楊舒無語地瞪了他一眼。
姜沛笑說:“是有點熱,自己在客廳待會兒,我先去樓上洗個澡,晚點咱們再親熱。”
頓了頓,他補充,“當然,你想跟我一起上去洗也行。”
他剛回來就極其不正經,楊舒無語地推他:“你趕去,上全是汗!”
姜沛去了樓上,楊舒獨自去客廳的沙發上坐著,順手拿起旁邊的一本育兒書翻閱。
第一次做父母,和姜沛也沒經驗,都張的,關于育兒和孕婦方面的書籍買回來不。
楊舒工作時間不長,閑下來的時候會隨便看看。
正翻閱著,想起剛才的景,還是覺得哪里不太對。
姜沛今天怪怪的。
今天外面三十二度,他回來居然還穿著西裝外套。
如果是因為車里開了空調溫度低,可他上明明出著汗,那就很不正常了。
琢磨著,楊舒放下書往樓上臥室里去。
輕輕推開門進去,屋里沒人。
Advertisement
楊舒向浴室的方向,緩慢走過去,握著門把手把門打開。
里面姜沛剛把外套下來,出里面的黑T恤,他右手的手臂上纏著繃帶,好像是傷了。
姜沛聽見開門聲回頭,看到眼皮一跳,右臂自然往后面藏,冷峻的臉上神坦然,語調懶懶的:“怎麼進來了?”
楊舒忙上前抓住他那條手臂,臉上寫滿了擔憂:“這里怎麼了?”
姜沛嘆了口氣:“沒什麼大問題,就是被告方狗急跳墻想毀掉證據,我一不留神被劃了一道,小傷,那些人早被警察帶走了。”
楊舒看著他的手臂有點著急:“怎麼還會遇到這種事呢,去醫院沒有啊,其他地方還有沒有傷到?”
說著就掀開他的服檢查別。
姜沛笑著攬過:“沒有了,真的就是劃了道小口子。”
楊舒看到洗手臺上放著醫藥箱,準備好的藥和繃帶在邊上放著,不太放心地問:“自己上藥行不行啊,不然還是去醫院吧。”
“真不嚴重,已經問過醫生了,就是皮傷。”姜沛無奈輕笑了聲,倚著柜子,手臂過去,“不信你看看,順便幫我換點藥,重新包扎一下。”
楊舒幫他把手臂上纏著的繃帶解下來,手臂上一條明顯被利傷到的劃痕。
傷口先前已經理過,止了,但看起來還是有點目驚心。
楊舒小心翼翼幫他清理一下周邊,重新上了藥,再用繃帶包扎起來。
全程低著頭不吭聲,明顯很不高興:“出差的時候還好好的呢,回來就這樣了,你們這個工作是不是不太安全啊。”
“哪有你說的那麼嚇人,律師跟其他工作是一樣的,這都是極數才會遇到的況,也是我一時大意,你怎麼因為這個就懷疑我工作的安全問題了?你們攝影的時候,不是也會跟模特、品牌方起糾紛?”
Advertisement
姜沛說著,又安地握住的手,“我以后會謹慎一些,不再出這樣的意外了,跟你保證。”
楊舒把手回來:“傷口不能水的,你洗澡的時候要小心點。淋浴下面容易濺水在手臂上,不然你還是泡澡吧,我去幫你放點熱水。”
徑直走去浴缸那邊,幫他調好熱水放滿。
一轉頭,姜沛在后面站著,目灼灼著,服還穿著。
猜測他可能是手臂傷,不太方便,楊舒上前幫忙。
姜沛難得被這麼照顧,有些寵若驚,彎腰低頭配合把上面的T恤掉。
剩下面的子,楊舒突然不了:“你自己單手應該是可以的。”
姜沛牽著的手,落在皮帶扣上:“哪有幫忙幫一半的,善始善終知不知道?”
楊舒只能著頭皮幫他。
“好了,你快去洗。”假裝沒有看到他上的反應,轉準備出去,卻被姜沛從后面抱住,“我還著傷呢,不幫我洗?”
掙扎了一下,輕輕推他:“我是孕婦,照顧你不合適吧?”
“或者你跟我一起洗,我照顧你也行。”他吮吻的耳垂,“老婆,我想你了。”
他聲音低啞,抱著時上溫度很高,是楊舒太過悉的一種狀態。
楊舒臉頰不覺有些熱,抿了下,提醒他:“寶寶能聽見的,你別說話。”
“咱們倆好,說明這是一個充滿□□。如果寶寶真能聽見,那麼此刻應該到無比驕傲和幸福。”
“……”
楊舒不想跟他鬼扯:“你趕先去洗澡,我去看看方姨今晚做什麼飯。”
從浴室里出來,楊舒拍了拍發燙的臉頰,下樓去客廳。
進廚房跟方姨聊了兩句,繼續去沙發上坐著看書。
Advertisement
不多時,姜沛從樓上下來,穿著黑T恤,材瘦高,眉眼清雋,頭發上沾著水汽,干凈清爽許多。
他朝這邊走過來,看著楊舒時角一勾,帶著慣有的。
楊舒抬眸:“你怎麼洗頭了,手臂上的傷沒事吧?”
“沒事。”姜沛在旁邊坐下,順勢將人抱在懷里。
楊舒檢查了一下他手臂上的繃帶,確定沒沾水才松了口氣:“最近還是要小心一些的,不能大意。”
姜沛應了聲,掌心落在腹部:“最近在家還好嗎,寶寶有沒有折騰你?”
楊舒笑著搖頭:“很乖的,我最近偶爾能到胎呢,很奇怪,不是一般二十周才會有胎嗎,我這才十八周。”
方姨做好晚飯從廚房出來,聽到這話笑著接:“都是因人而異的,太太比較瘦,胎知的早一些也正常。”
楊舒不好意思地從姜沛懷里起來。
方姨早習慣了這畫面,見怪不怪,跟姜沛和楊舒說晚飯已經做好,自己該下班了。
收拾東西離開,把時間和空間留給他們夫妻兩個。
自從懷了孕,楊舒的作息很規律,晚飯后和姜沛在客廳稍微坐了坐,便回房休息。
這幾天他出差在外,兩人許久沒見,躺下后楊舒依賴地鉆進他懷里,漸漸地,覺邊男人的呼吸有些沉。
楊舒不免又想起剛剛浴室里的畫面,還未回神,姜沛突然過來,封上的。
楊舒嚶嚀一聲,勾住他的脖子,回應他的熱。
好一會兒,姜沛放開,漆黑雙瞳一無際地深沉。
他結了,又懲罰般在上輕咬一口,啞聲道:“不早了,睡吧。”
醫生說過了三個月,胎兒穩定就能有夫妻生活,只要小心一些就沒問題。
這件事,姜沛曾經反復找醫生確認過。
不過如今都四個多月了,姜沛沒有向楊舒提過這方面的要求。
楊舒偶爾半夜醒來,迷迷糊糊會聽到浴室有水流聲。
他就是上逞能,行為上比還要謹慎幾分。
楊舒明顯覺他好像在克制,猶豫了一下,咬咬下,在他懷中小聲道:“其實,我可以幫你的。”
頓了頃,又道,“你要是怕傷到我,別的法子也行。”
姜沛垂眸看一眼,楊舒也恰好掀起眼睫。
兩人視線相撞,赧地避開,把臉重新埋進他懷里。
姜沛慵懶地笑了聲,湊在耳畔,低沉著嗓音道:“急什麼,會有你還回來的時候。”
猜你喜歡
-
完結104 章

最愛你的那十年
從來吵著要走的人,都是在最後一個人悶頭彎腰拾掇起碎了一地的瓷碗。而真正想離開的時候,僅僅只是挑了個風和日麗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門,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賀知書于蔣文旭來說是空氣是水,任性揮霍起來時尚不覺得可惜,可當有一天當真失去的時候才悔之晚矣。 “你所到之處,是我不得不思念的海角天涯。” BE 虐 慎入 現代 先虐受後虐攻 情深不壽 絕癥 玩野了心的渣攻&溫和冷清的受
13.1萬字8 14451 -
完結68 章

軟刃
言微靜悄悄嫁給了城中首富秦懷鶴。 她很低調,懷著秦懷鶴的孩子,為他居屋守廳堂,洗手做羹湯,卻換來了他不痛不癢的一句調侃:“她就這樣,言微人輕嘛。” 言微留下一句話,再也沒有回頭。 “他什麼都有,除了心肝肺。” 言微走后,秦懷鶴才知道,她曾經是他的捐贈對象,來找他,不過是為了“報恩”。 從此,一直在云端上行走的秦懷鶴再也看不到如她那般,心藏柔刃披荊斬棘的女人。 秦懷鶴在雨夜里,一把攬住她的腰肢,眸光深幽,“親一下,我把心肝肺掏出來給你看看。” 言微紅唇輕牽,“秦懷鶴,算了。” 友人:“鶴哥,心肝肺還在嗎?” 秦懷鶴:“滾蛋!” 他什麼都有,除了老婆和孩子。 一年后,秦懷鶴端著酒杯斂眸看著臺上神采飛揚的女人,與有榮焉,“我孩子她媽。” 言微明眸善睞,答記者問,“對,我單身。” 會后,他堵住她,眼圈泛了紅,“言總越飛越高了。” 言微輕笑,“人輕自然飛得高,還得多謝秦總當年出手相救。” 秦懷鶴眸子里那層薄冰徹底碎了,欺上她眼尾的淚痣,“你就這麼報恩?我救過你,你卻從未想過回頭救救我。” 秦懷鶴的微博更新一句話: 【吾妻言微,我的心肝肺。】 #深情千疊斷癡心妄想,沒心沒肺解萬種惆悵# #我不只要歲歲平安,還要歲歲有你。# 溫馨提示: 1、不換男主,he。 2、歲歲是寶貝,很重要。
21.7萬字8.09 30464 -
連載1666 章

冥王崽崽三歲半
華國第一家族霍家掌權人收養了個奶團子,古古怪怪,可可愛愛,白天呼呼睡,晚上精神百倍!大家在想這是不是夜貓子轉世投胎?冥崽崽:本崽崽只是在倒時差,畢竟地府居民都是晝伏夜出呢!人間奶爸:我家崽崽想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通靈家族繼承人:要不讓崽崽帶你們地府一日游?提前了解一下死后生活?冥王: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312.4萬字8.18 34643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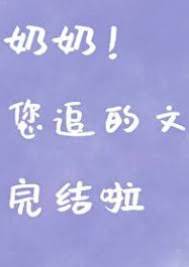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3195 -
完結719 章

封少,你家小祖宗馬甲掉了
注孤生的封二爺有一天對所有人宣布:“爺是有家室的人了,爺的妞性子柔,膽子慫,誰敢惹她不開心,爺就讓他全家不開心。”然後——“這不是拳打華北五大家、腳踩華東黑勢力的那位嗎?”“聽說她還收了一推古武大族子孫當小弟。”“嗬,你們這消息過時了,這位可是身價千億的國際集團XS幕後大佬。”然後所有人都哭了:二爺,我們讀書不算少,你不能這麽騙我們啊。而被迫脫馬的祖盅兒隻想:這狗男人沒法要了,日子沒法過了,老娘要滅世去!
126.9萬字8.18 90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