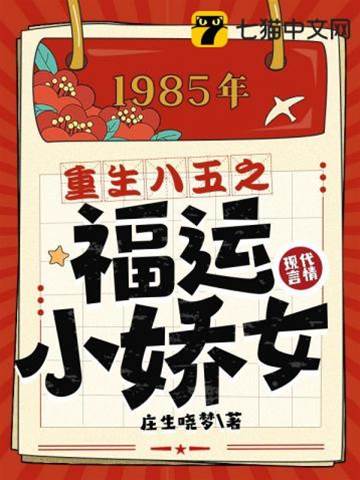《撿來的夫人是條魚》 第三章
像是解除封印一樣不過這是好事,至能聽得懂男人說什麼。
現在兩人只能用肢語言進行一些簡單流,云安安有點心累,好在整理了一些信息出來,收留的男人貌似是個大佬能輕而易舉的給弄了份。
一旁的李應看了眼時間可以登機了,手過去想要扶著云安安的椅推到飛機上,被檀革水阻止了李應有點懵。
云安安做在頭等艙,看著遠離地面的飛機心一陣自閉,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窗外的地面越來越遠,取代的是夜晚黑的云層。
云安安想著躺下睡一會整個人都是迷迷糊糊的,一邊空姐有眼力見上前將座位放倒,不知道為什麼從變人開始力就直線下降,好像永遠睡不夠。
過了不知道多久,到輕的作解開安全帶,將抱了起來后背抵著堅的膛穿過寬闊的大廳,又把放在座位上。
安全帶咔噠的一聲,云安安不舒服的了,發現都不了過了一會兒,突然間發燙渾上下都在囂著水分。
檀革水明顯到懷中的人,升高的溫紅撲撲的小臉上滿是汗水,云安安對水的到了臨界點覺在沒有水就要干了。
云安安雙手晃,到一旁固定住的水杯,對水的已經達到極致。
檀革水將杯子拿出來到了杯水喂給云安安,干的嚨接到水分滋潤,像是久旱逢甘霖。
但是這點水分本不夠云安安的需求,檀革水皺了皺眉將冰箱里僅有的兩瓶水喂給云安安。
云安安難耐的喝著水還不夠遠遠不夠,不過兩瓶水下肚拉回了一些理智人是清醒了一些。
好在車子停在了,一棟別墅門口管家在門口等候。
Advertisement
見到主人家抱著一位明顯生病的,平常穩重的腳步顯得有些凌。
“周叔倒杯水上來,黃醫生過來一趟云朵發燒了。”
周叔雖然年紀大了但是做事確有條不理,聽到吩咐趕去人幫忙。
檀革水抱著人放在客房里,上飛機前他就打電話吩咐人打掃客房,好在每天客房都有專門的人清潔現在剛剛好用到。
云安安腦子又開始模糊起來,小臉滿是不正常的紅,檀革水將水杯遞過去覺到水分的云安安,舒服的蹭了蹭檀革水堅的膛。
將兩升水一飲而盡,云安安終于緩了過來,腦子里混沌的思緒漸漸散開。
才發現自己在一個陌生的房間里,床邊圍一堆從來都沒有見過的人。
檀革水將一溫計塞進云安安里,用手帕拭這被汗的頭發。
周叔在一旁看著心驚膽戰,他在檀家也有幾十年了從來都沒有看見這位爺照顧過誰,這還是第一次看著自家爺生疏的手法。
周叔雖然是老人了,但是有些事還是拎得清也沒敢問這個突然出現的孩。
云安安躺在床上頭枕這檀革水的手臂,剛想起來挪一下,就被一只大手按住不能彈里叼著溫計,一旁急急忙忙趕過來的黃醫生敲了敲門。
“請問我可以進來嗎?”
“進來吧”
檀革水將測好溫度的溫計拿了出來遞給黃醫生,好在只是有點發燒,工有限黃醫生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由于明天云朵還要全面檢查,黃醫生怕影響檢測結果沒有開藥,只是叮囑了多喝水。
檀革水起送黃醫醫生,房間里只剩下云安安一人,本來還想在瞇一會可惜白天睡飽了,現在就再也睡不著了。
Advertisement
雖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顯而易見離自己的小海灘十萬八千里遠,聽見男人要帶去醫院檢查,云安安本能的抗拒,還是條魚萬一檢查出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被人送到研究所變保護那就糟糕了,云安安發愁想來想去也沒有思緒。
魚尾幻化雙實,云安安好奇的了,雙干燥的皮和空氣中干燥的氧氣,云安安不適的看了看上都起皮了。
云安安作為致的一條魚,在海里的時候還經常用藻類給魚尾做保養,從來都沒有出現起皮的狀況,這還是頭一次新奇看著自己上的死皮。
過了一會就瞄到了床邊的椅,椅上有特制的扶手云安安很輕易的爬上椅,駛進浴室眼就是一個巨大的浴缸。
云安安放滿了水將自己整個人都泡進去,漂亮的雙化銀的大尾,尾上明的鰭紗泡在大魚缸里。
云安安緩過勁的將自己整個人塞進魚缸里,可惜魚缸太小了不能游兩圈。
只能泡泡水,檀革水的手機顯示椅被啟點開定位發現在浴室,看了眼客房浴室的智能管家顯示按浴缸正在作業。
泡了兩個多小時,檀革水皺了皺眉頭,視頻會議里主管戰戰兢兢的匯報,看見大老板的臉越來越沉小心翼翼的匯報生怕踩到雷。
檀革水線下沒有什麼心思開會,已經泡了兩個小時了,洗澡也用那麼久吧,聽完季度匯報快速敷衍的結束會議。
視頻外的主管還有一堆要定奪的方案,但是還是沒敢說看著越來越冷漠的大老板掛掉視頻會議。
來到云安安的房門前敲了兩下,完全沒有反應又等了一會,拿出備用鑰匙打開門。
Advertisement
果不其然房間里空的沒有人,檀革水敲了敲浴室的門,云安安整個人沉水底,突然間聽見敲門聲嚇得魂都要飛了,慌的放水大尾撲騰的帶了一地水。
好在隨著水流的消失后雙變回來了,隨意的裹上浴巾打開浴室門就看見男人在外面等。
檀革水將椅推到房間地毯上,看著一片狼藉的浴室,到都是水地板上,浴室還做了隔絕水的隔斷連門口的地毯也被水打。
這是在浴室打水仗嗎?檀革水頭疼不已,他從小獨立嚴謹但是也沒有理熊孩子惹事的經驗。
“我讓李應請了個護工明天到,下次要泡澡或者有需要記得找護工”
“你這樣太危險了,萬一出了什麼事怎麼辦”
一旁的云安安看著滿地狼籍有些心虛,新來還有些發怵請護工萬一被發現了怎麼辦,眼神心虛的飄兩人僵持著,看了眼時間這個點周叔估計都已經睡了。
檀革水看著心虛的扣手指甲的孩,知道沒有聽進去,還想說什麼看見白皙細的手心被扣的通紅,皺了皺眉頭拉開被倍折磨小手。
檀革水認命的走進浴室收拾殘局,只是這小姑娘的破壞力也太強了,天花板上都是水漬檀革水頓了頓手上的作,不聲的收拾這殘局。
“以后我讓人將浴室的警報調兩個小時”
云安安點了點頭表示聽明白了,檀革水看著乖巧的點了點頭,剛想說什麼就看見云安安在外的肩膀上一塊塊紅痕。
像是被誰吻過一般曖昧又引人遐想,云安安到火熱的視線有些不自在著手臂。
檀革水將備用的藥膏放在床頭,看著小姑娘的拘謹和不知所措紳士的退了出去。
Advertisement
將門輕輕關上,他不是慈善家自然不會費那麼大力氣去收留一個孤,檀革水的邊不缺人可以說是花叢中過,片葉不沾。
一見鐘對于他來說等于天方夜譚,不過現在事好像超出了控制。
云安安一覺醒來,一早在門口等候的護工,聽見房門里的靜敲了敲門。
餐廳里的周叔看見云安安下來,趕忙湊上去雖然不知道自家爺,為什麼帶回來一個聾啞殘疾人,云安安看著桌上的盛的早餐。
心里一點郁悶也煙消云散,轉了一圈沒有看見男人,周叔看見椅上面容致渾散發脆弱的孩,一眼就明白在找什麼。
“檀先生,早上去公司了走的時候,吩咐了不用云小姐起床”
“大概下午三點回來,云小姐會手語嗎”
云安安猛地聽到一堆話,消化了半天才差不多理解,開心的看著滿桌東南西北各早餐。
這些都是的了,化人這兩天上頓下頓都是白粥,沒有看見一點好歹也是食。
周叔盛了一碗瘦粥遞給云安安,雖然也是清湯寡水的但是至有了啊。
吃過飯以后沒有什麼事周叔提出來要帶去花園里散散心。
云安安點了點頭護工推著椅,眼是就是一片驚艷紅,院子里中滿了卡羅拉玫瑰現在剛好是在花期,紅艷熱烈的玫瑰散發迷人的香氣。
一整個小花園全部是心培育的玫瑰,讓人忽視其他的,云安也喜歡花看慣了海底奇形怪狀的珊瑚和五六的小丑魚。
突然間看見一片玫瑰花園,讓人心一旁的周叔看見眼里殘留的驚艷,不免有些驕傲這些花雖然不是先生親自打理的,但也周叔心呵護的人老了就喜歡花花草草。
在記憶里好像看過這種熱烈盛開的花朵過,手輕輕著紅絨般的花瓣,這一看就是主人家的心頭好也不知道可以摘一朵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161 章
他養的小可愛太甜了
他是商界數一數二的大人物,眾人皆怕他,隻有少數人知道,沈大佬他……怕老婆! 沈大佬二十八歲以前,對女人嗤之以鼻,認為她們不過是無能,麻煩又虛偽的低等生物。 哪想一朝失策,他被低等生物鑽了空子,心被拐走了。 後來的一次晚宴上,助理遞來不小心摁下擴音的電話,裡麵傳來小女人奶兇的聲音,「壞蛋,你再不早點回家陪我,我就不要你了!」 沈大佬變了臉色,立即起身往外走,並且憤怒的威脅:「林南薰,再敢說不要我試試,真以為我捨不得收拾你?」 一個小時之後,家中臥室,小女人嘟囔著將另外一隻腳也塞進他的懷裡。 「這隻腳也酸。」 沈大佬麵不改色的接過她的腳丫子,一邊伸手揉著,一邊冷哼的問她。 「還敢說不要我?」 她笑了笑,然後乖乖的應了一聲:「敢。」 沈大佬:「……」 多年後,終於有人大著膽子問沈大佬,沈太太如此嬌軟,到底怕她什麼? 「怕她流淚,怕她受傷,更……怕她真不要我了。」正在給孩子換尿布的沈大佬語重心長的
105.2萬字8 127617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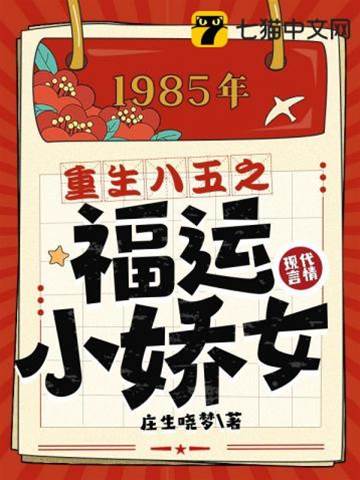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1891 -
連載552 章

妻女死祭,渣總在陪白月光孩子慶生
【重生+雙潔+偽禁忌+追妻火葬場】和名義上的小叔宮沉一夜荒唐后,林知意承受了八年的折磨。當她抱著女兒的骨灰自殺時,宮沉卻在為白月光的兒子舉辦盛大的生日宴會。再次睜眼,重活一世的她,決心讓宮沉付出代價!前世,她鄭重解釋,宮沉說她下藥爬床居心叵測,這一世,她就當眾和他劃清界限!前世,白月光剽竊她作品,宮沉說她嫉妒成性,這一世,她就腳踩白月光站上領獎臺!前世,她被誣陷針對,宮沉偏心袒護白月光,這一世,她就狂扇白月光的臉!宮沉總以為林知意會一如既往的深愛他。可當林知意頭也不回離開時,他卻徹底慌了。不可一世的宮沉紅著眼拉住她:“知意,別不要我,帶我一起走好嗎?”
101萬字8.33 184598 -
完結179 章

灼灼浪漫
大雨滂沱的夜晚,奚漫無助地蹲在奚家門口。 一把雨傘遮在她頭頂,沈溫清雋斯文,極盡溫柔地衝她伸出手:“漫漫不哭,三哥來接你回家。” 從此她被沈溫養在身邊,寵若珍寶。所有人都覺得,他們倆感情穩定,遲早結婚。 有次奚漫陪沈溫參加好友的婚禮,宴席上,朋友調侃:“沈溫,你和奚漫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沈溫喝着酒,漫不經心:“別胡說,我把漫漫當妹妹。” 奚漫扯出一抹得體的笑:“大家別誤會,我和三哥是兄妹情。” 她知道,沈溫的前女友要從國外回來了,他們很快會結婚。 宴席沒結束,奚漫中途離開。她默默收拾行李,搬離沈家。 晚上沈溫回家,看着空空蕩蕩的屋子裏再無半點奚漫的痕跡,他的心突然跟着空了。 —— 奚漫搬進了沈溫的死對頭簡灼白家。 簡家門口,她看向眼前桀驁冷痞的男人:“你說過,只要我搬進來,你就幫他做成那筆生意。” 簡灼白舌尖抵了下後槽牙,臉上情緒不明:“就這麼在意他,什麼都願意爲他做?” 奚漫不說話。 沈溫養她七年,這是她爲他做的最後一件事,從此恩怨兩清,互不相欠。 那時的奚漫根本想不到,她會因爲和簡灼白的這場約定,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丟在這裏。 —— 兄弟們連着好幾天沒見過簡灼白了,一起去他家裏找他。 客廳沙發上,簡灼白罕見地抵着位美人,他被嫉妒染紅了眼:“沈溫這樣抱過你沒有?” 奚漫輕輕搖頭。 “親過你沒有?” “沒有。”奚漫黏人地勾住他的脖子,“怎麼親,你教教我?” 衆兄弟:“!!!” 這不是沈溫家裏丟了的那隻小白兔嗎?外面沈溫找她都找瘋了,怎麼被灼哥藏在這兒??? ——後來奚漫才知道,她被沈溫從奚家門口接走的那個晚上,簡灼白也去了。 說起那晚,男人自嘲地笑,漆黑瞳底浸滿失意。 他凝神看着窗外的雨,聲音輕得幾乎要聽不見:“可惜,晚了一步。”
30.6萬字8.18 200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