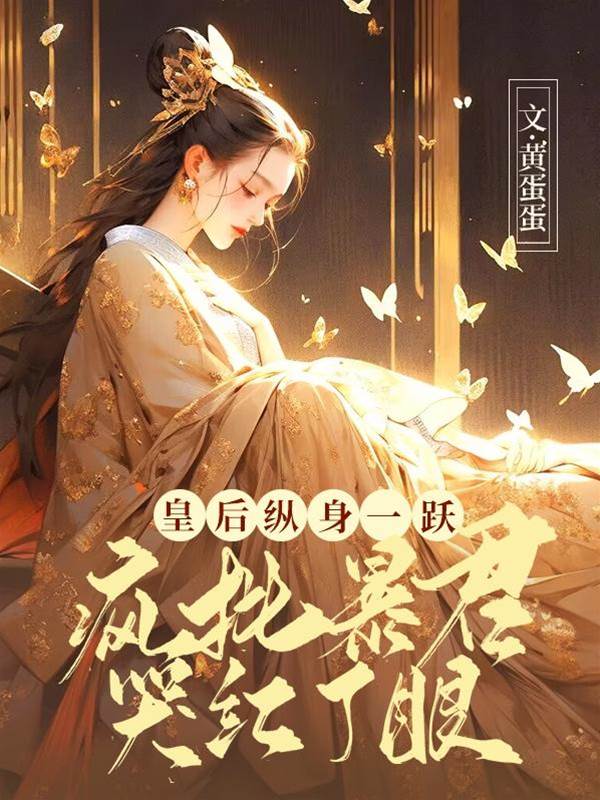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劍擁明月》 第52章 小十七
夜濃黑,純靈宮的宮娥卻不敢進殿中點燈,鶴紫心知公主今日了辱,此時必定心中難,晚膳未至,暫不敢進殿打擾,只得吩咐其他宮娥將外頭的石鶴燈籠柱全都點上,如此一番燭映窗欞,也不至于殿中太過漆黑。
外頭人影拂,宮娥低聲耳語,模模糊糊地傳殿,但榻上的商絨充耳不聞,手中一刃寒粼粼,輕抵上自己的手腕。
冰涼的輕脆弱纖薄的皮,握著刀柄的手控制不住地抖,恍惚間,想起折竹腕上那道經年的舊疤。
眼淚砸在刃上,細微的聲音撥弄著脆弱敏的神經。
已見過外面的朝,落日,冬日的雪,春夜的雨,綿延巍峨的蒼山,蜿蜒奔流的江河。
已擁有過此生最好,最的時,再回到這四方紅墻之,好似在這里的每一刻,都是比以往更為劇烈的折磨熬煎。
“公主,您該用晚膳了。“
鶴紫推門進來,卻不敢殿,只隔著那道簾子,在外頭小心翼翼地提醒。
商絨握著刀柄的手滿是汗意,失神般的,許久不說話。
吃過的人,如何能再心甘愿地茹素?
“鶴紫。”
鶴紫終于聽見簾后的公主輕聲喚。
“我要沐浴,”
聽見公主說,“去蘭池殿沐浴。”
鶴紫心中詫異,明明公主已許久都不肯去蘭池殿,怎麼今日……
卻也不敢多問,只應了一聲,忙喚來人,備好各項沐浴用,又殿去扶起公主,一行人到了后殿。
溫泉池,滿室氤氳。
鶴紫才要將花瓣撒池中,卻驀地抬頭見公主那雙空漆黑的眼,才驚覺自己這滿手的花瓣,本是囿困公主數月的夢魘。
Advertisement
立即命人將花瓣撤下,才要服侍公主解浴池,卻見公主搖頭。
鶴紫只好行了禮,帶著一眾宮娥退出殿外。
殿水聲流,一道又一道的紗幔在熱霧中微微晃,商絨看著那四四方方的浴池,一步一步走近。
袖間藏的匕首此時被握在手中,那是唯一抓得住的,屬于天高海闊,屬于他的東西。
薄刃割破手腕,殷紅的鮮流淌浸雪白的袖,滴落在可鑒人的地磚,赤足水,殷紅的也隨之在水波里暈開。
靠坐在浴池一角,烏黑的發尾浸在水中,腦海里又是那道聲音的主人在這池中嗚咽哭喊,那許多雙在那子上與頭上的手,好似也在這一瞬無形地強著一般。
的下去,慢慢的,整個人都沉水中,溫熱的水不斷涌的口鼻,的心肺。
不掙扎,卻閉起眼。
——
絳云州·櫛風樓。
“十七,你怎麼出來的?”
第十五與其他幾位護法正在廳中議事,忽見那黑年從門外進來,便有些詫異。
也不知是誰放出了蜀青造相堂藏有一批財寶的消息,他們三人帶著十七趕回櫛風樓時,江湖中已在傳造相堂財寶已落櫛風樓手中。
這一月來,不知有多江湖雜魚聚集起來圍攻櫛風樓,而第二與第四,第五遠在玉京,第七與第八也還在外,樓只余下他們九位護法,縱是櫛風樓在江湖中已有令人膽寒的惡名,但也總是不乏為求財而甘愿鋌而走險之輩番上陣來擾。
是十七潛其中引得他們各方勢力相互猜忌,又以幾大箱金銀珠寶作餌,將蜀青造相堂滅門一事推給那上了鉤的門派,如此,櫛風樓才算是暫歇風波。
Advertisement
但此事昨日方才揭過,樓主便命人將十七幽于瀾生閣。
“樓主恕罪!”
奉命看守十七的幾名樓中人一個個鼻青臉腫的,都踉踉蹌蹌地進門來伏趴在地上。
玉座上的子錦緞素,看起來約莫有個四十余歲,發髻看似青潤澤,但在嵌珠掩鬢簪下仍約幾縷霜白。
便是此的主人——苗青榕。
但比起天下第一殺手樓的樓主,更像一位溫婉秀麗的貴夫人。
“都下去。”
開口。
廳中眾人忙垂首應聲,極為迅速地退出門去。
那沉重的大門合上,這空曠的廳一時只余那黑年與玉座上的人。
“十七,你不該出來。”
苗青榕盯著他。
“近來瑣事繁雜耽誤太多,我尚有一事,還未問過樓主。”
折竹與相視。
“何事?”
苗青榕天生一張溫含面,此時也看不出什麼喜怒。
“劉玄意死前,曾問我一句話,”折竹不笑時,連他眼尾那顆小痣也是冷淡的,“他問我,我是不是你與妙善道士的野種。”
提起劉玄意這個名字,苗青榕眉眼間添了幾分厭惡,但再凝視年的面容,又不由輕聲笑:“怎麼?你難不真信了他?”
“我若信他,今日便不會問你,”
折竹嗤笑,“我若真是你生的,我會很憾的。”
苗青榕邊的笑意收斂,片刻,哼笑:“我自然生不出你這個天生的壞種。”
“妙善道士十六年前絕跡江湖,最后出現的地方是在業州神溪山,而我與師父張元濟在神溪山十年,樓主你說,我的師父是否便是劉玄意口中的妙善?”
空曠的廳燈火幽微,年的臉半遮于一片暗淡的影里。
“你既已經猜出了這答案,又何必再來問我?”
Advertisement
苗青榕手肘撐在扶手上,歪著子倚靠著枕:“十七,你已十六歲了,我也沒必要瞞你些什麼,我識得他時,他還是天機山的妙善,還未斷了臂膀,也還沒有將你這沒人要的壞種撿去養。”
“你不知他為何斷了臂,也不知他為何要居神溪山?”折竹不聲地審視苗青榕。
“他的事,又豈會件件都說與我知道?”苗青榕好似被什麼刺痛,坐直來,柳眉一豎,“我又是他什麼人?”
妙善,曾是俠濟天下的妙善,那時苗青榕還不是在雨腥風中殺伐果斷的櫛風樓主,尚在父親的庇佑下,做一個十幾歲的天真。
櫛風樓樹敵太多,但那時因父親將一直束在樓中不許出去,便與父親賭氣,不肯勤練武功。
沒見過太多世面,一朝得以跑出樓,便很快被人捉了,幸而得一年輕道士所救。
后來再遇,又被人騙了錢財,在小破廟里挨凍。
那年輕道士給了一個饅頭,又請吃了一碗春面,年竇初開,便一意孤行地跟在他邊三年。
可他始終,看不到的心意。
再后來櫛風樓生變,不再是當初的自己,他亦非曾經的妙善。
“樓主既什麼都不知道,那我便只好自己去尋個究竟了。”
折竹的嗓音冷冽如泉,打斷了恍惚的神思。
“十七,”
苗青榕敏銳地察覺出他話中的幾分深意,“你難道忘了你師父的言麼?玉京,你絕不能去。”
“樓主應知,若非是為他報仇,我絕不會活到今日。”
年嗓音冷靜。
十四年前妙善自玉京重傷而歸,回天乏,卻始終不肯他為何人所傷,又為何事所累。
Advertisement
苗青榕如何不知,若非是執意相救,這年三年前狠狠割在腕上的那一道傷口,便能將他的流盡。
是與他說,他還有師仇未報。
那時這年空有一卓絕的力,卻囿于無法知疼痛的奇癥,他之所以會答應櫛風樓,便是要在樓中的池里一遍又一遍地讓自己數清人上有多塊骨頭,又有多的命脈。
“吃飯的要借我櫛風樓來查你,那個不知是從哪兒鉆出來的辛章也要我櫛風樓來尋你和你上的東西,我將你關在瀾生閣便是不想聽你這樣一番話,可你,倒是倔得很。”
苗青榕一手撐著案角站起來。
“樓主這是何必?”
折竹輕笑,“你本沒有善心,當初救我,不就是為了今日?”
苗青榕定定地著年的臉,一如他所說,救他,原本便是因為在江湖,而妙善之死并不簡單,若輕易手,若牽連進皇家中事便會為櫛風樓招來禍患。
可絕不甘心妙善就這麼死得不明不白。
想必他一定是發現了什麼,也許那線索便在玉京。
“你可知要徹底離櫛風樓,便要一百鞭刑?”苗青榕說道。
“我的人我要帶走,”
年一點兒也不在乎似的,說著又忽然想起來什麼似的,他“啊”了一聲,又道,“還有十五哥,我也要一并帶走。”
櫛風樓本有如此規矩,樓中護法若能領一百鞭刑,便能重得自由,甚至可以帶走他的追隨者。
但人數卻只能控制在十人之。
而十七要帶走百余人與一名護法,這是樓中從沒有過的。
何況,櫛風樓中的鞭刑極為嚴酷,歷來也沒有人可以從那一百鞭下活著離開。
但苗青榕怎麼可能會讓他死呢?他若死了,妙善的仇,就沒有人可以報了。
“好。”
面不改地應下他的話:“這些天來你也解了我樓中危局,一百鞭刑改為五十,你想帶走的人你可以帶走,另外,造相堂那一批財寶也全部歸你。”
造相堂的那一批財寶如今已了燙手的山芋,苗青榕哪里是大方,分明是想將這禍患都丟給他。
但折竹卻微彎眼睛:“好啊。”
櫛風樓的鞭刑所用的鞭是嵌了鐵刺的,它打在人上的每一鞭必是皮開綻,鮮直流。
姜纓等人在廳握著手中的鞭子卻遲遲不敢。
“十七護法……”
姜纓滿臉擔憂地著那年。
“誰若是不鞭,或是輕了力道,莫說是跟著你們的十七護法離開櫛風樓,”苗青榕在玉座上冷笑,“便是要在樓中好好地待著也是不的,你們的歸宿,只能是池。”
被喚來執行鞭刑的五十人無一例外都是跟在十七邊三年的殺手,此時聽了樓主這話,他們面面相覷,卻仍舊不了手。
第十五瞧不慣他們磨磨唧唧的樣子,大約是這年真的守約要助他離櫛風樓,他此時眉目都是含笑的,提著鞭子便上前去:“只是五十鞭,你們若打了,他也不會死,但若你們不打,你們可就要死在池了。”
他說著,那鞭子便揚起來重重地在那年的后背,只這麼一下,那沉重鞭上的鐵刺便已沾上了鮮。
“姜纓。”
年眉頭都沒皺一下,淡聲喚立在一旁的青年。
姜纓才意識到他是覺不到疼的,此時又聽年喚他,他便閉了閉眼,心一橫,揚起鞭子。
一鞭接著一鞭落下,年的衫被鐵刺勾破,上一道又一道的鞭痕模糊,殷紅的鮮浸他的擺,無聲地滴落在地面。
第十五起先還眼眉帶笑,但見年的臉越發蒼白,額上已有了細的汗珠,漸漸的,第十五的角下去,再笑不出了。
再不會疼的人,了傷也會痛苦。
第十五從未嘗過樓中戒鞭的滋味,他不知那鐵刺有多尖銳,有多可怕,此時他再低首凝視自己手中沾了十七的的鞭子。
他出手指輕輕一其上的鐵刺,殷紅的珠瞬間從他指腹冒出。
耳畔的鞭聲不知為何令他心開始煎熬,他眼見那年渾浴,可他也只能站在這里,靜靜地看。
姜纓滿眼浸淚,見又一鞭重重落下,那年清瘦而拔的形倒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十七護法!”
他喚了一聲,想要去扶,卻聽見年氣弱的聲音:“還有嗎?”
折竹晃了神,忘了數。
剩下的幾名殺手幾乎都有些鼻酸,每一人上前的步履都似有千斤重,又是三鞭下去,伏在地上的年吐了。
最后一人遲遲抬不起鞭子,他的手都是的。
“打!”
第十五盯著那人,“他已了四十九鞭,你難道要他功虧一簣?你難道不想要自由了?打!”
那人膛起伏,撇過臉,用足了力氣甩下重重的一鞭。
最后一道鞭聲過后,滿廳寂寂,在玉座上的苗青榕見那渾是的年,微微抿,神未。
“小十七,小十七?”
第十五扔了手中的戒鞭,走到他面前去,蹲下,輕喚一側臉頰抵在地面的年。
也許是地板的涼意令折竹從沉重的困倦中維持了一的清醒,他睜起眼睛來,濃的長睫微。
他邊滿是,一張面容蒼白如紙。
“小十七……”
第十五見他睜眼,終于松了口氣,隨即將自己懷中的木盒子拿出來,遞到他的眼前:“你看,這是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寶珠,比你當初在平安鎮買的那些個還要好。”
,真是這世間最苦,最苦的滋味。
第十五滿心復雜,手打開盒子。
一共十七顆,顆顆瑩潤飽滿而泛著清凌凌的華。
年勉強接來那只小木盒,半垂著眼簾看了會兒。
他角又浸,嗆得他止不住地咳,一雙微彎起來的眼睛潤又朦朧。
若是用它們給編繩,
一定會喜歡吧?
猜你喜歡
-
完結617 章
絕色煉丹師
她毒藥無雙,一朝穿越!坐擁煉丹神鼎,修煉逆天!誰還敢嘲笑她廢柴!想要謀奪家財?她就讓他家破人亡;你家爺爺是絕世高手?不好意思,他剛剛做了她的徒弟;你的靈寵舉世難見?不巧,她剛剛收了幾隻神獸;別人求之不得的丹藥,她一練就一大把!她風華絕代,輕狂傾天下,誰欺她辱她,必定十倍奉還!可就有一個腹黑邪魅、手段狠辣的男人跟她情有獨鍾,還問她什麼時候可以生個娃。她橫眉冷對:“滾!我們不熟!”
112.2萬字5 108840 -
連載769 章

嫡女嫁到,侯爺寵上癮
前世為他人鋪路,一場賜婚等來的卻是綠茶渣男成雙對,她滿門被滅葬身亂墳。死後六年浴火重生,昔日仇人各個權貴加身,她很不爽,發誓虐死他們!偏偏有個男人霸道闖入,她怒了,“滾,彆礙著我的路!”寧遠侯輕輕一笑,甚是邪魅張狂,“我知你瞧誰不順眼,不如上榻聊,為夫替你滅了。”不要臉!說好的淡漠孤冷生人勿近,怎麼到她這全變了!
124.1萬字8 85793 -
完結80 章
與兄書
永樂郡主謝寶真身為英國公府唯一的女兒,萬綠叢中一點紅,上有三位叔伯護陣,下有八位哥哥爭寵,可謂是眾星捧月風光無限。直到有一天,家里來了位冰清玉潔從未謀面的九哥,從此平靜的英國公府內暗流涌動。這位九哥什麼都好,就是患有啞疾、身世悲慘。那日初見,小郡主以為九哥是父親背叛母親所生的私生子,故而百般刁難,小野貓似的瞪著他:“以后不許你靠近主院半步,不許出現在我眼前!”謙謙白衣少年發不出聲音,朝著小郡主頷首低笑,只是那笑意從未照入他的眼底。再后來,這個啞巴九哥將某位紈绔堵在深巷中,褪去溫潤如玉的偽裝,露出猙獰的獠牙。他冷眼盯著地上被揍得半死不活的紈绔子弟,一貫緊閉的唇終于開啟,發出嘶啞低沉的聲音:“以后你哪只腳靠近她,我便打斷哪只腳;哪只手觸碰她,我便斷了哪只手;多看一眼,我便挖了一雙眼,多說一句,我便割了你的舌頭!”永樂郡主這才明白,高嶺之花原來是朵不好惹的黑蓮花!閱讀指南1.女主嬌氣略作小可愛,男主裝病大反派,心狠手辣非善類,只對女主一人好;2.男女主無血緣關系。因情節需要朝代架空,勿考據.
27.6萬字8 18976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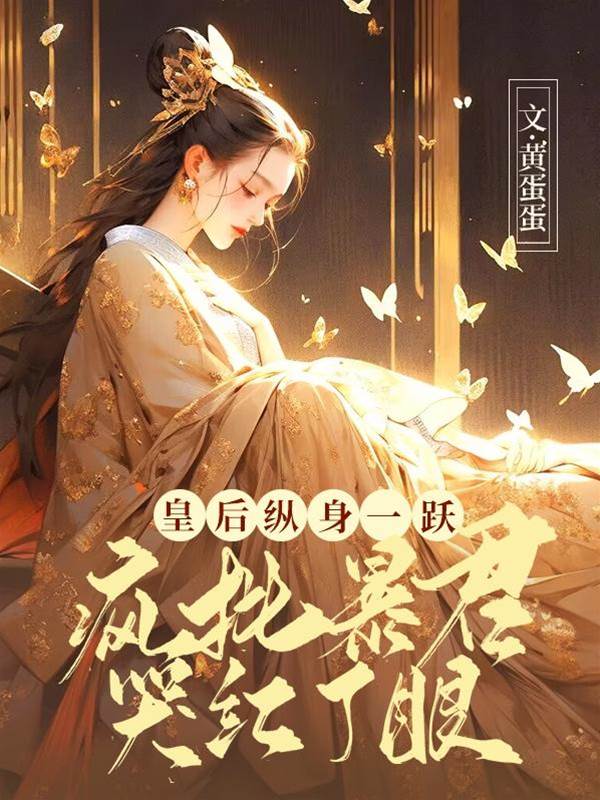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1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