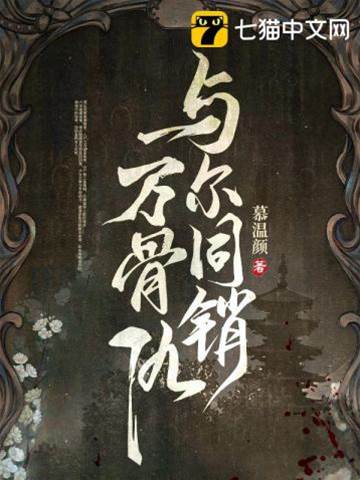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玉殿嬌》 第70章 守陵
疼痛如水般向他涌來。謝灼眼前一片漆黑,如同墜無盡的黑暗。
到了這一刻,謝灼才發現自己錯得何其荒謬。
年時接近是利用,可利用著利用,他越陷越深,憐惜心生愧疚想要娶,連他分不清自己這一份憐惜是始于對的愧疚還是喜歡。
他被發配去往北疆,四年里戒斷了心的一切,后來歷經流放回京,心早就麻木,知曉二人沒有任何未來,所以不想和過多牽扯,卻一步又一步淪陷。
可直到現在這一刻,他回憶過往,才發現自己瀕臨死亡前,想的都是。
年時對太懵懂,不懂什麼是喜歡。可憐惜之就是憐惜,對有了的波就是喜歡。
他對的,本就織著各種復雜緒。
昏黃的燭只打亮了他半邊子,謝灼背靠圈椅,線條繃的結,上下滾了一下,抑著仄病態的緒……
謝灼從回憶中,慢慢睜開了雙眼,眼前黑暗一點點消失。
面前的二人停下了說話聲,蘇祁看向謝灼:“你方才有聽我說話嗎?”
謝灼道:“何話?”
蘇祁嘆了一口氣,又道了一遍:“我說天下好看的姑娘多的是,你何必執著于一人?你外祖母在你離京前,不是給你相看了安遠侯府家郎嗎,那姑娘怎麼樣?”
謝灼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了一句:“不怎麼樣。”
蘇祁:“哎。”
謝灼站起來,低頭看一眼上的紗布,問太醫:“藥換好了嗎?”
胡太醫將沾滿鮮的手浸水盆中道:“藥是換好了,但你接下來一個月就好好養病,別再做這種糟蹋子的事了。”
謝灼嗯了一聲,撈起襟遮住上半,往外走去。
Advertisement
后傳來蘇祁的說話聲:“你去哪兒?”
蘇祁起道:“你不在京城的時候,我去王府照顧你外祖母,崔老夫人話里話外都是對你的關心,讓你早日納妃家。也不是我要掃你的興致,你和皇后的關系,到底不能擺到明面上的,你還是得聽你崔老夫人的話。”
謝灼沒什麼反應,腳步停都沒停一下,直接離開了大殿。
留下的蘇祁與胡太醫對視了一眼,不免嘆息了一聲。
謝灼從離開大殿后,便徑自回到寢殿,屋線暗淡,只看到床上臥著一道纖細的影。
已經安靜地睡去,呼吸安靜平穩,一只手從被窩里探出在了外面。
謝灼幫攏了攏被子,將的手放到被子里,正巧看見另一只手擱在隆起的小腹上。
謝灼的目在小腹停留了好半晌才移開。他站起,將上的袍一件一件褪下,上榻臥在側。
作之間,危眉從睡夢中醒來,睜開睡眼,迷迷蒙蒙看到是他,下意識往床了。
那一瞬間謝灼看出了的抗拒,可服了寧神的湯藥,眼睛睜了一下又合上,倒在他的懷中沉沉地睡過去。
謝灼垂下眸,看著懷中人的容貌。危眉的眼睫極其長,在下眼瞼上投下一層濃的翳。
謝灼的臂彎將摟抱住,另一只手搭上了的小腹上,輕輕按了,到來自手背的溫和溫度。
他將頭埋在頸間,連日來不停地奔波,他疲倦極了,唯有這會靠到上,聞到那悉的氣息,躁的心才漸漸地安靜下來。
這一刻他想,無論要他做什麼,他都可以答應,只要能挽留留下來。
謝灼在額頭上,輕輕地、慢慢地落下一個吻。
Advertisement
一夜更悄然流淌。
翌日,過紗帳照進來。縈繞在謝灼鼻尖那濃郁的蘭香已經消失,他睜開眼,見危眉離開了自己的懷抱,一個人坐在床。
背抵著床橫木,見他醒來了,一副若驚弓之鳥的模樣,避開與他對視的目。
謝灼輕聲道:“醒了?”
他手撐著子翻下床,幫危眉更,危眉說不用,可以自己來,可謝灼已經出手臂,將從床里頭拉到床邊,最后還是幫穿了裳。
謝灼立在危眉面前,替平肩膀上的褶,縱使還想再與待一會,但眼下朝中還有一堆要務在等著他。
“我才回京,有一些事要忙,白日暫時沒辦法陪你,晚上便會回來。”
危眉沉默不語。
謝灼看到面對自己冷淡的神,一時也沒說什麼,叮囑宮人照顧好,便先離去了。
等到謝灼走了,危眉繃著的肩膀才放松下來,眉心微蹙,閉上眼睛,手撐著額頭,回想昨夜宮宴上的種種。
謝灼那時說了那樣多似是而非的話,又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將帶走。
外人會如何看他們?
一遲遲涌來的恥,席卷了心頭。
可危眉的力無法支撐繼續想下去,腦袋昏昏沉沉,好像昨夜服下了那碗安神湯,腦中就如同生銹了一般。
坐在床邊,緩了好一會,不適才一點點消失。
也是此刻,聽到清晨洪亮的鐘聲從皇宮四角傳來,危眉看向窗外。云娥提醒道:“娘娘,今日是帝的下葬之禮。娘娘的子還能去嗎?”
危眉扶著的手臂起道:“我得去的,我是皇后。”
云娥“喏”了一聲,來幫危眉梳妝。
Advertisement
危眉離開未央宮,坐上攆去往殯宮。一路上能到宮人看的微妙眼神,閉目假裝養神,那些粘附在上的視線怎麼也揮之不去。
攆在殯宮前停下,危眉走下了轎攆,手扶著腰肢,朝殯宮走去。
殿前兩側立滿文武百,皆白單。
宮人稟告道:“皇后娘娘到——”
原本回著低低哭聲的大殿,漸漸安靜下來。危眉一素從外頭走來,無數道目追隨著。
宮宴上的事,經過一夜已經鬧得人盡皆知。如今宮里宮外說什麼話的都有。
有人說皇后腹中的孩子世不干凈,是攝政王罔顧人倫,強迫侄媳,讓皇后懷上孕;也有人說是皇后主勾引攝政王在先,投懷送抱,自薦枕席,無所不用,然而無論哪種言論,都在猜測攝政王與皇后早就有染,二人是青梅竹馬,舊復燃。
裴太后背對眾人立在大殿最前方,聽到稟告聲,手攏著佛珠回過頭來,目上下打量危眉。
危眉欠行禮:“是兒臣路上耽擱,母后久等了。”
拿起手帕揾去眼角細淚,一一容,盡態極妍。
裴太后角抿,著危眉這副樣子,不知該不該發作。
昨夜親眼看著謝灼將危眉帶回未央宮摁在床榻上的一幕,回去后便摔碎了一套茶盞。
裴太后心里怨恨啊,自己的兒子尚未下葬,危眉便和別的男人勾搭上了。
裴太后的視線從臉上掠過,沙啞的聲音道:“皇后昨夜在未央宮睡得好嗎?”
危眉聽出話語中的譏諷,抬頭道:“未央宮冰冷。兒臣在側殿一人歇下,夢中思念陛下又醒來,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裴太后端詳的神良久,冷笑了一聲,并未再說一句話,側過臉對負責典禮的太祝道:“到吉辰了,走禮節吧。”
Advertisement
太祝本該上前來跪讀帝的謚冊,卻環顧大殿一圈,道:“太后娘娘再等等,攝政王還未曾來。”
裴太后一聽攝政王三字,冷笑一聲:“攝政王故意拖延時辰。若再耽擱下去,帝的下葬吉時便要過了。”
裴太后命令道:“不用等了,誦讀謚冊吧。”
太祝跪在帝的棺柩前,面有些猶豫。
“娘娘還是等攝政王來吧。”
裴太后命令了好幾遍,看太祝久久不,知道他是攝政王的人使喚不,氣得說不上話來。
他轉而指向另一個臣子,命令他上來誦謚冊,那臣子低下了頭也不言語。
太后一連使喚了好幾聲,那些臣子都不為所。
攝政王不來,這典禮本沒辦法進行。
裴太后握了手心,幾乎咬碎一口牙,只能差人去請攝政王。
好半天,去請人的宦終于回來了,可帶來的不是攝政王,而是攝政王邊的王公公。
王公公一進門檻,便瞧見危眉著個大肚子立在棺柩旁,當即面一變,道:“娘娘,您怎麼在這立著,趕快坐下歇一歇。”
一邊說一邊轉頭斥責邊人:“還不給娘娘搬個椅子過來。”
大殿寂靜無聲,眾人看著攝政王邊素來趾高氣揚的宦,竟對危眉如此低聲下氣,殷勤地討好,氣氛極其微妙。
裴太后看著這一幕,臉發青。
危眉搖搖頭,輕聲:“不用,本宮可以站著。”
王公公卻怎麼也不讓,服侍著危眉坐下,之后看向裴太后,臉上笑容漸漸變淡:“太后娘娘,攝政王正在理政務,一時來不了。太祝先做法事也是可以的,等禮節走完,要送陛下的棺柩離宮,他便會到了。”
太祝聽了這話,這才上前來誦讀謚冊。
裴太后冷冷甩了甩袖子,滿是不滿。
一場法事做下來,大大小小各種禮節,前后足足一個半時辰。
百素服痛哭,王侯依次跪拜,終于到危眉作為帝的結發妻子去跪拜了,眾人屏氣凝神,噤若寒蟬。
危眉走到團邊,手捧著隆起的肚子,躬跪拜。
一拜、二拜、三拜。
“娘娘,您當心子。”
危眉行完了跪拜大禮,再抬起頭來時,眼眶已經緋紅,忽然輕喚了一聲:“母后。”
裴太后看向,危眉發逶迤,素的長鋪展如同玉蘭花在后,泫然落淚,仿佛在做什麼決定,了瓣。
裴太后問:“皇后何事?”
危眉手扶著棺柩:“兒臣想要在誕下這個孩兒之后,去皇陵為陛下守陵三年。”
這話一出,周遭霎時一片震驚。
裴太后蹙眉:“皇后要去為陛下守陵。”
危眉躬再跪,聲音清亮,婉婉如同珠玉:“臣妾待陛下一片赤忱之心,陛下崩逝后,無一日不在思念陛下,皇陵的日子雖然艱苦,但若能與陛下相伴,臣妾此生便也無憾了,懇請太后全臣妾一片拳拳之心。”
危眉的話不是說給太后一人聽,而是說給殿所有人聽——
有意與謝灼撇清關系,本不想委于謝灼。
裴太后聽了后,目微,上前來扶住危眉:“皇后有什麼難言的苦衷?”
恰在此刻,外頭傳來宮人的稟告聲,道攝政王來了。
眾人回作禮,危眉瞧見王公公快步迎上去,附耳在謝灼耳邊說了幾句,一邊說還一邊朝危眉這邊看來。
謝灼的目隨之落在危眉的臉上,眸雖平靜,卻像藏著洶涌的暗,聽完安公公的話,角輕輕勾起。
可他含笑的神,遠比不笑時更讓人心底發寒。
危眉猜到安公公必定將自己要去守陵的一番話告訴他了,握袖口,從團上起,當謝灼走過來時,危眉抬起一雙秋水長眸,喚了一聲:“七叔。”
嚨因為泣,聲線顯得模糊不清,似裊的吳儂語,帶了一層說不清意味。
往后退了一步,謝灼卻向又走近了一步。
二人的距離一下拉得極近,超過了應有的界限。
危眉眼睫,又喚了一聲“七叔”,提醒他這是大庭廣眾之下,自己的份還是他的侄媳。
可攝政王做事,又有誰敢阻攔。謝灼在側只一臂的地方停下,目帶上了幾分危險的侵略意味。
“陛下駕崩下葬,皇后去守陵做什麼?皇后對陛下的有這麼深嗎?”
語調又輕又緩,卻擲地有聲。
這樣一句話,令四下人不約而同屏氣,仿佛窺探到一些不可言說的之事。
猜你喜歡
-
完結1962 章

腹黑狂妃︰絕色大小姐
殺手?特工?天才?她都不是,她是笑顏如花、腹黑兇猛、狡猾如狐的蘭府家主。 想毀她清白的,被剁掉小指扔出去喂狗;想霸她家業的,被逼死在宗廟大殿;想黑她名節,讓她嫁不出去? sorry,她一不小心搞定了權傾天下、酷炫狂霸拽的攝政王大人! 他︰“夫人,外面盛傳我懼內!” 她眨巴眨巴眼楮,一臉無辜︰“哪個不長眼的亂嚼舌根,拉出去砍了!” 他︰“我!” 她︰“……”
180.4萬字8.09 132272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3 -
完結609 章
毒后歸來之鳳還朝
一朝錯愛,她為薄情郎擦劍指路,卻為他人做了嫁衣,落了個不得好死的下場。上蒼有眼,給了她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一次,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手持利刃,腳踏枯骨,鳳回天下。看慣了人們驚恐的目光,她本想孑然一生,卻陰差陽錯被個傻子絆住了腳步。這世上,竟真有不怕她的人?逆流而上,他不顧一切的握住了她的手。
153.9萬字8 14787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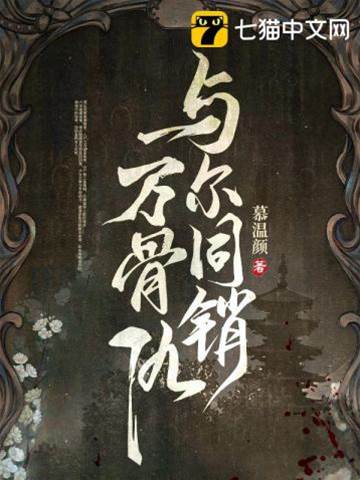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 7479 -
完結508 章

嫁給瘋批太子衝喜後
慕家不受寵的嫡女,被一道聖旨賜婚給命在旦夕的太子周璟沖喜。 不少人看笑話,可別把人給衝死在榻上。 周璟一睜眼,就多了個未婚妻。 小姑娘明明很怕他,卻還是忍不住的表忠心:“殿下,我會對你很好的。” “殿下,你去後我定多多燒紙錢,再爲您燒幾個美婢紙人。” “殿下,我會恪守婦道,日日緬懷亡夫!” 陰暗扭曲又裝病的瘋批周璟:…… 很久沒見上趕着找死的人了。 成親那天,鑼鼓喧天。 數百名刺客湧入隊伍,半柱香前還在裝模作樣咳血的太子劍氣淩厲,哪還有半點虛弱的樣子? 周璟提著沾血的劍,一步步走至嚇得花容失色的她跟前,擦去濺落她右側臉頰的血,低低似在為難:“哭什麽,是他們嚇著你了?”
84.6萬字8.18 143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