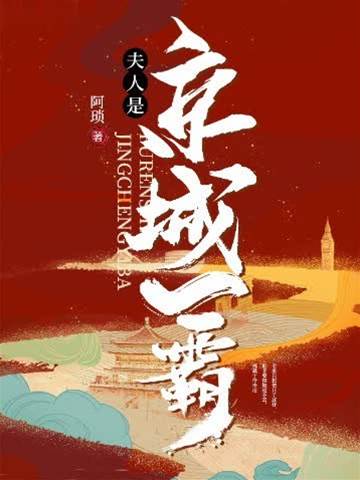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菟絲花外室跑路了》 第 44 章 第 44 章
“姑娘小心了。”
屏風后的聲音帶了點蠱的溫,聽起來沉穩有禮,可那雙手卻牢牢握住音音的指,有力又強勢。毫沒有松開的意思。
音音心頭猛跳,往后掙了掙,微提了聲調:“松開!郎君孟浪了!”
這聲斥也帶著孩子嗓音里的糯,沒甚威懾力。江陳不但沒松,反而輕輕挲了下,他說:“進來。”
他口中干,嗓音暗啞的,吐出這兩個字,竟再不能言。他在想,待會子進來,看見是他,那清澈的杏眼里,會是何等神?
這等待有些漫長,讓他下頷線繃了起來,抬手松了松領口。
音音從屏風上,約看見男子抬手去解襟,又握住了的手,要。還焉能不知他要作甚?這天化日,竟要強搶民,實在令人不齒。左手從袖中出一柄匕首,寒一閃,便在那雙大手上劃下一道口。
江陳手掌一痛,急急收了手,他看著那淋漓的,有些慍怒的不解:“你......”
音音猛然后退幾步,退到門邊,袖下的手還有些抖,卻是直著脊背,道:“我勸郎君三思,我夫君是個不要命的匪徒,你今日若敢.....我不信他會善罷甘休。”
這行商在外的,最怕得罪的便是當地耍狠的,不信這人為了這點姿,愿意惹麻煩。
江陳長眉微揚,忽而反應過來,這是誤會了。夫君?不要命的匪徒?他眸翻涌,問了句:“你夫君何許人也?現在何?”
“我夫君姓江,出了趟遠門,不日便歸。”音音咬定了,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樣。
姓江?說的夫君姓江!江陳來來回回咀嚼這短短一句話,暗沉的眸子里出來,揚了揚眉。
Advertisement
“你......你可思念他?”
屏風后的聲音沒了方才的咄咄,帶了點忐忑的溫,讓音音一時不著頭腦,只好囫圇道:“自然思念的。”
思念的嗎?原來,也是一直念著他的。
屏風后又是一陣沉默,音音只覺如坐針氈,又往后退了兩步,匆匆道:“既無事,那小便先行告退了,此次多謝郎君捎帶。盼船只早日到江陵,我有親眷已候了多時了。”
說罷,匆匆轉,出了主艙。
回了后艙,還心悸不已,只盼著早點到江陵。
好在接下來再未生事,船只揚起帆,很快便至江陵碼頭。
音音同阿素下船時,俱都松了口氣。
此時晚霞蔓上來,江面紅彤彤一片,已是黃昏時刻。兩人聘了輛馬車,想天黑前趕回季家。
“可算是到了江陵,這一路上擔驚怕的,等回了季府,姑娘你需得好好將養,你看你的手.......”阿素將包裹一放,絮絮叨叨,卻不妨被音音扯了下袖子,回頭便見自家姑娘一副警惕神。
音音朝擺擺手,悄悄湊近耳邊道:“阿素,有人跟著咱們。”
這一句話,讓阿素汗倒豎,打起了十二分神。
馬車在城中繞了幾個圈,并未去季府,而是拐去了平安坊的泗水巷。
音音先下了車,幾步進了巷子,閃躲進了一戶人家。
阿素拖拖拉拉下了車,立在巷子口,一壁付錢,一壁警惕的四下張,倒想看看,金陵城這樣的治安,天化日的,誰這樣張狂。
只剛付了錢,便見一匹高頭大馬踱過來,上面端坐了個男子,小麥,高大健朗,頗有幾分英氣。見了他,拱手道:“阿素姑娘。”
Advertisement
這人一副稔口吻,讓阿素愣怔了一瞬,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確實想不起這男子是誰。
那時在盛京,阿素確實同于勁打過幾次照面,只一個在前庭一個在后院,也從未有談,只匆匆而過。阿素又是個不記人的,此去經年,早忘在了腦后。
于勁起先還以為這姑娘是看見他驚到了,可看到眼里陌生的警惕,不口問:“姑娘你不識得我了?”
阿素將他上下打量一遍,忽而出了然神,指了他道:“識得的!”
健高大,常騎馬,可不就是那陸參軍的長隨--喚作福順的。
于勁頷首,翻下了馬,超巷子了眼,從腰間解下一枚玉佩,遞上去道:“沈姑娘在外苦了,大人令我來接你們,往后,定不讓姑娘再半點風雨。”
阿素擰了眉,這陸參軍慕家姑娘是知道的,可如今這話卻實在失禮,哪有不明不白接進府的?
往后退了退,面不太好:“大人的好意我們姑娘心領了,只如今卻不太合適,若是有心,不若臘月十八來廣寒寺賞梅。”
臘月十八,林嬤嬤給姑娘相看良人,倒也不多這一個。
于勁撓撓頭,人接不回去,有些為難,可也知道沈姑娘的脾,看著糯,實則是個有主意的,也不好來,只得去回話了。
江陵城南臨江的金臺坊,乃是個一等一的清雅富貴去,許多宦富商在這一帶置了私宅,偶爾來住。
一戶臨江而起的三進小院落,黛瓦灰墻,清雅素凈,里面假山流水潺潺。
江陳洗去了路上的風塵,換了簇新的月白長衫,一副清貴公子模樣。
他背立在廊下,目落在院里的紅梅上,聽見廊下腳步,也未轉,還是閑散模樣,只背在后的手,卻驟然握了。
Advertisement
那腳步聲越來越近,他卻聽出些不對,忽而轉,對著于勁蹙眉:“人呢?”
“沈姑娘......沈姑娘說是,今日相見有些不妥,想要邀大人后日廣寒寺賞梅。”
于勁說的小心翼翼,生怕又惹了主子不高興,他是個大老,實在想不明白,既想見人,船上直接扣下便是了,何必還要先回了住,沐浴更再見,白白折騰。
江陳不聲的揚了下眉,賞梅?
.......
音音躲在閉的漆黑木門前,微微探頭瞧了眼巷口,看見阿素大大方方走過來,低聲問了句:“是誰?”
這泗水巷前邊就是江陵府衙,料想定不會有歹人敢在此行兇,才放心讓阿素在巷口探看。
阿素噗嗤笑了一聲,掂著手中羊脂玉道:“是那陸參軍派了長隨來,說是要照顧姑娘一輩子。”攤開手:“喏,還送了塊玉佩來。”
音音被調笑的紅了臉,連看也未看,便將那玉佩推了回去,嗔怪阿素:“這玉可不是隨便收的,你先放好,改日必要還回去的。”
阿素吐了吐舌頭,只道:“知道了,知道了。”
兩人拐出泗水巷,經白下長街,再一拐,便至文戶巷的季家府邸。
紅漆門前的風燈已燃了起來,影影綽綽映出昏黃的。
季淮剛下了值,正進門,抬眼便看見了小姑娘單薄的影。
他微愣了下,三兩步走過去,頎長的影將小姑娘罩住,溫潤的聲音里有些無奈:“說好過幾日等我去接的,怎得自己回來了?這天寒地凍的......”
“大哥哥!”音音打斷他,含笑道:“我這不是回來了嗎,你年底政務繁忙,何必麻煩。”
季淮清俊的面上一閃而過的失落,小姑娘總是如此,自己能辦到的事,絕不麻煩他,獨立又堅韌。
Advertisement
可,他想麻煩他。
他吐出一口濁氣,還是朗月般的笑,只帶了點強勢,果斷道:“音音,別我大哥哥,喚我季淮。”
音音一愣,不肯松口:“不,大哥哥就是大哥哥,豈能......”
話還未說完,便見林嬤嬤扶著婢春杏的手,巍巍迎了出來。將人仔細打量一番,問路上吃用,問這幾個月可有委屈?
小阿沁也蹭蹭跑出來,拉著姐姐不松手。
一大家子簇擁著往里走,林嬤嬤事無巨細問了一遍,瞥了眼后的兒子,忽而轉了話風:“回來的正是時候,我帖子都下去了,等后日,嬤嬤帶音音去賞梅。”
賞梅不是目的,相看郎君才是。季淮一噎,得,老太太是忘不了這茬了。
臘月十八是個好日子,江南一連幾日的雪終于停了,出溫煦的日頭。
音音一大早便被林嬤嬤喚了起來,被催著挽發梳妝,換了簇新。
芙蓉掐腰上裳配一條宮緞素雪絹,清新又素雅,襯出段。烏的云鬢上只了一支步搖,綴著一只瑩潤東珠,晃阿晃,是楚楚的清麗。
林嬤嬤圍著音音轉了一圈,只覺這室都被小姑娘照亮了幾分,欣道:“我們音音這容貌,誰看了不心呢?”
音音原先以為林嬤嬤也就說說,走走過場就是了,倒沒料到今日費這樣大陣仗,忙扯了嬤嬤的袖子,道:“嬤嬤,我如今的份,本不宜張揚,萬一被京中那位曉得了.......再者,你可有告知今日來的郎君,音音早已非完璧?”
確實不會因失了貞潔便自輕自賤,但卻也不會瞞此事。
這話說的林嬤嬤心里一陣酸,這樣好的姑娘,卻白白那些苦,嘆道:“放心,今日來的都是小門小戶,非朝中宦人家,嬤嬤只盼著,你邊能有個知冷知熱的人。”
哪怕這知冷知熱的人不是兒子,也開心。
廣寒寺的梅花開的正盛,沿著后山,一層層漫開。
江陳站在半山腰的涼亭,一玄直綴,拔清貴,袍角的銀線暗繡麒麟微微揚起,閃著細碎的。
他臉上還是散漫神,微揚的眼,靜靜注視山腳下的行人。
于勁站的酸,換了個姿勢,抬頭瞥了一眼主子。他撓撓頭,想不明白,主子爺明明今日天不亮就起了,換了好幾套服,月白,竹青、象牙......每一件都是清俊模樣,可臨到出門,又換上了平日最常穿的玄黑。也不知折騰這一通,為的哪般。
他總覺得主子這兩日不太對,著子.....詭異,對,詭異!將政務時時放在心上的一個人,昨日竟推了一應政事,連京中加急送來的折子也未看,窩在書房,只為了雕刻一支桃花木簪。這怎能不詭異?!
他正瞎琢磨,聽見遠傳來喧囂的人聲,抬眼去,不由一愣。
江陳亦抬起散漫的眼,落在連廊上的人影上,微微凝了目。
他遠遠看見沈音音披了件翠紋織錦羽緞氅,飄飄的纖弱,脖上一圈白狐,襯的掌大的小臉盈盈。白皙的臉上皎潔,哪有什麼疤痕?整個人也是舒展的,毫沒有那日船上的凄苦無依,反倒比在京中時,更多了幾分自在的風骨。
江陳微不可查的蹙了下眉,那一點疑慮還未深想,目一偏,便見了旁邊跟來的男子,秀氣的小生,漲紅了一張臉,正一目不錯的看著沈音音。
音音今日見了兩三個年輕后生,已是有些乏了。此刻便只剩下拘謹的笑。
林嬤嬤拉了拉的手,介紹道:“這位是楊家老三,楊頌芝,家里行商的,也算殷實。”
楊家本是看中了季淮這個靠山,才攀了上來,這楊頌芝本存了幾分怠慢心思,只看到人后,卻手足無措起來,竟是漲紅了臉,不知說什麼好了。
看見林老夫人給他使眼,才磕磕絆絆道:“沈姑娘.......我.......我家中人口簡單,母親早喪,現只余個爹爹并兩個哥哥,你若嫁過來,我們分家單過,必不讓你委屈......”
這話一出了口,楊頌芝自己都呆住了,他從來也不是個急子,怎麼今日竟這樣不知分寸了。
他因著懊惱,臉漲的更紅了,一壁打量音音,一壁手足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林嬤嬤有些不高興,這八字還沒一撇呢,如何說這些?默了片刻,道:“楊家公子,今日就到這里吧,音音也累了,等改日我們再聊。”
打發走楊頌芝,林嬤嬤握著音音的手,往后山走,問:“音音,今日若有合眼緣的,一定跟嬤嬤說,我們改日再約出來好好看看。”
江陳離的遠,也未聽清連廊上的話語,只被那男子看沈音音的眼神刺的不舒服。
他微瞇了瞇眼,便見小姑娘已拾階而上,眉眼間瀲滟的秋水,一步步朝著他走來。
那雙幽深眸里的冷寒散了些,倒是染上了幾分飛揚的彩。
只還未看到沈音音走近,便見沿石階下來個男子,青竹般的背影,擎了一支臘梅,聲音溫潤:“今日可都見完了?”
林嬤嬤袖著手,一點也不替兒子著想,說起話來專季淮的痛,道:“見完了。李家公子聞玉,家里世代行醫,是個脾溫和的。還有那楊家小公子,長的也秀氣,據說行商有頭腦,人也靠譜。我瞧著都不錯,端看音音怎麼想了。”
季淮沒說話,默了片刻才道:“讓我同音音說幾句話。”
林嬤嬤瞥他一眼,轉下了石階。
季淮低頭,看見小姑娘的睫,嗓音里盡是溫的蠱,他說:“李家聞玉雖溫和,卻無膽識,他護不住你。楊家小子,是有幾分靠譜,但子尚不定。若論起來,最適合你的......”
他頓了下,抬手將手上的紅梅進了音音烏的云鬢,仰起臉,真誠又坦:“是我季淮。”
江陳目落在季淮扶著音音發鬢的手上,還有小姑娘的面。
他眼角跳了跳,背在后的手陡然握了,那支桃花簪應聲而斷,在他掌心劃出一道痕。
呵,原來今日是來相親的,還見了不止一個男子,邊還有個不懷好心的季淮,好個沈音音,真真長本事了!
作者有話要說:謝在2021-04-2008:58:43~2021-04-2109:11:40期間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營養的小天使哦~
謝投出地雷的小天使:49759107、48803417、呼嚕嚕1個;
謝灌溉營養的小天使:南柯13瓶;vkk6瓶;雨中吃土人4瓶;
非常謝大家對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的!
???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惜花芷
藏拙十五年,花芷原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穩一輩子,可當花家大廈將傾,她不得不展露鋒芒出麵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拋頭露臉是常態,打馬飛奔也常有,過不去了甚至帶著弟妹背著棺材以絕戶相逼,不好惹的名聲傳遍京城,她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她刀子的心理建設,也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獨獨沒想到會有人在出征前盔甲著身向她許終身!好稀奇,這世上竟然還有人敢娶她!?
132.4萬字8 211842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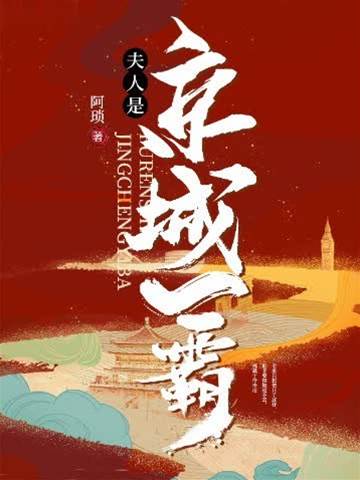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23 章

我不做妾
沈瀾穿成了揚州瘦馬。 雲鬢花顏,瑰逸絕倫,當得起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正因這份美貌,她要被送去給巡鹽御史裴慎做妾。 沈瀾不願意做妾,千辛萬苦逃了出去。 陰錯陽差,成了裴慎的丫鬟。 對丫鬟這份工作,沈瀾尚算滿意。 雖然全年無休007,但薪俸極高,常有外快。 更讓她滿意的是裴慎快要成親了。 只等裴慎成婚後,她便能銷去奴籍,靠着自己積攢的人脈、錢財,快快樂樂過完這輩子。 就在她滿心歡喜,只等放良之時,忽然發現,裴慎想納她爲妾。 沈瀾:我不做妾。 * 裴慎三年前就想納沈瀾爲妾,只是因爲守孝不得已忍了三年。 越隱忍,越剋制,想得到她的心思就越強烈。 如今三年已過,將要成親,正是納妾的好時候。 * 裴慎一生順風順水,官路亨通,遇到沈瀾,才知道世間唯情愛二字,最是摧心折肝。
39.9萬字8 74909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