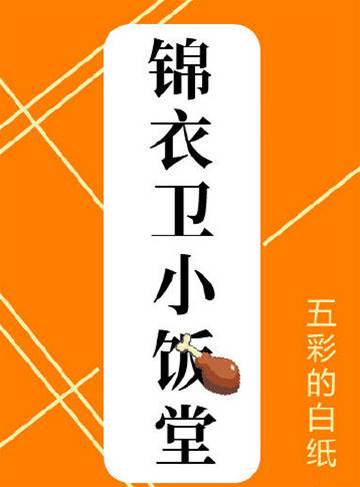《菟絲花外室跑路了》 第 56 章 第 56 章
???
大訂后,季淮麻利的很,趁著音音在江陵,不日便下了六禮,過了文定,去姻緣鋪子合了八字,正式將親的日子定在了五月初五。
音音總覺得太快了些,季淮卻眉眼和,玩笑的口吻:“自然要快些,夜長夢多,日子一長,我怕音音被旁人搶了去。”
音音也不好說什麼,便隨了他去。
季淮的意思,是如今鎮江不太平,要音音留在江陵待嫁。只夜里一閉眼,便想起那些爛泥地里乞討的孩兒,皮包骨頭,等一口救命的飯食。
音音實在放不下,左右鎮江還囤了不米糧,能救一個算一個,便執意在正月二十起了程,回鎮江。
這日倒是難得的好天氣,雖依舊冷難耐,但好歹出了日頭。
出城門時,卻被守門的兵士攔了下來,說是今日要盤查出城之人,音音只好同阿素下了車,耐著子,被盤問一通。
城樓之上,立了個頎長影,金線云紋的玄墨直綴微有些寬松,瞧著似乎消瘦了些許,更顯凌厲氣勢。
他纖長的睫垂下來,目凝在城樓下一素錦的小姑娘上。
于勁走上來,拿了件大氅,滿臉的憂:“爺,您披件裳吧,仔細您的子啊!”
江陳自打從季家出來后,便埋頭政務,三個日夜了,不眠不休,今早更是發起了高熱,卻全然不被他放在眼中。
于勁焦心的很,他其實明白,主子爺這是不敢閑下來,閑下來便是錐心的痛。只不管如何,也不能如此糟蹋子啊。
他斟酌了片刻,勸道:“爺,今日是您的生辰,老夫人一早便傳了信來,囑咐您要吃碗長壽面。這政務沒有完的時候,您今日就歇一晚吧,找個大夫瞧瞧風寒,不?”
Advertisement
江陳并未應聲,只垂了眸子,看音音同守門的兵士周旋,看細白的指疊好戶籍,放回了袖中;看轉上了馬車,纏枝角一閃,沒在車簾后。
直到那輛馬車駛出城門,再尋不到一點蹤跡,他才揚起利落的下頷,微瞇了瞇眼:“于勁,你如今管的益發寬了。”
于勁腦門上冒冷汗,知道他家主子自持底子好,不將這風寒放在心上,可底子再好,那也不是鐵打的啊。他腦子里轉了幾個彎,忽而道:“爺,鎮江的宅子也改造的差不多了,要不您今日去看看吧,便在那里歇一歇。”
他知道主子爺這癥結,歸結底還是在沈姑娘上,或許看到了人,能得片刻安心。
江陳并未接他手里的大氅,轉往樓下而去,聞言頓住了腳,微啞了聲,道了個“好”。
音音是午后到的鎮江,一下車,卻見門前了不人,正袖著手看熱鬧。見了,都訕笑一聲,紛紛讓出路來。
黑漆木門前黃杏兒正嗒嗒的哭,的母親崔氏拽著兒的袖子,一壁拉扯一壁高聲道:“那日,這位先生可是許過我們二十斗米的,白紙黑字寫下的,如今卻不認賬了。”
看見音音回來了,便抖著那紙文書,益發不依不饒:“我聽杏兒說,先生可是囤積了不的米糧,兩間的屋子里堆滿了米,滿的都要溢出來了。”
手比劃,夸張的很,又道:“先生還去西城施粥了,一碗碗的白米粥施舍出去,半點也不心疼的,怎得就不舍得還我們這二十斗米。”
這話在人群中引起一陣,眾人紛紛咂舌,暗中討論這先生到底囤了多米,如今世道艱難,大家沒幾個不肚子的,有這些存糧,可是不得了。
Advertisement
音音悚然一驚,掃到人群中有些面黃瘦的貧民已是眼里冒了,不由心下擔憂,上前對崔氏道:“崔夫人有事進門來說,在這門前喧囂,終是不妥。”
崔氏卻不依,胡攪蠻纏:“怎得就不妥呢?先生欠我二十斗米是真,我如何敢妄言。況且也好讓大家瞧瞧,我們這位先生,到底存了多米。”
“崔夫人是不想要這二十斗米了?”音音轉頭看,清澈的眸子里沉靜一片,是果決的威脅,看的崔氏訥訥一瞬,跟著進了院子。
音音將院門一關,喚阿素拿了五斗米來,往地上一丟,道:“只有這五斗米,崔夫人要拿便帶走,不要,那便請回吧。您也不用費心,今天我是一粒也不會多給。”
崔氏見態度堅決,知道再訛不出什麼,將那五斗米攏起來,同黃杏兒帶了去。
音音如今哪里還在乎這幾斗米,怕的是,災民們極了眼,暴起來,會洗劫了這小院。微微蹙眉,低低道:“阿素,這些米怕是留不得了,明日我們籌備下,后日便都分發給災民。”
阿素“啊?”了一聲,有些舍不得,可看見音音凝重神,也曉得這不是個小事,自然無甚異議。在門邊,聽見外面的人群漸漸散了,才松了口氣。
到晚間,冷的風愈刮愈大,吹的窗欞哐當作響,烏云聚起來,似乎又有了下雪的痕跡。
音音嘆了口氣,起去關窗牖,忽而瞥見隔壁的院子亮起了燈火,指尖一頓,微微愣怔了一瞬。
窗扇還未關上,卻聽見院門被拍的嘩嘩作響,阿素今日不太爽利,早早便去睡了,音音也未,披了件織錦斗篷去開門。
黑漆木門吱呀一聲,閃開一條,現了于勁黑暗中焦急的一張臉,見了音音,他眸一亮,急急道:“沈姑娘,我們大人病了,您去瞧瞧不?”
Advertisement
“病了合該請大夫,來尋我作甚。”
音音有些不耐,順手便要關門,卻被于勁撐住門扉,探頭進來,滿臉的懇求:“沈姑娘,求您了,大夫也請了,只如今大人高燒昏沉,竟是一點藥也喂不進去,您試試不?”
江陳向來厭惡喝藥,于勁跟在邊這幾年,幾乎就沒見他用過藥,偶有風寒,都是生抗。
只這次卻不,不同于以往的小癥候,這回大人已高熱了兩三日,拖到現在,陷了昏沉。于勁從未見過自家主子如此虛弱的一面,簡直心急如焚。
他想起那時在船上,頭一回見大人吃藥,是沈姑娘喂進去的,這才病急投醫。
他見音音神冷淡,并沒有的意思,一著急,竟噗通跪了下去,凝重道:“沈姑娘,您便是不顧大人,也該為這江南的百姓想想。如今南邊外困,所有擔子都在大人上,若他有個三長兩短,這江南決計不太平。”
音音聞言頓住了腳,在暗影中站了一瞬,終究道了個好。
這江南,不能再了。
進隔壁院落時,已近亥時,順著連廊,直直進了室。
室里燃了一支八角琉璃燭樹,影重重的明亮。音音止步在纏枝檀木床前,看安靜睡著的男子。
往日見到的江陳或是張揚的凌厲,或是強勢的篤定,亦或清冷的疏離,只從未想過,他會是現在這樣。
江陳冷白的面上有些微的紅,致的眉眼在燈下泛著溫潤的,病態的。
音音垂下眼,幾不可聞的嘆了一聲。接過于勁手中的藥碗,坐在了床側的繡墩上,舀了黑沉湯藥,往他邊送。
那床上意識昏沉的人聞見辛辣藥味,下意識偏開了頭,音音無法,只得微傾過去,追著他喂。
Advertisement
記憶中的清甜兒香一并飄了過來,讓床榻上的人止了作,連微蹙的眉目都舒展開來,懵懵懂懂啟了。
于勁了把額頭上急出來的汗,重重舒了口氣,這兩年他時常想,沈姑娘要能一直留在大人邊多好,可惜啊。
一碗湯藥很快見了底,燭影一晃,將音音床前的影子拉的老長。將最后一勺湯藥送進他口中,微舒了口氣。往回撤手臂時,冷不防蹭到了他腰間的什,微涼的順。
音音低頭一瞧,便見了那只朱紅緞子的荷包,上面金銀線歪歪扭扭,不太樣子。驟然愣在那里,下意識拿在了手中,凝了目看。
可不就是當初的那只,磨舊了些許,顯是時時放在邊挲。指尖在那歪扭的針腳上劃過,微微頓了頓,不曾想勾到了束口的帶子,啪嗒一聲,掉出一枚姻緣符。
染了紅漆的梨花木,上面刻了兩個名字:江陳、沈音音,字跡行云流水,凌厲有力,一看便知是江陳刻上去的。
音音愣怔了一瞬,卻也只嘲諷的笑笑,又將那枚姻緣符放了回去,抬手便去他腰間解那只荷包。
既然要斷,就該斷的干干凈凈,何必留著的荷包。
只剛要作,那方才還安靜的人忽而一,抬臂便摁住了的手,他掌心熱,微微發燙,讓音音陡然一驚。
以為江陳醒了,抬眼去瞧卻見他還是昏昏沉沉,只下意識中護住自己最要的東西。
于勁嘆了口氣,想起永和二年,跟著大人北上當值,路遇道觀,據說求姻緣最準。向來不信鬼神的大人,竟勒令停了兵馬,親進道觀求了這枚姻緣符。
他這些年一直記得,當初大人坐在暗沉的道觀,一筆一劃刻下他與沈姑娘的名字,虔誠而認真的模樣。
他忍了又忍,還是道:“沈姑娘,有些事,大人總覺得不值一提,可我總覺得,您也有知的權利。”
“當年您的二哥哥沈慎,大人過問此事時,他雖已拿到了釋罪文書,可你也知道,這窮山惡水,不是有了釋罪文書當地員便會放人,季大人當時還是地方小吏,手不了那麼長,是大人一層層下去,將人提了出來。也是大人,費了功夫,將沈慎刑部的案底給銷了,沈二爺才能在商場施展,暗中做了皇商。大人總覺得,此事上虧欠了您,可其實若較起真來,沒有大人,沈二爺也回不了京。”
“永和二年,大人北上前,是曾想過替沈家洗罪名,給姑娘個名分的。可您也曉得,沈侯爺當初可是堅定的太子一黨,公然翻案便是打當今天子的臉,況也會讓朝中扶持新帝上位的老臣心寒。新朝方立,百廢待興,大人的婚事,不只牽扯江家,也同樣牽扯黨爭啊。”
于勁記得,那時在北地,大人一閑下來,便會拿出沈姑娘的信件來看,他有時會問:“于勁,你說,往后沈音音有了孩子,柳韻真的會善待們母子嗎?”
這話于勁答不上來,他亦不知主子爺是如何想的。
他只知道即將返程時,他們大人給柳侯爺備了封信,他說:“于勁,我這樁婚事,若是想退,也需得讓柳韻借口江家的不是,主退了,方不傷及的面。你說,柳家那邊,又該如何補償?”
于勁悚然一驚,這婚期已近,如何突然說這個,他曾試探著問了句:“爺,您要退婚?”
江陳卻未回應,只揚了眉輕笑:“沈音音說要給我生孩子,一男一湊個好字,我只是怕萬一。”
怕萬一?怕萬一主母待們母子不好嗎?于勁也是那時才看清,主子的一顆心,早丟在了沈姑娘上。
他站在床邊斟酌片刻,才道:“沈姑娘,大人那時是有退婚的打算的,為的是往后,你們母子能不半點委屈。”
音音抬眼看他,有片刻的愣怔。
聽明白了于勁話里的意思,江陳當初雖不能給名分,卻是想過退婚的,留一個在邊,便是一時半會不能有名分,也能些委屈。
燭下,秋水盈盈的眸子眨了眨,忽而搖頭,釋然道:“于勁,到了如今,這些事我知道與否,并沒有不同。”
理了下擺,將要站起,才發覺一只手還在江陳掌心里,不由蹙眉,急急去手。
只作大了些,拽的床上那人長睫輕,睜開了眼。
許是喝完藥發了陣子汗,江陳臉上的紅退了去,冷白的致。察覺到有人他腰間的荷包,眉眼驟然凌厲,摁住那只冒犯的手,轉頭視,卻在看清那張芙蓉面后,頓住了作,呢喃:“沈音音?”
猜你喜歡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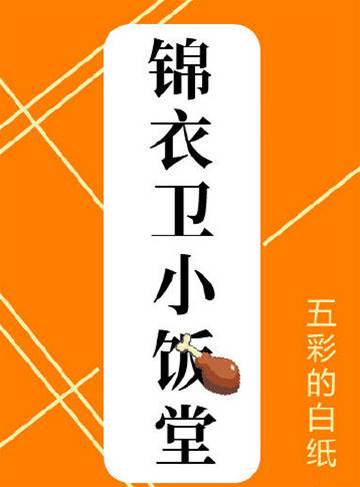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09 39238 -
完結656 章
和離后我把殘疾攝政王衣服撕壞了
她,百年宗門玄仁堂掌門,莫名穿越成大燕國花癡無顏女寧宛。 新婚當夜便讓渣男斷子絕孫,自請下堂。 一時間,萬人哄笑,惹來多個皇子頻頻側 人人都發現曾經的大燕國花癡傻子寧宛,沒了胎記,竟然回眸一笑百媚生! 覬覦? 羞辱? 陷害? 也要看寧宛那活死人肉白骨的醫術,答不答應! 從此,寧宛名揚四海,傾城容顏名聞天下,醫術通天驚泣鬼神。 一時間,國公府的門檻踏破,昔日萬人嘲笑的傻子,如今眾皇子挨個跪著求娶。 渣男更是泣不成聲:「宛宛,和我回家,以後什麼都給你」 寧宛巧笑倩兮。 “我把你們當侄子,你們居然還恬不知恥肖想嬸子?” 赫連墨川吻著女人的紅唇,咬牙切齒:“你究竟還認識本王幾個好侄子。
87.7萬字8 33947 -
完結131 章

寵妃的演技大賞
上輩子,世人都說蘇菱命好,姝色無雙,又出身高門,父親是鎮國大將軍,兄長是大理寺少卿。 十七歲嫁給晉王為妃,兩年後又順理成章做了大周皇后。 論其尊貴,真是無人能及。 然,延熙元年,鎮國公臨陣脫逃,蘇家被指認通敵叛國。 蘇菱誕下一子後,死於后宮。 待她再睜開眼時,卻成了五品太史令之女—秦婈。 一朝夢醒,她雖不會再惦記那個薄情的男人,卻不得不為了她曾生下的孩子,再入宮一次。 選秀當日,帝王靠在龍椅上垂眸不語,十分不耐地揉了下眉心。 便是留牌子都未曾抬眼。 直到秦婈走進去,頂著與蘇後一模一樣的臉,喚了一句:陛下萬福金安。 大殿之上,帝王驀然抬頭,幽遂的雙眸在對視間失神,茶盞碎了一地。 失魂落魄呢喃喊了一聲:阿菱。 【小劇場】 秦婈:再入宮,我發現當年坑過我的人都長了皺紋,包括那個狗皇帝。 蕭聿(yu):演我?利用我?然後不愛我? 【母愛小劇場】 她以為,人死如燈滅,過去的事,便永遠過去了。 可沒想到。 小皇子會偷偷跑到她的寢殿,拉著她的小手指問:“你是我母后嗎?” #她是他的白月光,也是他的心頭好。# #回宮的誘惑# ps: 非典型重生,時間線是持續前進的。 女主嫁了男主兩次,男主的白月光是她
34.4萬字8 11908 -
完結1648 章
殘王梟寵:涅槃醫妃殺瘋了!
“若有來生,定不負你一腔深情,讓那些害我性命、辱我親朋之人血債血償!“前世,沈玉眼瞎心盲,放著與暝陽王戰云梟的婚約不要,癡戀三皇子,為他奔走為他忙,害戰云梟殘了腿,瞎了眼,最后為她而死。可三皇子登基,第一件事情便是娶她表姐,滅她全族,一劍砍了她的頭!重生十五歲,沈玉醫毒雙絕,一針在手天下我有。斗渣男,虐賤女,挽回前世的深情冷王,帶領家族扶搖而上,秀麗山河更要有她一席之地!皇子妃有什麼好?她要一枝獨秀做皇后!前世那一腔深情的冷王“好說,掀了元氏皇族就是了!”1v1
293.5萬字8 48649 -
完結243 章

小小姐每天都在恐婚
大理寺卿之女的奚蕊,作爲京都貴女圈的泥石流,琴棋書畫樣樣不通。 奈何她生得嬌豔動人,家族又頗有權勢,縱然廢物了些,娶回去做個花瓶也是好的。 在她及笄那年,媒婆踏破了奚家門檻,奚父再三抉擇,終於選定吏部尚書嫡子。 奚 . 恐婚 . 蕊:天下男人一般狗,一個人多自在? 於是男方提親當日,她一襲素白長裙,淚眼婆娑,手持裙襬撲通一聲跪在堂前。 “父親有所不知,女兒早心悅祁家將軍,非卿不嫁,今聽聞其對戰匈奴生死不明,故自請守節三年。” 奚父氣得吹鬍子瞪眼,一場訂婚宴雞飛狗跳。 經此一事,奚家淪爲京都笑柄,衆人皆嘲她膽大妄爲又不自量力。 上趕着當未亡人的,這奚家小小姐倒是第一個。 說來也是,那大權在握的祁公爺若能活着回來,又怎會看得上這種除了美貌一無是處的女子? * 忽有一日祁朔詐死逃生,鎮北軍凱旋還朝,舉國歡慶。 隱匿在人羣之中的奚蕊遙望那身着厚重鎧甲,威風凜然的挺拔男子,隱隱感到雙腿發軟。 “......父親,女兒多年未見外祖母甚是想念,不如允女兒去丹陽縣住段時日?” * 後來,大婚之夜紅燭攢動。 男人高大的身形將她完全籠住,戲謔又低啞的哼笑在她耳邊響起。 “聽聞夫人深情至極?“ 奚蕊有氣無力,只覺那日所想的瑟瑟發抖果真不是幻覺。
36.9萬字8.18 156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