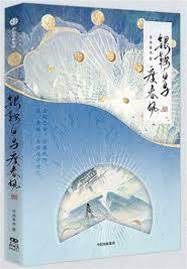《權貴的五指山》 第34章
第 34 章
正紅朱漆大門頂端懸著黑金楠木匾額,其上『淮侯府』四字氣勢恢宏,令人而生畏。
此刻,淮侯府中門大開,管家劉全帶著兩列護衛特來相迎。待兩頂四人抬的皂頂銀帷轎了府,他便回頭對披甲執劍的護衛們使了眼。
厚實的朱漆銅門緩緩關閉,兩列護衛手握佩劍,面無表的列於門後兩側。
繞過照壁,穿過垂花拱門,走過九曲長廊,而後不知越過多曲廊亭榭,顧家一行的轎子竟未曾在府停過瞬息,卻是徑直來到了淮侯府後的萃錦園。
顧家一行人下轎時,仍震撼於淮侯府的富麗堂皇,不提府其他建築的明廊通脊,氣宇軒昂,就單單萃錦園,銜水環山,古樹參天,放眼瞧去那曲廊亭榭竟是數都數不清,甚是恢弘大氣,就是比之王府也差不得多了。
「幾位貴人,請走這邊。」管家劉全指向側一條鵝卵石鋪就的蜿蜒小路,微躬邊含笑,恭謹而不失禮。
顧家一行人忙應是。沿著劉管家所指之,顧父走在最前面,顧母落下半步隨,之後便是顧立軒和沈晚一前一後。
蜿蜒甬道的盡頭是一座飛檐翹脊的亭榭。
亭榭周圍樹木蔥蘢,假山嶙峋,其上六角高聳,房梁上還刻著的圖案,屋脊上又刻有鳥,遠遠去甚是巧奪天工。
待沿石階踏上亭榭,劉管家引他們四人座,恭謹道:「還煩請幾位貴人稍坐,我們侯爺稍後便會過來。」
衆人面一,顧父忙連連拱手:「不敢,不敢。」
劉管家持石桌上的茶盞給他們一一斟了茶,而後恭謹退下。
顧家一行人方長長鬆了口氣。
顧父堪堪掃過周圍的參天古木,著角低語:「我的天爺,從前單聽得人提及這淮侯府如何如何富貴,便都覺得何等的奢華,如今親眼所見,方知這裡頭的富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咱顧家若是能有之一二……」
Advertisement
顧立軒面一變,急叱:「父親慎言!」
顧父訕訕的鼻子,咕噥:「就是說說罷了。」
謹慎的掃罷周圍,顧立軒皺眉低聲道:「畢竟不比在家,還父親謹言慎行,且須記得禍從口出的道理。」
顧父這才方有幾分不願的應下了。
若在往日,他這般的瞎咧咧,顧母早就打駡上了。可如今乍然了這權貴之府,饒是顧母素來子彪悍,此刻也是有幾分怯意的,僅不滿的掃過顧父一眼,便不自在的扯扯袖,撣撣襟,頗有幾許坐立不安。
「立軒,那……待會侯爺來了,咱可需行跪拜禮?」想起這茬,顧母忙看向顧立軒問道。
顧立軒一怔,隨即有幾許不悅的皺眉:「今日幷不算鄭重場合,行常禮便可。」
說著,他忍不住拿餘掃向旁的沈晚,見素手端著琉璃杯盞,側臉看向亭外神思似在恍惚怔忡,也不知有沒有在聽他們的談話。
顧立軒忍不住惡意揣測,事到臨頭,這是在擔憂?後悔?應也會有幾分悔意罷,那霍侯爺又豈是良善之輩?爲人素來酷厲,手段頗有幾分毒辣,伺候這樣的男人,又豈是那番輕鬆容易的?莫不是當世上所有男子都如他這般溫小意?
霍殷手握烏木摺扇踏亭中時,目的便是那顧立軒沉的冷笑,以及……他側娘子一襲湖藍羅衫臨亭而坐,素手執盞,眸微垂,溫雅慧猶如畫中人的模樣。
理細膩骨勻,綉羅裳照清秋。
饒是他從未覺得這顧家娘子的容貌又多麼驚艶,這一刻卻不得不承認,那秋日的艶以及滿園盛開的花,於這樣宛丘淑媛的娘子面前都多失了幾分顔。
指腹無意識的挲著扇骨,霍殷大概打量一番便收了目,斂眸掩下個中緒。
Advertisement
霍侯爺的到來無疑驚了顧家一干人等。
饒是顧父往日多有浪不著調,此刻也正肅穆的對著霍侯爺行了標準的拱手禮,顧立軒行了下拜上峰的拜見禮,顧母和沈晚則在他們後行了子半蹲禮。
霍殷淡淡掃過一眼,沉聲道:「起罷。」
衆人謝過,方起。
霍殷不不慢的走至亭上座。
沉眸環顧一周,霍殷方淡淡開口道:「今日不拘什麼,且座罷。」
又是連聲謝過之後,顧家一行人依次落座。
秦九執佩劍在於霍侯爺後側而立,見落座次序,不由心中冷笑。都到這份上了,莫不是還要面上裝相?
縱觀亭落座次序,霍侯爺居上首,顧父和顧立軒依次分左右落座下首,再下首便分別是顧母和沈晚依次落座。
若往日這般落座倒沒甚麼,可今日他們爲何而來雙方都心知肚明,如此這番作爲便頗有幾分不識抬舉了。
霍殷冷眼掃過,沉了眸。
顧家一行人只怕除了心知肚明的顧立軒,便沒有察覺到此廂有何不妥,更無人得知那霍侯爺驟然沉臉的原因。
顧立軒頃刻便呼吸一,下意識的拿眼去看側的沈晚。
沈晚回看過去,見那顧立軒此刻眼中傳達的幾許焦急又有幾分莫名的示意,心裡納罕了片刻,卻也懶得細想,又轉了眸不去與他對視。
顧立軒頓時急惱,明明之前已經同意,如今這般裝模作樣豈不是要在霍侯爺面前給他難堪?
此間一時便有些詭異的沉默。
顧家其他人不知道霍侯爺突然沉臉的原因,唯恐說錯話火上加油,便不敢突兀開口,遂亭榭中的氣氛愈發的死寂。
而顧立軒雖是有心開口糾正座次,可當著尚不知的顧父顧母的面,當真有幾分難以啓齒。心中對那沈晚便更多了幾分惱恨。
Advertisement
到側顧立軒對散發的莫名惱意,沈晚只覺得莫名其妙。
好半會,已然吃過兩盞茶的霍侯爺方沉聲開口:「上酒。」
秦九忙應。遂大步到亭下,吩咐在亭下候著的劉管家速去備酒。
不過一會功夫,燙好的上好烈酒便陸續端到了亭中,替換了桌面上的茶水。
在秦九的示意下,府管家親自給在座的每人面前的杯盞都斟滿了酒,然後便躬退於亭下。
指腹挲著杯沿,霍殷沉眸不明意味道:「今日諸位所至爲何,應不用本候細說了罷?」
此言一出,沒等那冷汗直冒的顧立軒回話,卻是那顧父自認爲已明瞭此間深意,忙誠惶誠恐的起道:「承蒙霍侯爺抬舉,隴西顧家真是……真是何德何能,焉能得侯爺青眼眷顧?能與侯府攀親,著實是咱隴西顧家三生之幸啊,之後學生定修書本家,此後隴西顧家定爲侯爺驅使,鞍前馬後,以效犬馬之勞!」
霍殷持杯的手一頓,目淡淡的掃過首下的顧立軒。
顧立軒愈發的冷汗如瀑。
「候……侯爺……」
沒等顧立軒戰戰兢兢的起解釋,霍殷已沉聲打斷:「顧家既然有此心,本候便心領了。如此,便飲過此杯罷。」
沈晚此刻約覺得氣氛貌似不太對。心中暗忖,莫不是要酒過三巡,方要讓人領了那子過來,如前世電視劇演繹般,或彈琴或起舞,然後順勢將人賜予顧家?
這般想著,手上也不得不執杯湊近邊。濃烈的酒香侵鼻間,沈晚微微斂了眉,抬袖掩面將其飲盡的時候還約暗嘆,便是到這古代也不消停,依舊不得這這般應酬的場合。
顧母平日甚飲酒,更何況此等烈酒?飲罷之後便側捂劇烈咳嗽起來,沈晚見狀忙起,於其後輕拍順,好一會顧母方消停了些。
Advertisement
接過沈晚遞來的帕子淨了,顧母面上有些發白,忙著對上座的霍侯爺連聲告罪。
霍殷的目在上流連了好一會。
沈晚陡然一僵。之後便重新落座,借由顧立軒的擋了些許那肆意的打量,心下微冷,只覺得那霍侯爺不是酒後失禮那便是生浪。於是愈發的到待在此難耐。
顧立軒也覺得僵得很,約湊近沈晚,小聲囑咐:「還不快去給侯爺敬杯酒。」
沈晚猛地看向他,見他眸中示意頻頻,顯然是剛才沒有聽差,頓時眸震驚充斥了不可思議之,儼然一副他莫不是瘋了的模樣。
顧立軒也覺得此刻他要瘋了,事到如今,莫不是反悔?
霍殷冷眼旁觀,沉臉靜默片刻後,方著烏木扇骨淡淡開口:「顧家娘子。」聲音微頓,頗有些意味深長:「今日前來,你可知爲何?」
驟然被問話的沈晚明顯驚了下。勉強收回對顧立軒的怒視,垂眉斂目剛出口回話,那廂顧立軒卻搶先答道:「回侯爺的話,自然知曉的,且之前已然答應那廂。」
霍殷掃過顧立軒一眼,面無表:「如此,甚好。」
隨即沉聲道:「嬤嬤,那你且帶那顧家娘子下去罷。」
卻原來那秦嬤嬤也一直候在亭下。聞言趕幾步上了臺階,行禮罷,就拉過沈晚的胳膊帶下了這亭榭。
沈晚頓覺一陣觳觫。
饒是再無知也能察覺到此間形不對。
用力抓住亭中石桌桌沿方未被秦嬤嬤那巨大力道拉走,駭然盯住顧立軒,急切開口便說清此事:「今日不是本該……」
「顧家娘子。」霍殷猛地出口打斷,聲音涼薄,卻有不容置疑的意味:「此事,斷無再行反悔的道理。」
沈晚到底還是失了禮,驚疑之下猛然抬眼看向那上座的男子。
恰那霍殷也徑直看向,目相對,沈晚只覺得那沉浮明滅的眸中約有殺伐之意,僅一眼便看的人心中狂跳。
猜你喜歡
-
完結277 章

醫妃有毒
前身被下藥,爲保清白撞柱而亡,卻把她給撞來了!雖然僥倖還活著,卻不得不爲了解藥找個男人劫色!!貪歡過後,她毫不猶豫拿石頭把男人砸暈了!天妒英才,想我堂堂的皇子,居然被一個女人趁機劫了色,完事了就把我砸暈了不說,還把我僅剩的財物都給摸走了!女人,你怎麼可以這麼沒下限?
78.6萬字8 47893 -
連載791 章
攝政王妃狂虐渣
她明明是侯府真千金,卻被假千金所矇騙挑撥,鬨得眾叛親離最後慘死。一朝重生,她重返侯府鬥惡姐虐渣男,順便抱上未來攝政王的金大腿。抱著抱著……等等,這位王爺,你為何離的這麼近?攝政王強勢將她抱入懷,冷笑道撩完再跑?晚了!
126.1萬字8 89085 -
完結81 章

暴君的籠中雀
葉蓁蓁六歲那年不慎落水,一場大病之後,她腦子裏多了一段記憶。 她知道大伯收養的那個陰鷙少年葉淩淵會在幾年後被皇帝認回皇子身份。 她還知道葉淩淵登基後,因為對大伯一家曾經的虐待懷恨在心,狠狠報複葉家,她和爹娘也沒能幸免。 她還知道他會成為一個暴君,手段殘忍,暴戾嗜殺。 重來一世,她發現少年和她記憶中的人天差地別,忍不住靠近
47萬字8 20813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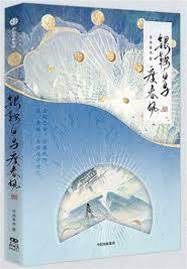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9 -
完結437 章
媚色難囚
一心復仇釣系心機美人vs禁欲清冷白切黑偏執大佬被心愛的夫君冷落兩年,最終趕出門去,沉尸河底。借尸還魂,重回夫家,她成了身懷秘密的遠房表小姐。媚眼如絲,顛倒眾生,她是令男人愛慕、女人嫉妒的存在。只有那清冷高貴的前夫,始終對她不屑一顧,眼神冰冷,一如既往。只是這次,她卻不再逆來順受,而是用媚色織就一張網,徐徐誘之,等著他心甘情愿的撲進來然后殺之而后快!裴璟珩紅了眼角嬈嬈,你依然是愛我的,對嗎?阮嬈嫵媚一笑你猜。(以下是不正經簡介)她逃,他追,她插翅……飛了!他摩挲著手中龍紋扳指,冷笑下令,“抓回來,囚了!”他囚了她的身,她卻囚了他的心。情欲與愛恨,走腎又走心。
86.5萬字8 29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