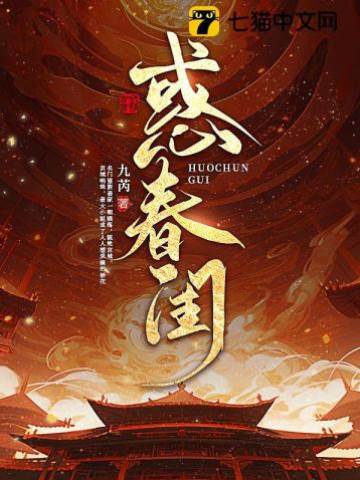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歲時有昭(雙重生)》 第125章 第一百二十五章
竹君過來稟告,說太子殿下在城門侯著時,容舒正在清點一批寒的資。
聽罷這話,忙將手里的棉遞給竹君,匆匆披上狐裘便出了屋。
顧長晉的馬車就停在路邊,常吉給放下腳踏,容舒踩踏上車,車門才將將闔起,一只修長潔白的手便將扯了過去。
容舒跌坐在顧長晉上。
男人漆黑的眸子一瞬不錯地盯著的臉,糙的指緩緩拭去臉上的雪沫子。
“瘦了。”他道。
容舒也他的臉,從眉骨到鼻梁再到冒著青茬的下頜,笑著道:“你也瘦了。”
車廂里很快安靜下來。
二人對視一眼,顧長晉將手掌按向的后腦,容舒樓了顧長晉的脖頸。
他們同樣急切,說不上是誰親吻的誰。
一個人想念另一個人了,是極其那人的氣息的。
就比如現在,瘋狂地汲取對方的氣息,用各種方式讓對方沾染上自己的氣息,是他與都想做的事。
顧長晉離開上京的前一日,容舒還在榻上吻了他一下,笑著說“今兒不,明兒吧”。
這個“明兒”一等便等了足足四個月。
年底的天,雪大如席,風聲蕭肅。
車廂里,藏在昏黃的里的曖昧聲響仿佛是平靜海面下的暗涌,來回涌,暗藏澎湃卻不外人所知。
他們的親吻從最開始的激烈與迫不及待,漸漸變了淺嘗輒止與耳鬢廝磨。四瓣溫熱的艷紅的分離時,馬車已然來到了東宮的大門。
容舒從顧長晉上下來,理了理腰間起了褶皺的裳。
看了看他,忽地“噗嗤”一笑,將一邊的大氅拋過去,打趣道:“殿下一會可得披好了,免得人瞧見了要笑話你。”
顧長晉垂眸笑,知在笑他此時此刻難以抑制的。
Advertisement
下馬車時,他攏了上的大氅,每一步都走得不疾不徐的。他們的面上風平浪靜,可十指扣的手卻因著涌在里的躁而濡了一片。
“不必伺候,我與殿下有話要敘。”進了紫宸殿,容舒溫聲屏退了左右。
外殿大門落下的瞬間,殿的簾子也跟著落下。
容舒摟著顧長晉,由著他將抱室,后知后覺地問:“這次出去,可有傷?”
不怪這樣問,這男人每回出任務都要帶傷回來。
雖他怎麼傷都跟個沒事人似的,但會心疼,會舍不得他傷。這四個月給他寫了三封家書,每一封都叮囑他莫要傷。
顧長晉將的手放在他腰封上,道:“一會你親自檢查。”
他說檢查,還真是讓檢查了。
幔帳落下時,他握著的手解開他的裳,用十青蔥般的白細指一寸一寸梭巡著他的。
月落參橫。
殿里沒掌燈,闃然幽暗的床榻里,容舒只能依靠手來知一切。
指下的皮其實并不,他上有許許多多的傷,新傷舊傷錯縱橫,有些傷還是因救而起的。
他上這些傷疤容舒了如指掌,沐浴時亦或燕好時都曾細細過。
“沒有新的傷疤,”在他下頜吻了下,毫不吝嗇地給了他一個獎勵,“這是獎勵。”
顧長晉低笑了聲:“就這樣?”聲音里是顯而易見的不滿足。
自從收到的家書,他對他這子可謂是呵護得,生怕落下個什麼傷又難過掉淚珠子。從前他出任務,從不曾這般瞻前顧后,便是知曉會傷,也從不遲疑。
可在信中與他道:顧允直,你的子不僅是你的,也是我的。你的每一道傷,不僅你會痛,我也會疼。
Advertisement
字字句句是對他的擔心,也字字句句是對他說的話。便不在他眼前,他也能猜出寫下這些字時會有何表。
讀罷那信,他當真是想想得。
有那麼一瞬間,他甚至想將那一封沾染著氣息的信箋撕碎片吞咽腹。
“昭昭,我想你。”
男人落下這話后,便掀開幔帳,掌了兩盞燈,旋即又落下幔帳,傾向前銜住的。
容舒被驟然涌的線刺得瞳孔一,卻沒閉眼。
他在行這事時,總喜歡掌燈,在明晃晃的燈里看。
不僅要看,也要看他,看他如何沉淪,又如何癡迷于,要將他骨子里那不為人知的對的癡狂一點一點袒在眼前。
寒意隨著落的裳攀爬上理,容舒先是覺得冷,很快又覺得熱。
“看著我,昭昭。”
容舒他沾滿的眸子里,那雙慣來沉著的漆黑的眼映著的臉。四目相對的瞬間,容舒忍不住輕呼出聲,“嘶”了聲。
方才顛簸在車廂里的急不可耐與迫切再次席卷而來,他的氣息離得很近。
垂在榻邊的幔帳無風而,容舒的眼睛漸漸漫上一層水霧。
他低頭去眼角的淚花,帶著些憐惜,可折騰的那勁卻更狠了。仿佛他走的不是淚,而是摧殘著他所有克制,他的理智寸寸潰退的春藥。
完事后,饒是二人已經腸轆轆了,也舍不得分離。
容舒摟著顧長晉,他們出了一薄汗,抱在一起時漉漉的,可這會好似也顧不上凈不凈了,只想將彼此的溫與氣息鐫刻在骨子里。
容舒雖覺累,但四月不見,自是有許多話說與他聽,在上京做的事,吩咐人在順天府做的準備,還有在大同府做的安排,一樁樁一件件都說與他聽,溫聲細語地絮叨著,如一個尋常的妻對遠歸的夫說著瑣碎的話。
Advertisement
顧長晉認真聽著,寄來的家書里,也會提幾句在忙的事,卻不詳細。眼下聽說,才知在他離京的這段日子里,究竟有多忙。
接下來幾日,顧長晉更是深刻地會到這姑娘究竟是忙到何種程度。
不是不心疼這般勞累,可是真的喜歡做這些事,既如此,他便也由著。從前他埋首案牘時,多半是在一旁看書作畫,如今能做的再不僅僅是這些。
說不要被宮里的四面墻圈住的天地,如今正在撞破那四面墻,去尋找的天地。而他要做的,不是以疼、這些借口阻攔,而是陪著走,一步又一步。
于是每日里地驅車去送膳接人的人倒了他。
直到十二月廿九,離除夕夜還有兩日,日理萬機的太子妃娘娘終于有時間好生陪陪他了。
這一日傍晚,顧長晉如前頭幾日一樣踩著點兒來接。
容舒上了馬車便摟住他,撒道:“都說萬事開頭難,果真如此,好在現在所有的事都安排妥當了,我能有多些時間陪你了。”
顧長晉“嗯”了聲,看了看道:“過兩日要宮赴家宴。”
他停頓片刻,復又道:“昭昭,今歲的除夕家宴大抵會是最后一個。”
容舒愣怔了片刻,聽明白了顧長晉的話外之意。
嘉佑帝,大抵是活不過明年的除夕夜。
這幾個月,容舒時常宮去見戚皇后,時不時地也會見嘉佑帝。
對這位溫文爾雅的皇帝,容舒與大胤的所有百姓一樣,都是極戴他的,這是一位他庇護的百姓對作為明君的皇帝的敬與重。
即便后來知曉他是自己的生父親,這份戴也不曾減過,因從不曾當是他的兒。顧長晉平安無恙,給自己討的那條命也已經討了回來,自然也就沒有怪責他的理由,更不會去計較他是不是一個好父親。
Advertisement
這四個月來,每回去坤寧宮尋戚皇后,嘉佑帝都要人賞賜些東西。
有時戚皇后留在坤寧宮用膳時,他也會從乾清宮趕來同們一起用膳。
三個人在君不君、臣不臣的怪異氣氛里用著膳。
初時容舒還覺著有些別扭,可后來卻慢慢習慣了,也漸漸見到了嘉佑帝作為帝王以外的另一面。
半月前,在坤寧宮與他用膳時,他還叮囑了兩句,莫要累著自己。
“你若是隨你母親,子康健,沒從娘胎里帶來甚癥,那自然是最好。但若是隨了……你父,那便不可過多勞。”
嘉佑帝生來便有不足之癥,登基為帝后又過于勞,這才會年不過五十便已有了日薄西山之勢。
容舒是頭一遭聽他提起生父生母的事,而提起的緣由,不過是怕像他一般,累出病來,活不到壽終正寢。
其實從說姓沈名舒,乃揚州府沈家時,嘉佑帝與戚皇后便知,不會認他們。
他們也不強求,而是順著,自始至終都只喚“太子妃”。
容舒喜歡這樣的距離。
可那日嘉佑帝說的話,卻是打破了這一點距離,用一種溫和地不生厭的方式。
車廂里,容舒垂眸思忖了片刻,忽然道:“你可知他喜歡吃甚?宮里的除夕家宴,我讓鸝兒陪我到坤寧宮的小廚房做一道他吃的菜。”
顧長晉搖頭,道:“這宮里的人除了皇后娘娘,大概沒多人知曉皇上吃甚。只是昭昭,你不管做甚,他都會吃。”
嘉佑帝的確如此。
容舒在除夕家宴,做了一道蕭懷安吃的素十錦和戚皇后吃的壽字鴨羹。的廚藝平平,便是有膳房的廚在一旁指點,做出來的味兒依舊是與廚做的無法相提并論。
可那日做的菜卻是最早吃完的,吃得最多的便是嘉佑帝與戚皇后了。
連汪德海都笑瞇瞇地道:“今兒皇爺胃口真真是不錯。”
宴畢,與從前的每一年一般,皇帝領著眾人前往東華門放焰火,與天下萬民同樂。
從前容舒都是在后宅里看東華門的這一場焰火,今歲是頭一回高高站在東華門,著底下那上百架禮炮同時往半空噴出彩斑斕的焰火。
容舒記得今歲與顧長晉大婚的那日,東華門也破天荒地放了一場焰火。
那一日的焰火里有花團錦簇,有福祿瑞,還有一金烏與明月。
今兒的焰火,依舊有一金烏與明月當空同照。
日月昭昭,那是帝后從不曾喚過的小名。
轟隆隆的焰火,似雷電一般照亮了嘉佑二十二年的最后一個夜空。當最后一縷焰火消散后,嘉佑二十三年悄然而至。
嘉佑帝著容舒,溫和笑道:“三日后,太子便要啟程去大同。屆時,太子妃一同前往罷,你如今已是能獨當一面,該同太子一起為大胤的百姓多做些事。”
這一番話,有信任,也有期盼。
容舒很明白,這一去,再回來定是數月之后。
今兒這一面,很可能是與嘉佑帝的最后一面。
思及此,抿了抿,拜了一個大禮,鄭重道:“兒臣,謹遵父皇之命。”
猜你喜歡
-
完結478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不從良
一場實驗爆炸將晏傾城送到青樓門口,睜眼便是妹妹帶著未婚夫抓姦的戲碼!可晏傾城早已不是那任人算計的小可憐,退婚事,虐渣妹,將二叔一家拉下馬,從此再無人敢稱她為廢物!一手醫術出神入化,揮手間治好三叔的斷腿,爺爺的暗疾,銀針在手,是生是死皆由她說了算!風雲湧動,當她站在山頂傲視群雄時,身邊卻多了個怎麼甩都甩不掉的牛皮糖。某位王爺一笑:「這,就是本王給你打下的江山。」
85.4萬字8 13984 -
完結431 章

娘娘們拼命宮斗,丑王妃擺爛上位
【雙潔+輕松+爆笑+沙雕+甜寵+絕不原諒+擺爛】路扶瑤哭了!!!別人穿越都是貌美如花、擁有金手指。怎麼輪到她穿成受氣的草包嫡女?被人下毒,新婚夜獨守空房,成為盛王朝的笑柄。最氣人的是,挺著大肚子的孕婦上門來鬧,讓她喜當媽!看她好欺負??王爺有本宮這般如花似玉、傾國傾城的絕色,怎麼看得上外面的野花。看本宮如何擺爛就成了當今九王爺心尖寵,讓王爺日日早朝遲到!
74.7萬字8 24459 -
完結370 章

驚!瘋批反派竟被養成奶香小團子
玉姝穿書穿到了自己看過的小說,成了里面那個囂張跋扈,無腦的反派親媽。她瞅了下挺著的肚子和床邊還是小娃娃的反派,心里復雜的很。好在穿書前兩天意外有了個空間,里頭采買了一大堆東西,回去是不可能了,她心里給自己打個氣,決定努力種田養崽崽~只是那個原本斷腿回來然后會失蹤的丈夫,你看著我作甚!
64.8萬字8 40048 -
完結266 章

望門嬌媳
徐雲棲參加宮宴,陰差陽錯被醉酒的皇帝指婚給京城第一公子裴沐珩爲妻,人人道徐雲棲走了大運,方高攀了這麼個金龜婿,就連徐家上下也這般認爲。 成婚方知,裴沐珩有一位門當戶對的青梅竹馬,原是打算娶她爲妻的。 新婚夜,裴沐珩淡漠疏離,與她約法三章,徐雲棲一聲不吭悉數應下,婚後,二人相敬如賓,無波無瀾過日子,徐雲棲始終恪守本分,不越雷池一步。 * 裴沐珩芝蘭玉樹,矜貴無雙,是當朝最受矚目的皇孫,原是滿京城的名門閨秀任他挑選,最後被皇祖父亂點鴛鴦譜,定了一普通門第的官宦女爲妻,裴沐珩即便心中不喜卻不得不接旨。 他一月有大半歇在皇宮,對那新婚妻子印象是,嫺靜溫婉,安安分分不纏人,圓房後再瞧她,她容貌嬌,性子軟,兢兢業業在府中操持家業,如此賢惠,即便出身不好,他亦可容她攜手終老。 直到一次宴席出了岔子,他無意中發現,她心中有個“白月光”.... 裴沐珩自認冷情冷性,從未將什麼人放在心上過,這一次卻在深夜輾轉難眠,嚐盡求而不得的滋味。
40.9萬字8.25 66004 -
連載282 章

替嫁給病弱佛修太子后,他破戒了
傳統古言宅斗宮斗+重生爽文+替嫁+男強女強+黑蓮花姜南枝從城樓縱身一躍后,與嫡姐姜檀欣雙雙重生。上一世,姜檀欣為做太子妃,舍棄了青梅竹馬的世子沈徹,還設計讓姜南枝嫁給沈徹做了她的替身。可誰想到,那太子不止是佛修,還病弱到不能人道,最后甚至讓叛軍攻入城!高樓之上,叛軍將二女綁在了城樓上,讓沈徹二選一。他最后選了姜檀欣。重生歸來,姜檀欣主動要嫁給沈徹,還要讓姜南枝替嫁東宮,姜南枝就知道,嫡姐也重生了!選吧選吧,等你嫁入侯門,就會知道內里有多雜亂腌臜!當娶到手的白月光遇上表妹通房外室的時候,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呵,侯門主母并不是那麼好當的!而且,沒了她,這一世沈徹也休想做那威風凜凜的鎮國大將軍了。姜南枝轉身收拾收拾,嫁入東宮,成了大楚太子妃。太子雖然中看不中用,但或許可以合作,一起避開五年后的叛軍之禍。可合作著合作著,為何她的肚子卻大了起來?姜南枝震驚“你不是不行麼?”俊美腹黑的太子殿下,捻了捻手腕上的佛珠,溫柔一笑,“孤行不行,太子妃不知道麼?”姜南枝“……”太子破戒了,嫡姐氣瘋了,前夫火葬場了。
50.8萬字8.18 84472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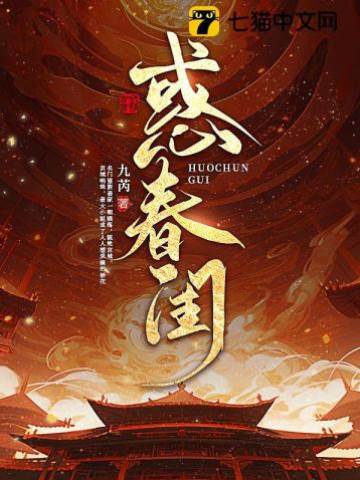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