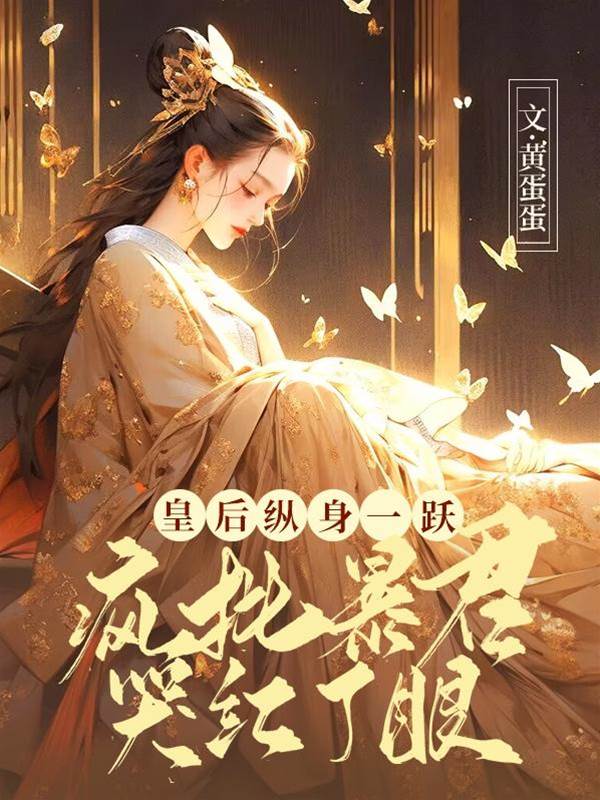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一簪雪》 第83章 第82章
在泥里滾了一遭, 裳上全是斑駁的泥點子,沙子從領頭進,夾雜著熱浪的風撲面而來, 令人渾黏膩, 狼狽不堪, 蹭破皮的傷口也一陣一陣地疼。
但這些在夜里都可以被掩藏。
霍顯已經披上盔甲, 姬玉落跟在錦衛當中,一路恍若無事地回到行宮。
正門由軍把守, 側門則是由錦衛站哨。
姬玉落從側門進,只見守夜的錦衛朝霍顯拱手, 離得稍近的能瞧見姬玉落狼狽的模樣, 但都不敢聲張,心照不宣地垂下頭。
行至花園,恰遇見巡守的一隊軍。
最末兩人并不跟著隊伍,而是慢慢踱步, 走近方看清, 原來是蕭元景。
兩方迎面走來,皆是堪堪剎住步。
霍顯笑了一下,“原來是蕭大人, 巡夜辛苦。”
蕭元景提著食盒,后跟著的是伺候起居的小廝。
他臉上有一剎那的僵滯, 但很快又恢復疏離淡淡的模樣,道:“白日里皇上問起過鎮大人的行蹤, 有人稱是病了,眼下看, 大人的病可好了?”
說罷, 他朝避在霍顯后的人影瞟了眼, “貴夫人也在。”
姬玉落隔著霍顯,朝他半福了子。
霍顯看著蕭元景,滴水不道:“勞蕭大人關心,鎮國公接連大捷,想必不日就要回京了吧,蕭大人可聞風聲了?”
四目相對,蕭元景的眼神逐漸鋒銳,那藏在溫文爾雅的外表里的危險像浮出水面,卻又倏地了回去,“霍大人在皇上邊,軍報比我及時。”
霍顯玩味道:“那可未必,你姓蕭麼。”
蕭元景沖他笑了下,卻不肯再周旋,拱手道別,走出一段距離,神才漸漸暗了下來。
他向來不是很愿意與霍顯談,這人看著和誰都能玩到一起,可實則心思深著,心眼就像馬蜂窩一樣多,還全帶著刺,誰都能,誰都能為他的墊腳石。
Advertisement
不經意的三兩句話被他翻一翻,能要命。
蕭元景幾次三番提醒蕭元庭遠離霍顯,可惜蕭元庭是個沒長心的,拿人當親大哥,到現在都不知蕭家此次出兵是被霍顯踹了一腳。
思及此,蕭元景摁著鼻梁深緩了口氣。
回了一眼。
霍顯毫發無損地回到行宮,說實在話,蕭元景并沒有很意外,但總歸是失落。
小廝道:“公子,怎麼了?”
蕭元景回過頭,將食盒遞還給他,“沒怎麼,長安,你先回去吧。”
名喚長安的小廝“嗯”了聲,“那公子當心。”
他這才提著食盒,往軍分配的住所走。
姬玉落在這時回過頭,若有所思地了一眼,才跟霍顯回到住。
碧梧放好水,姬玉落迅速沐浴,草草洗凈子便從湢室出來。
霍顯晚些還要去九龍殿周遭巡視一番,故而來不及重新燒水,就著姬玉落沐浴后的熱水拾掇完畢。
姬玉落在這當口向碧梧打聽了九龍殿的向,碧梧忙說:“今夜召見惜妃。”
這次出行不便帶朝,朝行為舉止皆太扎眼了,故而碧梧才有機會隨行,來之前小姐便囑咐要時時關注行宮的靜,無論大小事,是以碧梧才能很快回稟消息。
即便并不知緣由為何,也不敢問。
姬玉落再三確認:“確定是惜妃?”
碧梧提心吊膽地說:“小姐回來之前,奴婢在園子里與其他幾個夫人家的丫鬟閑聊,正巧見公公前去惜妃那兒宣旨請人。”
姬玉落眉梢輕挑了一下,眼里落了點沒有溫度的笑,隨后提了提自己的擺,出蹭破皮的腳踝,說:“去給我拿點藥。”
那傷乍看之下格外瘆人,碧梧當即“呀”了聲,怎麼能就這麼沐浴水呢!
Advertisement
急急忙忙找出膏藥。
姬玉落沒讓伺候,將遣了出去。
不多久,湢室里的靜漸輕。
簾子開,霍顯從里頭出來,看到的就是姬玉落那只傷的腳踝。
不止是腳踝,手背、手腕都有多傷。
子剛潤的烏發披肩,一聲不吭地給自己上著藥,手法甚至不算溫和,哪怕對自己也從不肯曾半分。
角抿出的是一堅毅,那朵脆弱、需要人保護的霜花,忽然又凝了一塊冰。
但姬玉落或許不知,這樣的會讓人更生憐。
至,他從不曾對那些弱弱、手無縛之力的子產生過這樣的惜。
霍顯踱步過去,道:“你這樣,十日能痊愈的傷,非要磋磨個二十日才能好。”
他拿過姬玉落手里的藥,順勢落座。
姬玉落半屈著,抬頭打量他一眼,“聽說皇上召了惜妃侍奉,這個時辰了,你還要去面圣?”
霍顯頭也不抬地說:“外邊轉兩圈,不看不放心。”
姬玉落沒說話,下頷擱在膝蓋上,靜靜看著霍顯嫻的手法。
他理傷口亦是手到擒來,但作比姬玉落仔細了不是一星半點,很難想象,他這麼個起手來不拘小節的人,但實則很會照顧人。
姬玉落慢慢咬住里的,臉看起來不太好。
霍顯擰起眉,道:“怎麼,還有哪里疼?”
姬玉落直起腰,手往后腦勺了,霍顯這才順著的作探手過來,果然在腦袋后頭出一個凸起的包,甚至還不小,想是方才摔進暗里時磕著的。
他把人轉過去半圈,藥油在掌心熱,“剛才怎麼不說?”
姬玉落道:“剛才不疼,這會兒有些暈。”
Advertisement
話說得輕輕淡淡,仿佛摔壞的不是的腦袋。
“你——”霍顯啞然,甚至想打,可指都屈起來了,卻不知往哪敲,也不知上還有沒有別的傷,愣是把氣順下去,才咬牙說:“能耐的你,這會兒不把自己的命當命了?”
姬玉落有些累,抱著膝蓋不,語氣慢慢道:“沒到那份上,我知道,我這個人很惜命。”
“是,你惜命。”霍顯嘲諷:“但也沒把自己當回事。”
霍顯一直覺得姬玉落是個生命力旺盛的人,就像臺階里長出的野草,但又不在乎怎麼活,活什麼樣都無所謂。
讓人心里冒火。
姬玉落輕飄飄了下眼,嘲諷回去:“比不得你,連命都不想要。”
霍顯著腦袋的作頓了一下,“誰說的。”
漫長的沉默,他才低聲道:“我想活。”
姬玉落呼吸也靜了瞬,心里竟松快了,仿佛有一直著某塊石頭,現在才堪堪挪開了點。
霍顯的掌心都熱了,空氣里盡是藥酒的味道,他的前襟時不時過的鼻尖,姬玉落在這當口抬起了頭。
仰長的脖頸白皙優,映著燭火熠熠的輝。
只消那麼一眼,霍顯都覺得姬玉落是在故意勾-引他。
他就不能多看一眼。
-都像浪,他遲早得把自己煉一堵結實的堤壩。
-
風推著燭火,也推著霍顯。
空氣里是舌纏綿的水聲,霍顯那只手下意識要住姬玉落的腦袋,剛往上一,又向下移到脖頸。
姬玉落側坐在他上,仰著頭,承著他的吻。
這種事也在能生巧的范圍里,猶記第一回 時,他們還像兩頭只會撕咬的野,曖昧沒品嘗出來,兇倒是都兇,骨子里那點逞強的天全擱在里頭了,兩條舌頭也像是要拼個你死我活一樣。
Advertisement
但如今卻不會了,他們學會了糾纏和品嘗。
霍顯把姬玉落松開時,的臉已經因為缺氧而通紅,那點紅蔓延到脖頸,用指甲輕輕一刮,立起細細小小的疙瘩。
“還暈不暈?”
姬玉落頭往他肩上一趴,“嗯”了聲道:“暈,更暈了。”
霍顯覺得今夜的姬玉落有些粘人,他上的一截背脊,說:“真不要給你找個醫?”
姬玉落道:“不要,你剛才著我了,藥都給你蹭沒了。”
霍顯悶聲一笑,“你怎麼那麼煩人?誰先的口?”
他說話時重新捂熱了藥酒,掌心覆蓋在姬玉落后腦勺上,就抱著的姿勢著。
姬玉落嘆氣,“霍大人,倒打一耙要不得。”
霍顯在腰間撓了兩下,姬玉落笑著躲了躲,又被他摁了回去。
他往窗外看了一眼。
今夜他不當值,九龍殿那兒值守的應該是籬,里三層外三層,不是錦衛就是軍,尋常來說不會發生什麼事,只是白日里無故消失,雖說順安帝恐怕也想不起這件事了,但霍顯心里放不下,還是想看一眼。
姬玉落像是趴在他肩頭睡著了,霍顯拍了拍,沒吭聲,反而拿臉蹭了蹭他的裳。
毫無攻擊。
只是那雙手環著他的脖頸,讓他片刻也無法。
霍顯在榻上坐著。
窗外的黑云追著月亮,來來去去,沙里藍的沙粒漸漸盡。
屋門忽地被推開,向來最知規矩的籬神慌張,“大人,皇上、皇上不見了!”
纏繞在頸間的手不知何時松開了,霍顯輕而易舉地把姬玉落放在榻上,起道:“什麼不見了?在哪不見的,何時不見的,里外不都是錦衛和軍嗎!”
猜你喜歡
-
完結617 章
絕色煉丹師
她毒藥無雙,一朝穿越!坐擁煉丹神鼎,修煉逆天!誰還敢嘲笑她廢柴!想要謀奪家財?她就讓他家破人亡;你家爺爺是絕世高手?不好意思,他剛剛做了她的徒弟;你的靈寵舉世難見?不巧,她剛剛收了幾隻神獸;別人求之不得的丹藥,她一練就一大把!她風華絕代,輕狂傾天下,誰欺她辱她,必定十倍奉還!可就有一個腹黑邪魅、手段狠辣的男人跟她情有獨鍾,還問她什麼時候可以生個娃。她橫眉冷對:“滾!我們不熟!”
112.2萬字5 108842 -
連載769 章

嫡女嫁到,侯爺寵上癮
前世為他人鋪路,一場賜婚等來的卻是綠茶渣男成雙對,她滿門被滅葬身亂墳。死後六年浴火重生,昔日仇人各個權貴加身,她很不爽,發誓虐死他們!偏偏有個男人霸道闖入,她怒了,“滾,彆礙著我的路!”寧遠侯輕輕一笑,甚是邪魅張狂,“我知你瞧誰不順眼,不如上榻聊,為夫替你滅了。”不要臉!說好的淡漠孤冷生人勿近,怎麼到她這全變了!
124.1萬字8 86023 -
完結80 章
與兄書
永樂郡主謝寶真身為英國公府唯一的女兒,萬綠叢中一點紅,上有三位叔伯護陣,下有八位哥哥爭寵,可謂是眾星捧月風光無限。直到有一天,家里來了位冰清玉潔從未謀面的九哥,從此平靜的英國公府內暗流涌動。這位九哥什麼都好,就是患有啞疾、身世悲慘。那日初見,小郡主以為九哥是父親背叛母親所生的私生子,故而百般刁難,小野貓似的瞪著他:“以后不許你靠近主院半步,不許出現在我眼前!”謙謙白衣少年發不出聲音,朝著小郡主頷首低笑,只是那笑意從未照入他的眼底。再后來,這個啞巴九哥將某位紈绔堵在深巷中,褪去溫潤如玉的偽裝,露出猙獰的獠牙。他冷眼盯著地上被揍得半死不活的紈绔子弟,一貫緊閉的唇終于開啟,發出嘶啞低沉的聲音:“以后你哪只腳靠近她,我便打斷哪只腳;哪只手觸碰她,我便斷了哪只手;多看一眼,我便挖了一雙眼,多說一句,我便割了你的舌頭!”永樂郡主這才明白,高嶺之花原來是朵不好惹的黑蓮花!閱讀指南1.女主嬌氣略作小可愛,男主裝病大反派,心狠手辣非善類,只對女主一人好;2.男女主無血緣關系。因情節需要朝代架空,勿考據.
27.6萬字8 18978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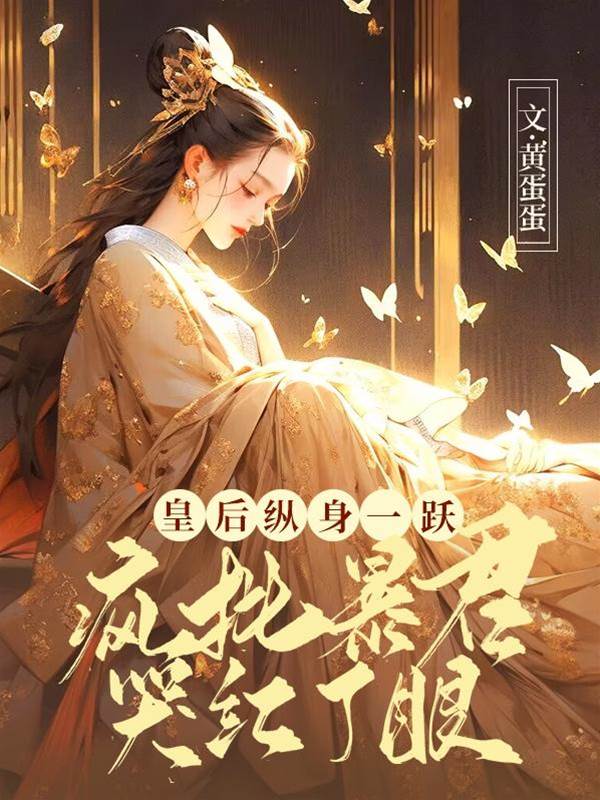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1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