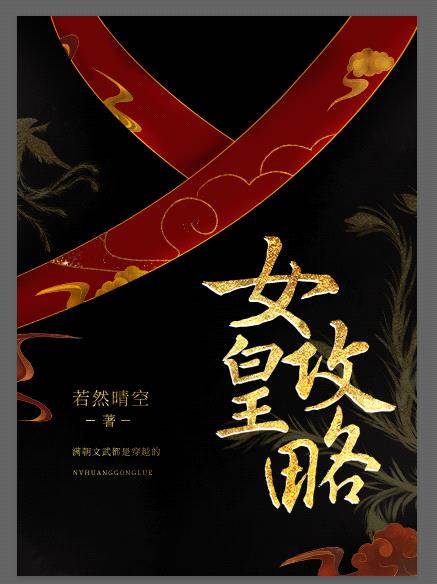《求生在動物世界[快穿]》 第8章 第 8 章
首領是一個族群的核心。
但凡是群居的社會化的,大多都會自然而然地分出等級,區別只在于是母系社會還是父系社會,以及制度是否被嚴格地執行。
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族群會被分為數個階梯,上位者可以隨時要求下位者對其展示臣服。
例如斑鬣狗。
當一頭高等級斑鬣狗要求低等級斑鬣狗臣服時,后者必須立刻停下在做的一切事,抬起后,甚至需要出自己的私部位。如果它們沒有第一時間這樣做,那對不起,麻煩事就來了,被打一頓還是輕的。
在這個系下,小鬣狗也逃不掉。為了維護權威,高等級員有時候會故意殺死低等級員的孩子。而鬣狗王自己的子嗣,特指雌,從出生開始就是“皇室員”。它們會得到最好的照顧、吃到最多的食,也有最高的概率直接接過母親的權柄。
殘酷,但是非常非常高效。
等級制度確保令行止,在王的帶領下,斑鬣狗狩獵功率遠遠高于獅子。
除了這兩種之外,食草如大象、斑馬、水牛、羚羊都是群居;捕食者中年輕獵豹近年來漸漸開始抱團生存,而一直以小家庭著稱的、對不群的胡狼也多次被目擊到集活......自然而然的,這些群落都會有屬于自己的首領。
生存在非洲大草原上其實很多時候就是群和群的對抗,只看哪一邊的群更有力量,哪一邊的首領更有智慧。
首領要做出決策,要領導戰斗,要把一整個族群扛在肩上——
同時也著最好的待遇。
安瀾當然想為首領。
接下來好幾天都在流和協同狩獵中度過,一邊發展自己,一邊照顧母親。后者一開始還能參與搶食,到后來只能接獅群的投喂。那條傷開始化膿,散發出不詳的氣味,哪怕最輕微的挪都會讓它疼得一哆嗦。
Advertisement
對流浪獅子來說,落單就意味著危險,意味著死亡,但一直到躺倒在地,母親都沒有落單,因為安瀾實在沒法對它哀哀的呼喚無于衷。
從進這個世界開始,陪伴著的是母親,保護著的也是母親。獅子是有的,人更是有的,但凡還有一線希,都不希母親因為被拋下而死去。
安瀾并不是唯一一個舍不得的。
至黑耳朵和短尾都沒有半點離開的意思,馬赫雄獅也沒有阻止它們投喂失去行走能力的員。但日復一日地投喂著、清理著傷口,病痛還是讓母親消瘦了下去。
理智是一回事,緒又是一回事。低落太過強烈,以至于安瀾就想不起什麼將來不將來的事了。
可是不去想,這事卻自己有了戲劇的發展。
那是母親傷后的第十二天,獅群停留在水壩領地邊緣的一個高地上,撕扯著前一日獵到的黑斑羚。正當尼奧塔和蘇麗因為最后一塊而撕打起來時,遠傳來了車聲。
趴在母親邊的安瀾猛地坐直、豎起耳朵。
這聲音……很陌生。
認得出制片人三輛車的聲音,也認得出大部分營地向導的車聲,卻從來沒聽過這一個引擎聲。如果說有什麼比陌生的車更讓人不安的事,還聞到了藥劑的氣味。
麻/醉/槍?
安瀾像被蛇咬了一樣竄起來,來回走著。死死盯著車聲傳來的方向,直到它完全出現在的視線中。
這是一輛深的小皮卡,車上坐著八個人,其中一個是拿槍的向導,一個是很悉的薩曼莎,還有六個都不認識。他們穿著一樣的制服,帽子上印著和車上一樣的標記,一個圓圓的印章。
Advertisement
是救助隊!
安瀾長出一口氣。
放下警惕,取而代之的是慶幸。慶幸自己沒有遇到獵者,也慶幸西岸獅群生活在一個有救助制度的保護區里。
沒錯,不是每一個保護區都會救助野生的。南非和東非的獅子命運就大不相同。
南非的克魯格國家公園和薩比森私人保護區都是舉世聞名的獅子公園,前者奉行不干預政策,后者則進行非常有限的救助,還曾有判斷失誤把沒致命傷的獅子安樂死的案例。
比起南非,東非在救助上就做得好多了,馬賽馬拉、塞倫蓋、察沃這些國家公園都會對傷的獅子進行救助,不拘是人類造的傷害還是其他傷害。
有人猜測是因為東非許多國家把旅游業當作支柱,不能失去一些明星獅子;也有人說他們經濟狀況更佳,不像南非比較窮。總之東非什麼都救,先前還花大功夫把一頭陷泥塘的非洲象撈了出來。
南非撒手不管、東非干預太多,很難說哪種模式更好,它們各自也有各自要面對的的獨特問題。前者是獵陷阱、后者是人獅沖突,許多牧民會在獅子的傳統活躍區放牧,獅子也會闖村落。諾遲聯盟的雄獅最后就大部分都死于牧民之手。
但今天,今天不會有獅子死去。
從車窗出一個黑的槍口,隨著“啪”的一聲輕響,一支紅的麻醉鏢穿過空氣,牢牢地扎在了母親的腰上。到刺激,它咆哮了一聲,四爪并用地抓刨著地面。
亞年們立刻圍了上來。
一直到母親完全停止活,獅子們都沒有離開。醫不得不揮舞著工,按著喇叭,試圖把道路清理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始終站在后方的馬赫開始了吼。它得很輕,很急促,一聲連著一聲,但所有的獅子都聽到了。作為這個小獅群的父親,馬赫在要求兒們讓開道路。它認得這些直立行走的穿深服的,它知道他們是特別的。
Advertisement
亞年們不不愿地退后了,等距離被拉開,向導先下來了,然后是拎著大大小小箱子的醫和志愿者,最后是扛著攝像機的薩曼莎。
他們先做了清創,然后用能被吸收的線把傷口合起來,再涂上一層厚厚的藥膏。其中一位醫生在獅子脖子上扎了一枚針劑,看包裝應該是某種抗生素。等一切都理好之后,他們低聲討論了片刻,年紀最大的醫生點了點頭。
在他們做最后的包扎時,安瀾小心翼翼地往前靠了些,然后蹲坐下來,懷念地輕嗅著。挪的很慢,也沒有做出攻擊姿勢,因此向導只是警惕地抬了抬頭。
現在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有不到三十米遠,救助隊員之間的對話清晰可聞。他們在念著獅子們的名字,說著其他獅群的近況,還有營地里發生的事。
原來是薩曼莎向保護區反映了母親傷勢加重的況。作為拍攝者,制片人們必須遵守職業道德,無法直接干預的行為,但他們可以通知向導,也可以直接向保護區通報負傷的況,讓管理人員據條例自行決定是否進行救助。
為此,安瀾將永遠心懷激。
出于這種激,對著鏡頭坐了好久,讓薩曼莎能清晰地拍到想要的畫面。大概是被錮的時間太長,尼奧塔和蘇麗開始來回踱步,在馬赫和安瀾的勸阻聲中不耐煩地呼應著。
在某個時間點,尼奧塔按捺不住地朝這個方向走來。越靠近安瀾,它走得越慢,直到彼此平行時,它猶豫片刻,一只前爪試探著越過的。
安瀾側過頭咆哮起來。
一個坐著,一個站著,兩頭母獅的眼睛對上了。從那雙野的眼睛里很難判斷出它究竟在想什麼,是型的差距,還是過去搶食時的那些手,但幾秒鐘過后,尼奧塔停在了原地。
Advertisement
它坐下了。
沒過多久,蘇麗也靠了過來,同樣坐下了。
馬赫在一旁觀察著、評估著。像以往一樣,它不會手母獅子之間的地位爭斗,即使一個兒在要求其他兒服從。它知道這里不是它的戰場。
這次地位鋒是短暫的,但影響深遠。
在下一個狩獵之夜,當母親還因為養傷躺在樹林里時,安瀾悶聲不響地走到了隊伍的前端,和馬赫隔著半個位。而在獅群四散開來準備狩獵陣型時,站在原地沒有彈,仍然和獅爸爸站在一起。
這是驅逐的位置,是要和獵正面鋒的位置……是狩獵主力的位置。
沒有一頭獅子對此表示不滿。
小分隊驅逐并包圍了作為目標的非洲大羚羊,馬赫做了封口的工作,而安瀾做了鎖的工作,尼奧塔和蘇麗咬住獵的后,兩頭亞雄則做了制的工作。
當獅子們都開始搶食的時候,母親一瘸一拐地加了它們。被占位置的尼奧塔剛剛發出嗚嗚聲,安瀾就朝它出了牙刀。
尼奧塔挫敗地著,耳朵向后背起,尾不安地收在邊,但它終于還是讓出了一個位置。
母親靠上來,了安瀾的臉頰。
一種奇異的覺在心中翻涌。
盡管沒有被戴上皇冠,也沒有被舉在榮耀巖上,但安瀾知道一切都已經改變。如果說過去只是一只格外健壯、狩獵技巧也學得不錯的崽,那麼現在,已經是這群亞年中的主力了。
希。
安瀾在心里念著從人類口中聽到的話語。
真是個好詞。
在荒野中生存,誰都用得上一點希。
猜你喜歡
-
完結827 章
四福晉的嬌寵日常
時空管理局新出“嫡妻系統”。穿越者進入古代,為那些被誤解、被花樣黑、被謠傳誤了名聲的嫡妻們正名。佳凝便是接了這個系統任務的第一人。一個晃神的功夫,她來到大清,成為胤禛的嫡福晉烏拉那拉氏。作為被黑的代表性人物,四福晉一直是蛇蝎毒婦的形象,都說是她害得四爺子嗣稀少。佳凝表示,這任務容易啊。把謠言的苗頭掐死不就行了?在她心里,古代生活十分愜意,每天隨手做做任務就好,閑暇時間便來享受人生。然而事實
132.2萬字8 9793 -
完結115 章

男主他老是那樣絕情
穿進宮斗小說,角色出場三章就要領盒飯。看過這本“絕情帝王愛上我”的顧儀掐指一算,還有三天。顧美人死于三天后,生死時速三十六個時辰。好不容易熬過原地去世的劇情,顧儀要靠保住主線劇情,狗頭保命,才能在男女主角認愛要做一生一世一雙人,散盡六宮之時,出宮做一個快快樂樂的富婆!可惜,絕情帝王最終絕情地拒絕了她的請求。“卿卿,昔年說愛我,原來都是騙我?”
33.1萬字8 11208 -
完結18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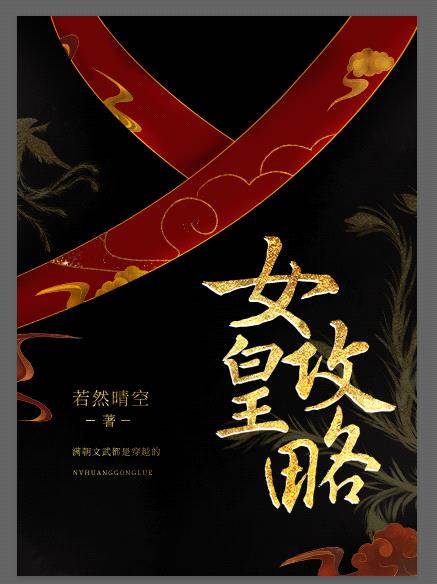
女皇攻略
不正經文案: 姬越登基那天,意外綁定了一個失落文明的明君係統小V。 小V告訴她,開局一龍椅,能臣全靠氪。 姬越喝著媚娘泡的茶,果斷推行王莽的新法。 順手把氪來的曹操趕去練兵。 白起掌刑獄斷案,狄仁傑任國子監校長。 送諸葛亮北伐的那天,姬越又抽到一張ssr。 霍去病,聽上去就是個神醫啊! 正經文案: 一千年後,姬越搜索了一下自己。
33萬字8 438 -
連載1022 章
末世,帶著全家求生存
【末世】+【重生】+【空間】+【屯物資】+【各種極端天災人禍】 某一天,突然而至的九月飛雪,毫無預兆的極寒冰雹,大地乾裂,草木皆枯的極熱高溫,沙塵風暴,傾盆不斷的雨,毒霧籠罩…… 且看重生回來的林青青和她媽媽,如何帶著她親愛的爺奶,在天災末世里掙扎求生過日子。 先賣房! 再賣地! 金銀首飾全回收! 囤米囤面囤菜油! 鵝絨襖子不能少,油丁煤爐暖寶寶!
242.9萬字8.18 26545 -
完結262 章

被獻祭神明后我馴服了他
[穿越重生] 《被獻祭神明后我馴服了他》作者:松庭【完結+番外】 文案 [貌美沙雕小公主 × 法外狂徒創世神] [正文已完結,番外更新中] 穿成異世界公主的當日,宮斗失敗的尤莉婭被送往魔龍之城獻祭。 在遙遠的故國,她的私生女姐姐即將成為王位繼承人,光明圣女預備役,無數大佬將為她神魂顛倒,等著為她鏟除異己。
39萬字8 16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