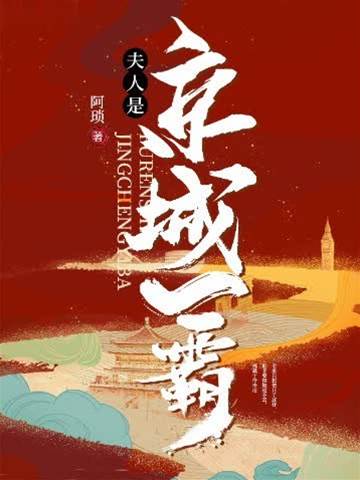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偏執太子的掌心嬌》 第21章 第21章
夜深重,月溶溶。
秋風卷寒霜,四周山林都蒙了層朦朦白霧。
郁林與涼州界的一蔽深山中,燈火通明,酒池林。
喧鬧聲中,有數名著輕紗,搖曳生姿的從黑暗中走出,們弱無骨的倒在那些喝得爛醉的男人上,眼中帶著討好笑。
“還是紀大當家手段通天,能尋得這麼個一本萬利的生意路子,讓我這種窮吏也能時常開葷得趣。”有人喝得爛醉,著懷里的人\\\\,高聲夸贊。
他繼續肆無忌憚:“嘖,就是不知艷娘那個小娘皮,這次又會帶什麼好貨回來,如今世道生意不好做,以大當家的手段,那涼州又算得了什麼,我看不如把郁林的路子也打通,日后也能再多條生財路。”
首座上的刀疤男人小口抿了酒水,并沒有接話,昏昏燈火下,他眼中有冷一閃而過,看著下首喝得已經不知天南地北的男人,對下頭使了個眼:“趙縣丞喝多了,扶他下去休息。”
這位紀大當家,比起四周那些滿臉橫的山匪,他生得其實不錯,甚至舉手投足間,能算有幾分儒雅,只不過他面上有一道從眉心向下,一直拉到耳后的猙獰長疤,皮翻紅,芽橫生,那才是他顯得異常猙獰恐怖的地方。
“大當家,不好了!”有人神慌從外頭進來,踢翻了地上酒也毫不知。
“怎麼?”男人神不耐。
那人臉慘白道:“大當家,艷娘他們在郁林地界不知所蹤。小的順著艷娘他們留下的標記去查,在一不顯眼的山坳里,發現了除艷娘外所有人的尸首。”
“哐當。”首座上男人酒杯掉在地上,摔得碎。
Advertisement
他幾乎控制不住自己發的左手,死死的盯著下面的人,語調森:“全死了?那同艷娘一起的白臉書生呢?”
“被、被剁了首級,和所有的兄弟埋在了一。”
空氣在一刻靜得嚇人,紀方雙眸刺紅,生生碎了座椅扶手。
于他而言,無論是艷娘還是那些悍匪死活,都是無關痛的事,艷娘死了,了做生意拐人的牙婆,大不了再尋便是。
但是!
紀方想到此目眥裂。
那個一直跟著艷娘,姓埋名做白臉書生打扮男人,卻是他的同胞弟弟紀盛,他才是艷娘的主子。
艷娘不過是他個藏份的晃子,他們這些山匪能把皮生意做得這般風生水起,全靠了紀盛的出謀劃策。
但是紀方怎麼都想不到,紀盛就這般不明不白的死了。
紀盛自小就聰明過人,奈何連年征戰家里實在太窮讀不起書,哪怕紀方他后來當了山匪,手里有錢有權,也絕不讓紀盛沾山匪這些骯臟路子,山匪中并沒人知道紀盛是他弟弟,以為不過是艷娘養在邊的小玩意。
要不是艷娘,紀盛怎麼會那些見不得的生意,又怎麼會卷進來。
紀盛這仇他若不報,誓不為人!
紀方霍然起沉著臉吩咐:“立刻收拾家當離開,后山藏著的那些稚不好轉移,那就理干凈。”
*
翌日清晨,天蒙亮。
慕時漪“嚶嚀”一聲在馬車醒來。
先是有些迷茫的了眼睛,睜眼去四周都是好聞的旃檀香,印象中明明還在篝火旁,怎麼就睡著了。
蜷著上錦被,習慣蹭了蹭臉蛋,霎時又通紅不已,這是殿下的錦被啊。
還不待反應,外頭聲音伴著山風清冽,近在咫尺:“夫人,醒了?”
Advertisement
讓慕時漪呆呆開簾子,朝外去。
花鶴玉站在不遠的青松下,墨清雋,四周山霧氤氳,郎艷獨絕。
“嗯。”慕時漪趕放下簾子,輕輕應了聲,似乎已漸漸習慣,他時常語調淡淡,輕得像人低語那般的“夫人”二字。
“這幾日,可能要委屈夫人一番,暫時就不進城了。”花鶴玉繼續說道。
慕時漪略微一思索:“可是艷娘那邊審出了什麼消息。”
“嗯。”
花鶴玉聲音緩緩:“那伙人的頭目是紀方的山匪,被我們誅殺的紀盛是紀方的胞弟,這群人一般在涼州郁林界的清源山四作。。”
“昨夜審完艷娘后,蒼狼就連夜去了清源山,卻不想那已人去樓空,帶不走的東西通通被一把火燒得。”
慕時漪心下一,手掀開紗簾,清冷眸帶著寒意:“那艷娘口中提到的,那些稚呢?”
花鶴玉眸頓了頓:“都殺了。”
慕時漪微震,心底冒出涼氣,這殘忍程度和北留外族屠城又有何區別。
花鶴玉從袖中掏出一遞給:“你看看這個。”
那是四顆狼上的獠牙,上頭還染了朱砂紅印,慕時漪蹙眉細細看了許久:“這是北留巫醫祝由時留下的東西?怎麼會出現在郁林境?”
花鶴玉頷首:“巫醫在北留部落地位極高,東西估計是他們撤離時不小心落的。”
慕時漪心口發沉,清楚這東西若是出現在蒼梧邊界還能勉強說得過去,但出現在郁林境,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郁林乃至整個大燕國,都已混北留探子。
慕時漪聲音輕輕,抬眼直視花鶴玉的雙眸:“殿下不進城不住店,難道是要放餌釣兔?畢竟狡兔三窟,還不如讓他們自投羅網。”
Advertisement
他笑聲低低,帶著一微啞,讓人止不住心尖發:“不愧是我夫人,果然聰慧。”
明明二人間只是扮作假夫妻,但偏偏一字一句從他\\舌\中溢出,每個字都帶著滾燙灼人氣息。
休整過后,再次出發,慕時漪回到了自己的青帷馬車。
看著同樣騎在高頭駿馬上的山梔,微微有些羨慕,山梔自小蒼梧長大,騎很好。
但除了年時在蒼梧時,父兄帶騎馬外,回堰都后,便再也沒有過了,二夫人崔氏照顧的這些年,對極好,但教的總歸是堰都貴必學的琴棋書畫。
慕時漪低聲一嘆,下心,余不自覺留在馬背上的花鶴玉上,不想男人就像后長了眼睛那般,笑著朝來。
慕時漪心底微驚,趕忙放了紗簾,雪白貝齒咬著瓣,心慌得,眼里急得泛了一層薄薄水霧,人。
一連三日,這路上除了秋風越發蕭瑟,金秋落葉滿地外,一直平靜無波。
直到第四日巳時,町白騎馬來報:“殿下,兔子出山。”
花鶴玉聞言,角勾了勾。
等到未時,日頭偏西,沉沉暮的波碎影下,青帷小車托著長長斜影,□□民護衛跟隨左右,他們走山腳下道,一行人似乎匆匆趕路,并未注意周遭靜。
車馬聲陣陣,并沒人察覺到山林中藏著的重重危機。
紀方站在蔽山丘上,親眼看那一行人,走他設的圈套。
這些護衛手好那又如何,騎馬的能跑出去,那坐車的可就別想了。
總歸,這些人是要拿一條命給他胞弟償還的,若是他弟弟紀盛還在,一定不會像他這般猶豫,紀方深吸口氣,手朝空中打了個手勢:“放!”
Advertisement
這瞬間,無數巨石從山頂滾落,鋪天蓋地轟隆聲陣陣,若是砸實了,這下邊的人恐怕得活生生城泥。
隨著巨石落下,青帷馬四周護衛大吼一聲,拔出刀:“敵襲!保護夫人。”
兵荒馬,烈馬嘶鳴。
紀方在山丘上冷眼看著,心中閃過快意,他一定要去瞧瞧那些會被砸何等凄慘的模樣。
許久后,紀方朝后打了個手勢:“去,我們去看看。”
“大當家的,真要冒險面?不如遠遠確定人死了就行了,畢竟小心駛得萬年船。”
紀方雙眸刺紅,神瘋狂:“我們那數十名弟兄就白死了?去看看都砸什麼樣了。”
山林另一側,花鶴玉帶人回來,護衛們為了演得像假裝被巨石砸中的樣子,此時除了花鶴玉外各個狼狽,不人\\\,被飛濺碎石出幾道不明顯的小口子。
暗衛町白從后方策馬歸來,他眸沉冷,下馬稟報:“殿下,兔子咬鉤了。”
花鶴玉抬手接過西風遞上的棉帕,不了手上跡,淡淡吩咐:“讓蒼狼帶人,全部活捉,好好查一查紀家兩兄弟的底細。”
町白:“是!”
慕時漪帶著山梔站在不遠的松林下,看得分明,花鶴玉的手背似乎了傷,上頭印著一道朱紅痕。
然而他在轉走向時,卻不聲往后藏了手背,面上看不出一異。
“殿下傷了?”慕時漪清凌凌的眼眸向他。
花鶴玉明顯一愣,下意識想要否認。
“原來殿下這般清風朗月,也會騙人?”慕時漪莫名有些惱了,但依舊找西風拿了藥箱,一言不發站在一旁,漂亮眉心蹙著也不看他,那毫不掩飾的驕縱小子,格外楚楚人。
花鶴玉垂了眼,眼中神漆黑,有順著他指尖低落,最后無奈一嘆,緩步走到前,把視線落在松松綰起的發髻上:“那就,勞煩夫人了。”
眼前出一只白如羊脂玉般的手,那手手背骨節分明,薄瘦有勁,白皙上有一道寸許寬的痕,泛著鮮紅的珠子,瞧著甚是駭人。
慕時漪依舊不理他,貝齒輕咬瓣。
他淡淡聲音,在耳邊響起,著一無奈:“臟,我怕嚇到你。”
猜你喜歡
-
完結184 章
穿書之我成了暴君的掌中嬌
玄風淺不過是吐槽了一句作者無良後媽,竟穿越成了狗血重生文裡命不久矣的惡毒女配!為保小命,她隻得收斂鋒芒,做一尾混吃混喝的美豔鹹魚。不成想,重生歸來的腹黑女主恃寵生嬌,頻頻來找茬...某美豔鹹魚掀桌暴怒,仙力狂漲百倍:“今天老子就讓你女主變炮灰,灰飛煙滅的灰!”某暴君霸氣護鹹魚:“寶貝兒,坐好小板凳乖乖吃瓜去。打臉虐渣什麼的,為夫來~”
32.1萬字5 22571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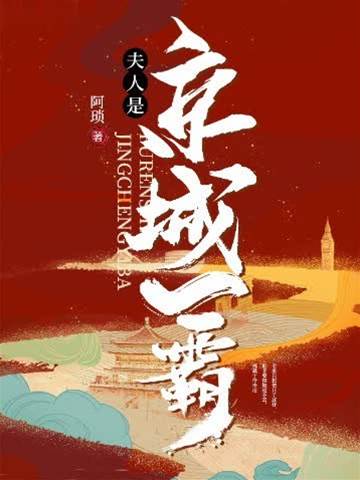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64 章
全能毒妃:世子降不住
穿越到死人的肚子裏,為了活下去,晞兒只好拚命的從她娘肚子裏爬出來。 狠心至極的爹,看都沒看她一眼,就將她歸為不祥之人。 更是默許二房姨娘將她弄死,搶走她嫡女的位置。 好在上天有眼,她被人救下,十四年後,一朝回府,看她如何替自己討回公道。
186.1萬字8 19787 -
完結791 章

齊歡
她可以陪著他從一介白衣到開國皇帝,雖然因此身死也算大義,足以被後世稱讚。 可如果她不樂意了呢?隻想帶著惹禍的哥哥,小白花娘親,口炮的父親,做一回真正的麻煩精,胡天胡地活一輩子。 等等,那誰誰,你來湊什麼熱鬧。
153.4萬字8 96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