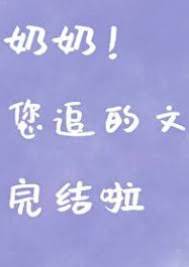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拒嫁豪門,少奶奶又逃了》 第165章 原則性的問題
電話通了很久,但那邊卻遲遲再沒霍澤的聲音。
他像是站在冷冽的寒風中,猛吸了兩口氣,又緩了好一會兒才輕笑出聲,「沒關係……」
越是這樣,卻越讓蘇小小覺得無比愧疚。
可眼下,真的沒辦法兩邊都顧全,只能做取捨了。
蘇小小了一下鼻子,「霍澤,等這陣忙完了,我主約你,或者我和宋時宴一起,我們三個人吃個飯吧。」
「不必。」霍澤拒絕的很快。
蘇小小心裡擰繩似的,「那好,我們兩個人單獨吧。」
又是一陣靜默,霍澤突然嗤笑出聲,「小小,其實你也不必對我有多愧疚,宋時宴回來a市的事,我一清二楚,還有他的病我也知道,之所以他一直不見你也是我以母親從b市過去a市和其餘醫生一直治療他的條件,是我不讓他見你,你明白嗎?」
「說白了,我就是個自私的人,為了得到你,以為這樣就可以了,但你的心始終沒辦法在我上,其實母親在告訴我他最近病時,我甚至想過期盼他死亡的消息,這樣我們就可以永遠在一起了,但看到你為了他不惜跑那麼遠去找稀缺型的源過來時,我好像真的低估了你們之間的。」
「算了,就這樣吧……」
霍澤一腦說了很多。
他真的很害怕蘇小小說那句對不起,更害怕說我們不要再聯繫。
可終究還是要義無反顧在他邊,他就是個局外人而已。
霍澤掛斷電話,揣進兜里,在路燈下站了很久。
他看著天空中又飄起了雪花,落在他的肩膀上,很快又融化進呢子大里。
霍澤在原地發愣,幾分鐘後進了後的酒吧裡面。
雖然已經是冬日了,但酒吧裡面氣氛燥熱,有不只穿著弔帶超短在裡面熱舞。
Advertisement
霍澤今天一個人來,只求,他沒開卡座,找了個吧臺一個空閑的地方。
朝服務員打了一個響指,「一瓶威士忌。」
服務員震驚,「先生,您一個人喝嗎?」
「怎麼了?不行?」霍澤語氣微怒,這種時候看誰都不爽。
服務員連忙不是,「先生,這威士忌酒太烈,我怕您一個人喝不了這麼多,要不一杯一杯來?」
「我說了一瓶就要一瓶,別墨跡,喝不喝的了我自己心裡清楚。」
服務員只好遵從客人意願,「好好好,我這就給您拿。」
……
幾杯烈酒下肚,霍澤已經覺整個人的胃都要燒起來了,神智還夠清楚,就是有一點點上臉。
手機隨意扔在桌子上,屏幕閃爍著蘇小小的來電提示。
霍澤看了一眼,煩躁地將屏幕扣在桌面上。
冷冷笑出聲來,「呵!」
霍澤又能灌了半杯。
突然,後肩膀上搭了一雙纖的手掌上來。
徐安娜坐到霍澤旁邊的空位置上,給自己也要了一瓶威士忌。
笑著,臉上帶著明的笑意,並不像那種夜場子,看穿著還是有氣質的,估計是同病相憐之人了。
徐安娜,跟霍澤打招呼,「一個人喝這麼多嗎?需不需要人陪啊?」
霍澤臉紅彤彤的,抬眼看,上下打量了幾分。
略微冷淡,「關你什麼事兒。」
徐安娜又說道,「今天卡座都滿了,我訂不到位置,想獨自買醉只好來這個角落了。」
「先生,我看你才喝了幾杯就不行了,要不我們比比酒量怎麼樣?」
徐安娜格豪爽,也不扭扭,更不屑用勾搭男人。
不管霍澤同不同意,直接拿著自己的被子和他了一下。
「我先干為敬。」一口氣飲了乾淨。
倒拿著杯子滴不出一點酒來。
Advertisement
霍澤本就心裡煩,還來了個挑釁他的人,自然更不爽了,也將自己杯子倒滿,「好啊,來就來。」
……
酒過半旬。
霍澤或許是有心事,已經喝的不樣子了,站起準備去上廁所,高大的影卻猛然依靠在徐安娜懷中。
一頭扎了進去。
「喂?你不行了?不行就投降唄?」
「先生?」
以為他裝的,沒想到了好幾聲都沒反應。
徐安娜沒辦法,只好自己買單,扶著他出了酒吧門口。
「你家住哪裡啊?我讓司機師傅送你回去,或者有沒有家裡人電話號碼?」
霍澤喝的迷迷糊糊的,抬頭看,沒說什麼話,倒是給徐安娜用大拇指點了個贊。
佩服真能喝。
算了!
徐安娜也累了,給他開個酒店得了。
最終打車兩人去了就近的酒店裡面。
……
這一夜,雪下的極大,在地面足足落了十厘米的樣子。
明天就是聖誕節了。
走廊里的工作人員都在布置聖誕老人,聖誕樹,說說笑笑的。
霍澤在睡夢中約約聽到聲音,隨後又被窗戶里照進來的大太給炙醒。
他緩緩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的吊燈,覺有點陌生。
昨天喝斷片了,本不記得後面發生的事兒,他環顧了一周發現自己是在酒店。
而在看到旁摟著肩膀出來的人時,霍澤瞬間嚇到從床上彈起,「你是誰?」
「怎麼會和我睡在一起?」
他這麼一,腦袋瞬間傳來炸般的疼痛。
又使勁著太想記起昨晚的事,可真的斷片了,完全想不起來。
等到徐安娜被聲音醒,也半夢半醒從床上坐了起來。
隨後看著赤著上半,下面又只穿了一件短的男人,低頭看向了被子里的自己。
也沒穿服。
Advertisement
我去!
難不睡了?
昨天兩人一進酒店,這男人又哭又鬧,真的是煩死了。
徐安娜差點沒把他從十樓給丟下去。
至於到後面,好不容易安頓好他躺下,酒店裡突然熄燈了,然後後面就等了一會兒,也不知不覺睡著了。
再醒來,就是這幅場景了。
徐安娜也懊惱地拍了拍腦袋,又抬眼看著一驚一乍的霍澤,「你慌什麼,怎麼看也是你佔了我便宜好嗎?我才是吃虧的那一個。」
霍澤無語,恨不得殺了自己的心都有。
媽的!
非要去喝酒,非要買醉,還非要和著人杠上,結果變現在這樣。
他還怎麼有臉去見蘇小小啊!
這算是什麼混蛋事兒。
霍澤煩得要死,心態都快要炸了。
徐安娜立馬扯過來一件服穿著,從床上下來,看他猙獰的表真是瞧不起,一個大老爺們,既然事已經發生了,就坦然面對唄,搞得這麼嚴重幹嘛。
徐安娜找到沙發里的包,直接掏出來兩踏鈔票甩在霍澤懷裡。
「放心,不會白睡的,我徐安娜出來社會闖,就算自己吃虧也不會讓別人吃虧,這些錢夠你閉了吧。」
「還有,不準報警,昨晚的事兒就純純是我瞎好心才造的,拿了這些錢,咱們就一筆勾銷,從此江湖不見,再見也是陌生人,明白了嗎?」
徐安娜一肚子火氣,丟下錢拿著自己外套就摔上門走了。
霍澤一臉懵,甚至一頭霧水。
這個什麼事兒啊。
真實的!
他低頭看著手裡的鈔票,完全就是鴨子的待遇。
靠!
他真的要瘋了。
……
霍澤從酒店退房出來,特地去前臺問了一下那人信息。
好歹知道個名字吧。
前臺拿出份證來,「先生您好,這是昨晚開房那位小姐的份證,忘記拿了,請你幫忙歸還。」
Advertisement
霍澤連忙搖頭,臉冷得嚇人,「我還不了,你們打電話聯繫。」
「先生因為是您過來退房,的份證和押金我們都會退到您手上,麻煩您還給朋友就行。」
朋友?
誰和是朋友?
霍也沒辦法最終只好先裝份證進了口袋裡,這人他這麼多這輩子都不願意見到了,為什麼讓他上這麼狗的事啊。
真抓狂。
……
霍澤從酒店出來的時候,就打車去開自己的車了。
又從酒吧門口開到車才敢給蘇小小打電話過去。
比起昨晚,他語氣里多了不張,「小小,我們現在可以見一面嗎?」
不見一面他真的不安心。
蘇小小看時間,早上有點不太方便,「霍澤,要不今晚吧,今晚我騰出來時間,我們一起吃飯。」
話音落,那邊又傳來其他聲音,好像忙的。
對面就掛了電話。
霍澤神迷茫,忍不住猛地砸在方向盤上。
猶豫了一會兒直接將車子開去了研究所的地方。
到地方的時候,霍澤提前給母親打了一通電話。
「媽,小小在裡面嗎?」
最近有幾天聽不到他的消息,不知道幹什麼去了,突然接到他的電話,霍瑩也擔心。
「在裡面呢,不過在照顧宋時宴。」
「你要進來嗎?」
霍澤在猶豫,一時間沒說話。
霍瑩又苦口婆心勸道,「兒子,要我說就算了吧,這段不適合你,再繼續下去對你也是傷害,趁自己還沒有徹底陷進去及時吧。」
「我在這裡的這段時間,看到蘇小小為了宋時宴那種義無反顧的神,都給我了,真的很久沒有見到過這麼堅固的兩個年輕人了,現在他們已經將誤會說開了,你啊,就放棄吧。」
霍澤這種氣候哪裡聽得進去這些,就覺腦袋裡一陣嗡嗡。
他開口問道,「媽,你說我要是犯了錯誤,小小會原諒我嗎?」
「兒子,我跟你說的話你是不是一句也沒有聽進去?」
「媽,你就告訴我會不會?」霍澤堅持。
「我覺得不一定,要看什麼問題,如果是原則上的問題,那絕不可能。」霍瑩說罷,突然回想明白過來。
「兒子,你不會幹什麼了吧?找其他人了?」
霍澤又沒聲了。
霍瑩覺到一陣無奈,真是碎了心,「如果你真的要是犯了原則的錯誤,那就不要再假裝還很別人的樣子了,完全沒有必要,媽媽也是過來人,為什麼不和你父親住在一起,就是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經不住,犯了錯,我實在過不了心裡那一關,所以到現在婚姻搞得一團糟。」
霍瑩嘆氣出聲。
正好蘇小小從旁邊房間里出來,霍瑩就連忙將電話掛了。
「他怎麼樣了。」霍瑩裝作無事發生,關切問道。
蘇小小點頭,心明顯好了一些,「霍醫生,你昨晚讓我幫忙盯著一點他的心電圖,一直都很平穩,還有其他數據都慢慢出來了,都比之前穩定了一些,什麼的也都降了下來,是不是代表他況在有所好轉啊?」
霍瑩聽到這話,突然臉上現出一激來,立馬將前面的事拋之腦後,「我進去看看,如果真的能數據有所好轉,就證明那葯是有用的,已經在一點點回籠。」
「那太好了,終於看到希了。」蘇小小澤連忙激起來。
霍瑩點頭,「對,你可以理解為這是近段時間來最好的消息。」
「等下我複測一遍,然後你每天一定要叮囑他一些注意事項,幫我看著他不要隨便下床,更不要與任何人有接。」
「好,我知道了。」蘇小小一進房間就帶上了消過毒的手套,十分注意衛生。
……
等到兩人忙完已經是一小時之後了。
況確實不錯,有所好轉了。
蘇小小和霍瑩臉上都出滿意的笑容,然後出了門。
而霍澤就在門外面不遠的長廊拐角站著。
蘇小小愣了一下,霍澤看到的影就主走了過來。
霍瑩想說什麼,但被打斷了,「媽,我和有幾句話想聊,你去忙你的吧好嗎?」
霍瑩嘆氣搖了搖頭,每說一句話走開了。
蘇小小跟著霍澤去了一旁的窗戶邊。
外面的冷空氣慢慢滲進來。
蘇小小也做好了準備,但開口還是那句恆古不變地,「對不起!」
但是很誠心的道歉。
霍澤突然僵住了,也連忙道歉,「小小,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我該死!」
霍澤本沒有勇氣面對昨晚的事,可是他有沒有辦法去瞞,憋在心裡真的難至極。
蘇小小一看就覺到他緒不對勁,皺眉問道,「是不是出什麼事了呀?你為什麼要跟我道歉,如果是因為昨晚你說的那些話,其實沒事,我不介意的。」
「而且站在你的立場想想,肯定是不願意讓我知道他生了病還回了a市,霍澤我明白上一個人的時候,大家都是自私的,你不必自責。」
猜你喜歡
-
完結104 章

最愛你的那十年
從來吵著要走的人,都是在最後一個人悶頭彎腰拾掇起碎了一地的瓷碗。而真正想離開的時候,僅僅只是挑了個風和日麗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門,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賀知書于蔣文旭來說是空氣是水,任性揮霍起來時尚不覺得可惜,可當有一天當真失去的時候才悔之晚矣。 “你所到之處,是我不得不思念的海角天涯。” BE 虐 慎入 現代 先虐受後虐攻 情深不壽 絕癥 玩野了心的渣攻&溫和冷清的受
13.1萬字8 13246 -
完結68 章

軟刃
言微靜悄悄嫁給了城中首富秦懷鶴。 她很低調,懷著秦懷鶴的孩子,為他居屋守廳堂,洗手做羹湯,卻換來了他不痛不癢的一句調侃:“她就這樣,言微人輕嘛。” 言微留下一句話,再也沒有回頭。 “他什麼都有,除了心肝肺。” 言微走后,秦懷鶴才知道,她曾經是他的捐贈對象,來找他,不過是為了“報恩”。 從此,一直在云端上行走的秦懷鶴再也看不到如她那般,心藏柔刃披荊斬棘的女人。 秦懷鶴在雨夜里,一把攬住她的腰肢,眸光深幽,“親一下,我把心肝肺掏出來給你看看。” 言微紅唇輕牽,“秦懷鶴,算了。” 友人:“鶴哥,心肝肺還在嗎?” 秦懷鶴:“滾蛋!” 他什麼都有,除了老婆和孩子。 一年后,秦懷鶴端著酒杯斂眸看著臺上神采飛揚的女人,與有榮焉,“我孩子她媽。” 言微明眸善睞,答記者問,“對,我單身。” 會后,他堵住她,眼圈泛了紅,“言總越飛越高了。” 言微輕笑,“人輕自然飛得高,還得多謝秦總當年出手相救。” 秦懷鶴眸子里那層薄冰徹底碎了,欺上她眼尾的淚痣,“你就這麼報恩?我救過你,你卻從未想過回頭救救我。” 秦懷鶴的微博更新一句話: 【吾妻言微,我的心肝肺。】 #深情千疊斷癡心妄想,沒心沒肺解萬種惆悵# #我不只要歲歲平安,還要歲歲有你。# 溫馨提示: 1、不換男主,he。 2、歲歲是寶貝,很重要。
21.7萬字8.09 30385 -
連載1666 章

冥王崽崽三歲半
華國第一家族霍家掌權人收養了個奶團子,古古怪怪,可可愛愛,白天呼呼睡,晚上精神百倍!大家在想這是不是夜貓子轉世投胎?冥崽崽:本崽崽只是在倒時差,畢竟地府居民都是晝伏夜出呢!人間奶爸:我家崽崽想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通靈家族繼承人:要不讓崽崽帶你們地府一日游?提前了解一下死后生活?冥王: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312.4萬字8.18 33566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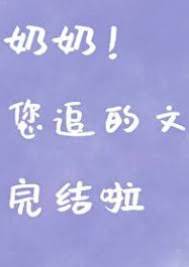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3167 -
完結719 章

封少,你家小祖宗馬甲掉了
注孤生的封二爺有一天對所有人宣布:“爺是有家室的人了,爺的妞性子柔,膽子慫,誰敢惹她不開心,爺就讓他全家不開心。”然後——“這不是拳打華北五大家、腳踩華東黑勢力的那位嗎?”“聽說她還收了一推古武大族子孫當小弟。”“嗬,你們這消息過時了,這位可是身價千億的國際集團XS幕後大佬。”然後所有人都哭了:二爺,我們讀書不算少,你不能這麽騙我們啊。而被迫脫馬的祖盅兒隻想:這狗男人沒法要了,日子沒法過了,老娘要滅世去!
126.9萬字8.18 37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