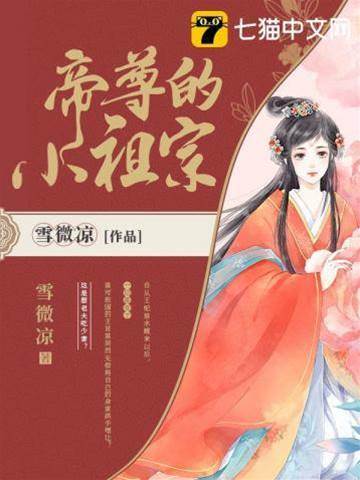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撩了奶狗世子后》 第 11 章 煎熬
賀裁風見藺長星赴死一般的神,哭笑不得:“你怕什麼啊你,又不會吃了你!”
藺長星不想理他,來的幾個姐兒,上用香濃郁,熏得人頭疼。
藺長星擔心失禮,將噴嚏一忍再忍。
們卻不識好歹,一左一右地齊心協力聲勸他酒,他推不去,只好杯杯咽下肚。
正盤算著怎麼尋借口開溜,剛巧見人到跟前打招呼。
廣云臺分東西南北四樓,中間是庭院曲廊,能著是緣分。
江鄞開竹簾,不同于平日的清風明朗,面上帶著醉醺醺的風流姿態,拱手笑說:“果然是賀家小侯爺和燕世子爺,我方才遙看著就像二位,真是好興致。”
賀裁風起回禮,邀他坐下來喝酒,江鄞看了那幾個姑娘一眼,擺擺手,推說公務在。
等人離開,賀裁風笑了兩聲,眉弄眼地問藺長星:“你可知江尹有多懼?”
藺長星酒意上頭不肯再喝,夾著菜吃,任憑旁邊的人勸酒也不理會。
“別我,我熱。”他不解風地吩咐完,抬眼問賀裁風:“如何個懼法?”
賀裁風見藺長星臉越來越難看,怕他真在這里怒,招手把姑娘都到他這邊坐。
“他后面跟著的那清秀小廝,猜猜是誰?”賀裁風說:“量你也沒注意到,那是江夫人!”
藺長星猛地抬頭,“蒙焰剛才在這里?”
“正是。江尹在場,潔自好卻總有推不開的應酬。他怕家中夫人誤會,就每次帶著夫人來,讓親眼看……哎,你哪兒去?!”
賀裁風話還沒說完,藺長星已經將腰間的荷包拋給他,扔下句“自個兒結賬”,撒沖了出去。
他將荷包顛在手里,靠在姑娘懷里迷了會,才笑瞇瞇地從中拿出一片金葉子:“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Advertisement
藺長星心慌,一路狂奔出廣云臺,到外面大街時,江家的馬車早就走了。
他頹喪地了把臉,在盛夏微熱的晚風里一吹,酒醒了大半。
怎麼辦?
蒙焰若哪日閑談時告訴謝辰,謝辰會怎麼想他?
以的脾氣和他們如今的關系,謝辰問都不會來問他,只會在心中鄙夷他的孟浪。
可他不是孟浪的人,他在面前,只因喜歡才不自。
今晚就算他追上蒙焰也沒用,總不能說,請你千萬要瞞著謝辰,我還想娶呢。
謝辰若知道他在朋友面前招搖舊事,會把他掐死的。
年人一旦出格,準有麻煩,他沒想到麻煩的還在后頭。
藺長星心里煩悶,在街上漫晃半個時辰才回家,進府時已過戌時。
燕王妃帶著一幫人候在院子里,臉上是有的嚴肅。
藺長星看見燈火通明心知不妙,快步到面前,彎腰行禮:“母親。”
燕王妃上下打量他眼,見他衫還算整齊,臉稍作和緩,語氣仍是僵冷:“哪兒去了,這個時辰才回?”
“與表哥吃飯喝酒去了。”
“哪里喝的酒?”
賀裁風靜默半晌,在考慮說不說實話。實話一說,他挨頓罵不要,只怕害賀裁風挨打。
藺長星邊的小廝木耘著聲音提醒,“世子。”
“罷,你別說了,我也不想聽,你這麼大的人了,玩無可厚非。”燕王妃站起來,終究沒忍心苛責,囑咐他以后晚上早點回府,別讓燕王知道了不高興。
藺長星這回趕忙應下。
從他旁過時,燕王妃嗅到他已經散得差不多的酒味和脂味,神復雜,又代道:“如今你尚未娶親,當注意言行,別在外面留了浪的名聲。”
Advertisement
藺長星頭更低,語氣誠懇:“兒子曉得了。”
就算王妃不代,他日后也不想再去喝什麼花酒,酒還不好喝。旁人能尋到樂子便罷,他在那鬼地方簡直度日如年。
若謝辰介意,日后因此更不想再搭理他,他得不償失。
沐浴后,藺長星躺上床。已過子時,四下萬籟俱寂,他翻來覆去睡不著。
今晚廣云臺之行,賀裁風選的姑娘確是按他所說。果然,手臉,倒酒夾菜,幾乎不讓他手。
也的確風韻出塵,二十出頭的年紀,很知道說什麼話讓客人高興,做什麼作最讓男人興。
藺長星那時雖煩躁,腦中卻十分冷靜,像在欣賞一出的戲,而他自己不在其中。
他徹底明白過來,他對姑娘沒什麼偏好,環燕瘦都沒意思。還不如枕頭下的春圖,好歹還能籍自個兒,以解長夜之苦。
而他所謂的偏好,全是依著謝辰的樣子,謝辰什麼樣,他就喜歡什麼樣。若不是謝辰,天仙也不行。。
他不喜歡那些人刻意的近,千百地喊他爺,他寧愿聽謝辰冷冷地喚一句“藺長星”。后者給予他的愉悅,是前者拍馬也趕不上的。
想清楚后,他踏實睡了過去。外頭月澄亮,照著一城酣眠。
隔日一早,藺長星去給燕王妃請安。燕王妃留他吃早膳,沒再提昨晚的事,卻說起當年送他去南州后,與燕王閉門幾月不出,傷心斷腸的舊事。
飯后,賀裁風來府,質問他昨晚跑什麼。藺長星說喝多了想吐,剛好嫌吵就沒進去。
賀裁風說:“你天生就是個老實人,罷了,孺子不可教也。”
藺長星呵呵兩聲。
賀裁風唬人一套一套,膽子實小,昨晚亦沒有留宿。怕他老子打他,自詡為風流才子,屋里卻連個通房都不敢收。
Advertisement
倒有臉笑話自己。
賀裁風陪他練過武便躺下了,藺長星不敢懈怠,看書看到深夜。練武雖累,文墨更不能落下。
從書房回屋后,直接進了凈房沐浴,原打算睡個好覺,然而才到床帳前,便瞧出了不對。屋里被人擅作主張地燃了香片。
怪不著,方才木耘眉弄眼,
藺長星上前開帳子,床上躺著個姿曼妙的子,裳穿得沒比廣云臺的多。
月清風爽,玉簟紅紗。
子緩緩坐起,含帶怯地看他眼,滴滴道:“世子,今夜讓眉兒伺候您吧。”
藺長星無于衷,轉到一旁給自己倒了杯水,看也不看那子,“母親讓你來的。”
那子怯了半日,見藺長星非但沒有親近的意思,反而不悅。在燕王妃面前做事,是個有眼力勁的,忙翻下床跪著,發抖著回:“是。”
“披件裳回去,與母親說,我院里不需要人伺候。”
那子聞言咬住下,眼中掠過不甘,不敢相信世子就這樣推走。他這般溫清雋的郎君,早就傾心,只恨份低微不得接近。
好不容易得了這個機會,哪怕連個通房都不是,只要能伺候他一夜,也是的福分。
于是直起腰,出抹上大片的,委委屈屈地嗲聲問,“世子爺,可是眉兒做錯了什麼?”
這番作和腔調,藺長星不至于不明白,與那廣云臺的姑娘無異。
他眉眼逐漸漫上不耐煩,似是有火要發,低頭將手中杯子轉了兩圈。再開口,聲音依舊溫潤,“不是你的緣故,我讀書累,只想早些歇息。你下去幫我傳個話,以后我的屋子,沒有允許,誰都不得隨意進。聽見了沒?”
Advertisement
最后一句陡然拔了音調。
“聽……聽見了。”
眉兒慌慌張張下去后,藺長星煩躁地將手中瓷杯往桌上一砸。杯子磕得碎了半個,叮當兩聲滾在木地板上。
這才將中的氣勻。
他揚聲喚來木耘,“把床上的件全換了,還有這七八糟的香爐都給我扔出去,熏得頭疼。”
木耘本以為王妃疼世子,世子爺定會高興,誰知道竟頭一回見他發怒。
莫不是嫌眉兒姿不夠?
后幾個人作麻利地忙起來,藺長星著太,站在雕花的圓格窗邊。一枝子夏花長在窗外,生機,遠湖水上波粼粼,漣漪漾開。
煩躁的心緒漸漸平緩,對京城的富貴人家來說,這本沒有什麼。是他在南州生活得久,脾氣怪罷了。
他知道王妃一片苦心,與其讓他在外面來,還不如家里給他安排個清白好管的伺候。
藺長星手出去,摘下朵花來嗅。麻煩,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許是被屋里的濃香刺激,他腔里窩了團火,發過脾氣后又竄上來,撲滅不去。
他不控地想謝辰,想起他們在南州的日子,想起那夜的纏綿,很快騰起旖旎的念頭。
莫說這兩天晚上刺激,就是在尋常夜里,謝辰兩個字對他而言也是煎熬和。
他曾無數回地夢見第一回吻他時,那時候他醉酒,有賊心沒賊膽,只敢用指尖的。
微微啟,半含不含地挨著他指尖,說話間送出縷縷意,“好嗎?”
他息著點頭,額邊沁了汗珠。
的手從他脊背后上去,摟住他的脖子湊到耳畔,吐氣如蘭地笑:“不是用來的。”
背后陣陣麻引得藺長星抖,子與子之間不留半點隙。他極力想掩蓋的不得之,到底被察覺了,謝辰如他所愿地過去。
作輕緩而細致,藺長星霎時耳鳴,只聽得見自己艱難的息聲,和謝辰在他里撥出的水聲。
他木訥到現在,不是人傻,純是被禮法規矩束縛。
他怕自己變壞,怕謝辰只是逗玩玩,怕笑話他的失態,厭惡他的念。
可他終究不是圣人。
他學什麼都快,包括接吻。
他不愿只他一人浮在海里,而除了溫耐心地給予他煎熬,眉眼似乎并未沾染旁的緒。
很快,他開始回應,兩手不再僵在一旁,沿的頸線往下探去。
這回終于到謝辰輕,渾發燙,嚶嚀出聲,偏過頭去氣。
他順勢埋進雪白溫熱的頸里,在那兒繼續點火。
招架不住,推開他說:“別這樣了。”
……
屋里人早就退了出去,藺長星躺在床上,舒緩自己的難。月無聲傾斜在屋,過了許久,他停下來,將自己整理干凈。
鐲子已經送出去,他暫時尋不到理由去見謝辰,總不能回回趁出門去堵,把人惹惱了更糟。
算算日子,太子殿下的冠禮在即,按理后宮會設家宴。他打聽過,皇后娘娘最喜歡謝辰,到時定會昭進宮,他總有機會再見一面。
來日方長。
正如那夜,先撥的他,后來想走也沒走掉。如今一樣,躲沒用,他不會放手。
猜你喜歡
-
完結1860 章

鳳唳江山
戰功赫赫的太子妃重生成廢柴醜女,精分世子強寵不成反被虐。
331.5萬字8 22400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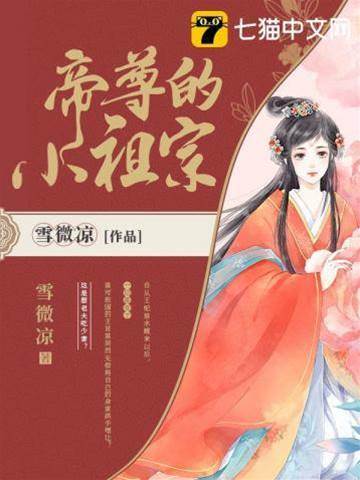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917 章
失寵王妃
墨府二小姐墨柔柔癡傻膽怯,上不得臺面,被太子退婚,淪為了京城笑柄。正當眾人以為她嫁不出去之時,京城首富之子蘇九生和蜀王朱元若爭相求娶。最后蜀王抱得美人歸。蜀王的求娶打亂了墨柔柔的計劃,于是她天天對著蜀王搞事情。成親前,她找人給蜀王施美人計,敗壞他名聲;成親時,她找人搶婚,搶了蜀王,讓他淪為笑柄;成親后,她天天作妖,每天都想著怎麼失寵。蜀王說:“失寵是不可能失寵的,我家王妃有點傻,得寵著。”
111.4萬字8 14385 -
完結578 章

毒醫凰后:妖孽世子霸道寵
癡心錯付,血染佛堂,她是名門嫡女,卻被未婚夫庶妹亂棍打死。 再睜眼……她是華夏鬼醫聖手,心狠手辣的殺手女王,身負毒王系統,一根銀針,活死人,肉白骨;一雙冷眸,穿人骨,懾人心。 當她穿越成了她……一毀渣男天子夢,二踩庶妹成小妾,三送后媽七隻鴨,四虐親爹睜眼瞎……古代生活風生水起,只是暗「賤」 易躲,明、騷、難、防! 他是腹黑神秘的妖孽世子,傲氣孤高,不停撩騷。 當他遇見她……「天下江山為聘,地鋪十里紅妝,我娶你」 「歷史有多遠,請你滾多遠! 關門,放狗」 他上前一步,將她打橫抱起,壓倒在床,邪魅一笑:「一起滾,滾出歷史新高度」
114.9萬字8 451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