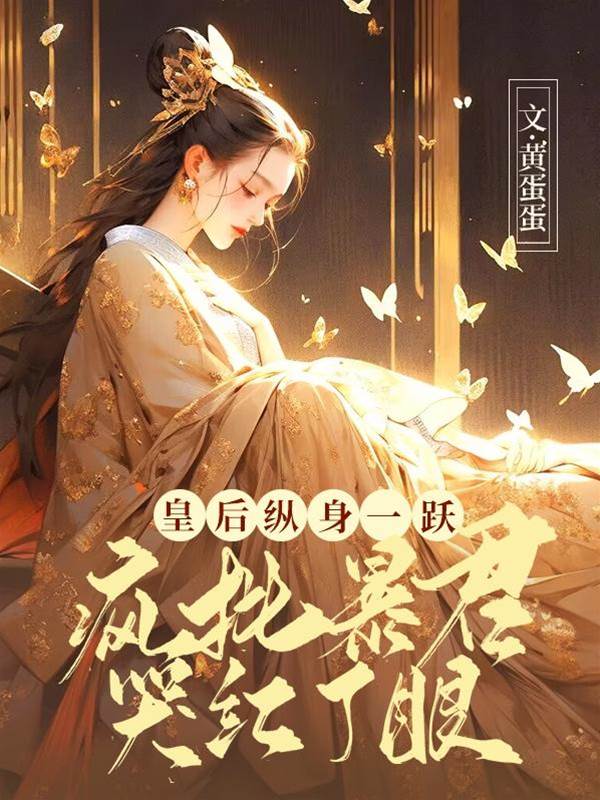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嫁給殘疾首輔衝喜》 第59節
,就著聞致的手迷迷糊糊將藥丸含中,又“呸”地一聲吐掉,皺眉道:“難吃!”
解酒丸是自己配的,這會子倒嫌棄難吃起來。
聞致心中一,覺得醉酒的樣子一點也不似平常沉靜淡然,任得可怕,連眉梢眼尾都是春瀲灩的嫣紅一片,像是四月盛開的荼蘼花。
“好熱,好暈……為何不開窗?”明琬又扭起來,手去解淡緋的春衫。
因為醉酒神誌不清,索了幾次都沒能順利解開裳,登時生氣悶氣來,用力扯著領。
聞致怕這般蠻力傷到自己,隻好單手重新倒了藥丸在掌心,另一隻手騰出來按住明琬扯領的腕子,將撈到懷中錮住,低聲道:“夜裏冷,你飲了酒不能吹風。別,飲了解酒丸會舒坦些。”
他說話時腔震,聲音沉而安定。明琬不再扯裳,隻是扭過頭,緋的抿得的,就是不肯吃藥。
聞致沒有法子,隻好擱了藥丸。
明琬按住了他的手,掌心滾燙。
聞致微微訝然,抬眸向明琬因醉酒而格外豔麗的容。
明琬雙目迷蒙,搖搖晃晃湊近腦袋,兩手啪的合攏一拍,捧著聞致的臉頰疑道:“聞致?是你嗎?”
“嗯,是我。”下手沒輕沒重的,聞致覺臉上麻疼,蹙眉拉下的手握在掌心,問道,“怎麽了?”
明琬輕輕打了個嗝,眼中泛濫的水不知是酒意還是淚,抿著輕聲道:“聞致,我難……”
類似於“撒”的語氣,令聞致心尖一。
他問:“哪裏難?”
“這裏。”拉著聞致的手,按在了自己的心口。
掌心下紊的心跳,令聞致霎時一震。他目幽深灼然,深邃得幾乎恨不得將明琬的靈魂吸其中,占為己有。
Advertisement
明琬將暈乎乎的腦袋抵在聞致的肩頭,悶聲道:“聞致,我當初總是在想,不管我嫁聞府的初衷是什麽,我都努力去彌補和改變了,可為何你總是連好好同我說句話都不肯,為何遇到問題從來不顧我的任意為之?現在回想起來,那樣患得患失的自己,真夠傻的。可是聞致,我好不容易忘了你有了自己的生活,你為何還要來招惹我呢?你難道未曾聽過一句話麽:世上哪兒有什麽破鏡重圓,遲來的深比草賤……”
燭火搖曳,聞致心中仿若被鈍刀來回割著,不自攬了明琬的肩,沉聲道:“我說過,我們可以重新開始,這一次,換我照顧你。”
“不。”明琬無拒絕,醺醺然道,“你說世上的並非千篇一律,說占有偏執亦是有,可是聞致,我又不是狂,不過是千千萬萬平庸子中的一員,為何就不能擁有一份甜平等的?”
“明琬……”
“我要懲罰你!”
明琬忽的抬頭,瞪著聞致深邃的眉眼,加重語氣道:“我要狠狠地懲罰你!”
夜幕籠罩,塵世的喧囂還未散盡,仿佛萬千華都落在明琬眼中。聞致結滾,半晌沉啞道:“你待如何懲罰?”
明琬掙他的懷抱,搖搖晃晃起,歪往寬敞的床榻上一坐。虛眼許久,忽然想到什麽“好主意”似的,命令聞致道:“你,給我跪下!”
聞致瞪大眼,眸中滿是不可置信。但畢竟是經過大起大落之人,他很快恢複了麵上的鎮定,盯著明琬低沉道:“你醉了,明琬。”
而且醉得不輕,連自己說了什麽胡話都不知道。
明琬大概覺得他此時的表十分有趣,瞇著眼晃腳尖道:“你不是想和我重歸於好麽?就這點誠意?當初你躺在榻上,我哪一次不是躬半跪給你施針?”
Advertisement
每當聽提及當初,聞致就像是被住了命門般毫無招架之力,所有的清高與疏離皆不攻自破,潰不軍。
除了父母天子,他此生從未跪過任何人,此時卻將下裳一,輕而緩慢地屈膝,而後膝頭重重落在腳榻上,並非隆重臣服的雙膝跪地,而是以一個虔誠的姿態單膝而跪。
他的上依舊是拔的,無一狼狽之態,隻是半垂的眼睫遲遲不願抬起,在燈火的暈染中微微。
下一刻,一隻巧的繡花鞋橫到眼前。
榻上的醉貓翹起一,以腳尖抬起聞致的下,迫他仰起頭來。若在旁人做來是折辱極強的作,偏生配著醉眼朦朧的樣子,卻人生不起氣來。
惡人先告狀,委屈道:“首輔大人為何不肯看我?”
聞致強住心底的難堪和翻湧的燥熱,單手握住纖細的腳腕,警告道:“阿琬,別鬧了。”
“這便是鬧了?還不夠呢,我可沒罵你嘲諷你,也沒有將你趕出門。”明琬又打了個酒嗝,撐著腦袋皺眉道,“給我鞋寬。”
聞致五指一,灼熱的視線下移,落在那隻秀氣的腳上。而後依言,生認真地為除去鞋。
的腳很是纖細幹淨,玉琢而似的,帶著微微的。還未多看一眼,榻上的醉貓卻是又改了主意,起住聞致的下,渙散的瞳仁盯著他許久,像是在研究一個新鮮件似的,又像是在權衡什麽。
接著,小心翼翼靠近,去嗅聞致那兩片薄而好看的。
聞致一驚,微微側首錯開了的瓣。
盡管他明琬的親近,了整整五度春秋,盡管的每次靠近都像是在撥他心底最後一理智的弦……可他也清楚地知道,明琬醉了,醉得難以控製言行,這些所作所為非本願。
Advertisement
他不能,再讓明琬厭惡他了。
可惜,酒醉的登徒子顯然誤會了聞致的一片好心。
明琬皺眉,很是不滿的樣子嘟囔:“別掃興!”
於是生生扳過聞致的臉,對著他因驚愕而微微張開的啃了下去。
兩片磕在一起,一時間兩人都悶哼了一聲。疼痛讓聞致決堤的理智稍稍回籠,他推了推明琬,皺眉道:“別這樣,你會後悔的……”
等到明天醒來,定會惡心自己吻了一個不通,且又神有疾的瘋子。
話音未落,他忽的悶哼一聲,熄起來。
明琬輕而易舉地按住了他的位,很是得意般欣賞他震驚難堪的神,彎著酒氣迷蒙的眼睛道:“你知道麽?此位活助興,按之有奇效。”
聞致眼角連著耳尖皆是一片淺紅,眸深沉仿佛醞釀著洶湧的風暴,咬牙按住明琬的手,一字一句艱難道:“明琬,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放手。”
“不。”明琬梗著脖子和他對峙,惡狠狠道,“我不會對你言聽計從了,我要懲罰你,讓你也嚐嚐而不得、被人輕視作踐的滋味。”
說罷,一口咬上聞致的頸側脈,似在宣泄自己全部的委屈與痛意,直至嚐到了淡淡的腥味。
自始至終,聞致形僵如鐵,呼吸急促微,任由為非作歹,肆意捉弄。
如果,這能讓消氣的話,他甘之如飴。
明琬不知自己是何時睡著的,醒來時天還未全亮,殘燭昏暗,錦帳生香,頭疼得像是要裂開。
懶懶抬起手臂擱在額上,卻到了旁睡的形。
一怔,下意識扭頭,頓時一僵,瞪大眼宛若五雷轟頂,山崩地裂。
聞致安靜地仰躺在一側,雙目輕閉,側如神祗,借著昏暗的,可看見他的頸項滿是……那樣的痕跡。
Advertisement
視線再上移,正好對上了聞致黑沉的眼眸。
‖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線‖上‖閱‖讀‖
第58章痕跡
明琬約記得是小花出主意,從房中取了一壇好酒相贈,說夜宴時讓與聞致邀月對酌,趁酒酣正濃,兩人再開誠布公地將心中嫌隙說清楚。
當時,小花寶貝似的抱著那壇酒,賊兮兮說道:“嫂子可別小看這壇酒,我可是珍藏了好些年,和普通酒大不相同,保管一杯口冰釋前嫌,兩杯下肚便是掏心窩子的話也能挖出來,三杯腹忘憂忘恨,飄然若仙滿室生春。”
明琬很是懷疑小花這主意的可信度。若世間真有如此酒良藥,可解千愁化萬憂,沒有生老病死怨憎嗔癡的煩惱,還要這大夫作甚?
倒了一杯酒嚐嚐味道,是微甜的,頗有果酒的芬芳,便忍不住將一盞都飲盡了。
從前要嚐藥辨藥,為了保持鼻舌的靈敏,明承遠從不許沾烈酒,隻有在逢年過節時才能嚐一碗用水和糖衝淡的甜酒解饞,故而明琬的酒量素來極差。那壇竹葉春雖說口甘甜,卻後勁極大,沒過一盞茶的時辰明琬便飄飄然不知今夕何夕。
後來,好像聞致來了……
“我要狠狠地懲罰你!”
“你,給我跪下!”
“你不是想和我重歸於好麽,就這麽點誠意?”
“給我寬鞋。”
“別掃興!”
明琬捂著鈍痛的腦袋,昨夜醉酒後的零碎記憶爭先恐後湧了上來,記憶仿佛籠罩著一層橙紅的薄紗,朦朦朧朧,辨不清是真是幻。
明琬記得好像是自己先咬了聞致,糊裏糊塗對他肆意輕薄了一番,後來不知怎的,等回過神來時已被聞致抵在榻上兇狠地親吻。聞致的呼吸很燙,腦後半披散的長發自肩頭垂下,溫地掃過明琬的鼻端,惹得扭頭連連打了兩個噴嚏。
聞致的子很沉,及上實勻稱的,明琬難以呼吸,便皺著眉掙紮起來,推搡之間似乎還抬手打到了聞致的臉頰,很清脆的一聲響。
霎時,兩人都怔了一怔。
明琬醉得厲害,渾渾噩噩地看著聞致,被他盯得有些心虛忐忑。明琬以為聞致會生氣打回來,但他沒有,隻是輕輕握住的指尖送到邊一吻,啞聲道:“小心些。”
再後來如何,什麽也不記得了。
此時,被趁醉捉弄輕薄的對象就躺在側,目深沉地著,靜默無聲,勝過千言。
明琬腦中一片空白,忽的坐起挪遠些,薄薄的錦被自上落,出了純白的裏……好歹還算裳完整。
見下意識往榻裏挪移的作,聞致眸黯了黯,也跟著坐起來,薄紗錦帳跟著輕輕鼓,燭過紗帳暈染一片昏暗曖-昧的暖黃。聞致起時,襟隨著他的作微微敞開些許,明琬看到了他從頸側到心口的一溜兒痕跡……
就,很令人窒息。
明琬調開了視線。
倒不是因為難看或是別的什麽,聞致無論何時都是賞心悅目的,不知是不是燭火的緣故,他的麵容不似平日那般冷白嚴肅,微豔,襯著襟下約可見的痕跡頗有種說不出的清傲靡靡之氣……讓人口幹舌燥,難以直視。
明琬剛考太醫署的那年也喝醉過,拔了老師種的藥草,還跳到池子裏撈了半個時辰的月亮,最後被氣得吹胡子的老師送到明承遠那兒,很是
猜你喜歡
-
連載1163 章

云鬢亂:惹上奸臣逃不掉
守寡三十年,卻發現自己的老公沒死,躲在外面又養了一個!婆婆、叔嬸都知道,可為了逼她當年做馬,獨獨瞞著她!到死,她都沒有享過一天福!再次睜眼,柳云湘重生到嫁進靖安侯府的第三年。既然侯府對她不公,她便顛覆這一切,要背叛她的渣男付出代價!成為天下第一女商賈,權傾朝野!只是,上輩子那個把她當替身的奸臣嚴暮,怎麼黏上來了?不是應該為了扶持白月光的兒子登基,甘愿犧牲嗎?
198.3萬字8.46 397182 -
完結399 章
穿越后我在四爺后院當團寵
都說四爺是個高冷不好女色的人,為什麼她遇見的這貨夜夜找她纏綿,纏的她腰酸腿軟還要被他其他小老婆算計。好不容易熬到宮里升了官還是沒有一天安生的日子。...
90.2萬字8 10191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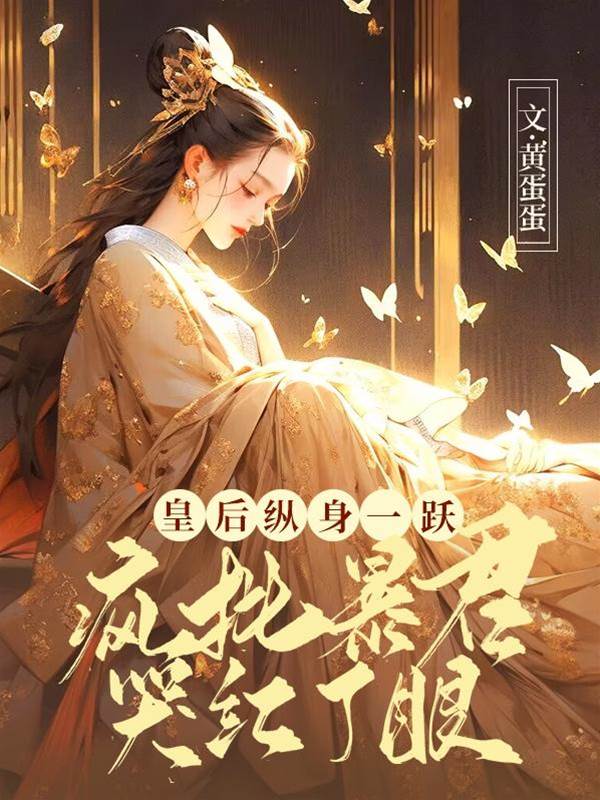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631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49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