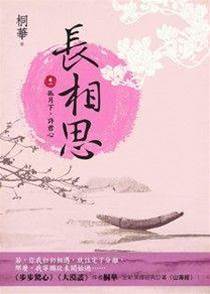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無鹽為後》 第二百九十九章
朱翊鈞領著太子從外面回來,太子小臉紅撲撲的,顯然還是十分興,一進殿,就看到榮昌和昭宜,一騎裝,雙手頂著銅盆過頭的站在側邊,銅盆里顯然還裝了水,也不知道兩人頂了多久,現在都是滿臉通紅,手發抖,再看看肩膀上的水跡,顯然是已經抖了一點出來。
「這是怎麼了?」朱翊鈞奇道。
「別管們。」王容與說,「宴席已經散了嗎?」
「不散不行,都喝的五五六六了。」朱翊鈞說,王容與湊近了問,「陛下也喝了不吧。」
「我只略沾了。」朱翊鈞笑說,「那些個武將,有個打頭的,就一波一波的來給朕敬酒,就是做做樣子,不知不覺也喝了不。」
「陛下先躺一會吧。」王容與說,又蹲下來看太子的況,「你的臉怎麼這麼紅啊?今天一天都跟著父皇,高興了?」
太子笑瞇瞇的點頭,「母后,大姐姐和二姐姐怎麼了?」
「們犯錯了,母后罰們呢。」王容與說,手去太子的後背,「今天出汗了嗎?」
「黏黏的。」王容與說,「趕去泡個熱水澡,讓人好好按按,然後就去睡覺吧,今天玩了一天,落下的功課,明天該要補上才是。」
太子看著依舊是和平日一樣溫的母后,再回頭看看的頂著銅盆的姐姐們,連連點頭,乖巧的讓人帶著他離開。
本來和父皇過來,是還想和母后黏糊一下。
還是等母后不罰姐姐的時候再來吧。
等到太子走後,朱翊鈞看著榮昌,「犯什麼錯了,讓你母后這麼生氣。」
榮昌抿不說話,顯然在賭氣。
「跟父皇說說,父皇知道怎麼回事,也好跟你們母后求,不然,這舉的不難啊。」朱翊鈞倒不至於跟兒生氣。
Advertisement
他又小聲對王容與說,「向來兒和眼珠子一樣,現在又這麼捨得了。這人來人往的,你讓們站在門口,不得了是其次,自尊多傷啊。」
「就是要讓們難,不然懲罰還有什麼意義。」王容與瞟他一眼,「陛下別管了,一塵土,去泡個澡吧。」
「懲罰也是意思意思就可以了。」朱翊鈞說,「難道是犯了天大的錯誤?」
「錯不在大小,懲罰卻不能兒戲。」王容與說,「我說罰們頂半個時辰,但是認錯就可以提前結束,你看,是像認錯的態度嗎?」
「這是第一次被你懲罰吧,這心裡肯定也委屈著呢。」朱翊鈞還想給兒求。
「你快進去洗澡吧。」王容與說,「我心裡有數。」
朱翊鈞起,趁著轉的功夫,對榮昌眨眼說,「錯了就跟母后認個錯,服個,母后還能不心疼你們嗎?」
榮昌還是抿不說話。
朱翊鈞嘆氣,去浴室了,王容與說個小太監給陛下按按,騎了一天馬,肯定酸痛。
王容與坐在那,好整以暇的看著兩個兒。榮昌和昭宜才到獵場邊上,就被母后的人帶回來,王容與問們知錯嗎?榮昌想連獵場都沒進去,犯什麼錯呢?
於是梗著脖子,問自己犯什麼錯了。
王容與就讓們頂著水盆在頭上,「那就什麼時候想清楚了再放下來。」
嘩啦~昭宜的手一,剩下的半盆水都澆在自己頭上,登時變落湯,可憐兮兮的。
「給昭宜公主重新滿上。」王容與說。
榮昌看著王容與,「母后,昭宜不想去的,是被我拖去的,母后要罰就罰我,不要罰了。」
「昭宜,你覺得呢?」王容與問。
「昭宜甘願罰。」昭宜說。
Advertisement
「那你知道錯了嗎?」王容與問。
昭宜看一眼榮昌,榮昌的子,肯定不會先開口認錯,搖搖頭,「昭宜不知道哪裡錯了。」
「那就繼續頂著吧。」王容與淡淡說。
看昭宜形容狼狽,還要抖著手舉起滿盆的水,可預見不過多久,昭宜就又要被水淋了。
「我知道錯了。」榮昌紅著眼睛說,對王容與說,「我知道錯了,我不該今天還去獵場的,母后說了今天不能去的,我不該因為好奇,想要自己去看。」
就像昭宜總是默默的跟隨,支持的所有決定,也比心疼自己,更心疼昭宜。
「我不該不顧昭宜的勸阻,還非要帶一起去。」
「我不該不認錯。」榮昌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我不該跟母后犟的。」
王容與點頭,宮人就上前去把兩位公主頂著的銅盆接了過來,「帶公主去整理一下儀容。」
等榮昌和昭宜再妝容整齊的進來,王容與面前的桌上已經擺好了飯菜,「來吧,都了吧。」
「母后也跟著我們沒有吃呢。」榮昌走過來說,被昭宜提醒了,「我錯了。」
「既然已經認錯,這事就過了。」王容與說,「母連心,我看著你們挨,這飯怎麼能吃的下。」
榮昌低頭拉著碗,有些歉疚,興緻不高,又開始掉眼淚。
王容與給夾菜,「是不是知道錯了,還是覺得委屈?」
「獵場我每天都去了。」榮昌說,是比一般的閨秀都活潑些,如果是在宮裡不覺得,後來去宮外公主府玩,姑母們總會請很多閨秀來作陪,一個個文靜,不用明說,榮昌也覺得自己的不同來。
但是並不在意,既然母后都沒有說要改,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Advertisement
是嫡長公主,大可以瀟瀟灑灑,紅塵作伴。
但是今天母后就告訴,就算是深得父皇母后喜的嫡長公主,也是不能盡的瀟瀟灑灑。
「今天不能去獵場的原因,母後跟你說過嗎?」王容與耐心問,是不想拘著榮昌,但是榮昌要是被教一個不看場合肆意妄為的任之人,那以後收到的所有責難和辱罵都是這個母親的過錯。
榮昌點頭,「可是又不是沒有和父皇一起去過獵場。」
「大皇子也在,為什麼我就去不得。」
「因為大皇子是男兒,而你是兒。」王容與說,「我也和你父皇一起去過獵場,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就不會去。」
「男有別。」王容與說,「因為我的放鬆,在宮裡,這四個字你很模糊,但是等你出嫁了,去到宮外公主府,有你自己的社圈,你還這樣不分男外,就要吃大虧了。
「可是獵場里的臣子,雖然是男也是臣,我是子卻是君,為何要以君避臣?」榮昌不服的說,「我和大皇子常在獵場賽馬,這個時候再來說男有別,那當初就不算男有別嗎?」
「母後來告訴你,現在男有別到什麼樣的程度。」王容與說,「男七歲不同席,便是一個娘胎里出來的骨至親,到七歲以後,能面的機會也是屈指可數,子十歲后連父親的面都不能常見,這才是現在的常態,現在的習以為常。
「而像你現在這樣自由散漫,不避諱父皇兄長,才是和常理不合的。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我不想讓你過那樣的生活?我不希你在自己家裡,見自己的父親,和自己兄弟姐妹玩耍都都有那麼多規矩。」
「是的,你是公主,在臣子面前,你是君。」
Advertisement
「當初山公主也是這麼想的,弟弟是皇帝,是皇帝的姐姐,皇帝能有三宮六院,為什麼不能有?」
「如願有了,當時是不是開心的我不知道,但是死了后肯定是不高興的。死了一千年,還是有人對口誅筆伐,不得安寧。」
「你也想做那樣的君嗎?」王容與問。
榮昌猛地抬起頭,滿臉紅,「母后如何能拿我去跟山公主比?」
「你如今已經把你君的份放在你是子的份之前,那未來還有什麼不可能?」王容與說,突然捂臉嘆道,「都是我的錯,我太縱著你了。」
「母后,我不是這樣的。」榮昌哭著說。
「母后,榮昌沒有那個意思,只是小孩心,只是好勝心強想要去比較一番,沒有覺得自己是君,就無所不能。」昭宜替榮昌說道,「只是為了和母后回才說了這樣的話,心裡清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
王容與擺擺手,「母后不知道你能聽進去多,便是你父皇,天下之君,也有很多不能做的。你若是不明白,就慢慢想吧。」
「你當然可以任意獨行。」王容與說,「只是你做的任何事都在別人眼裡,出格一點便是留在史書上,讓父皇母后陪著你一起丟人罷了。」
「我不會的。」榮昌說,「我不會做不好的事,我不會讓父皇母后因為我而丟臉。」
「在規矩允許的範圍,活的輕鬆自在。」王容與說,「這是我的事原則。」
「從來沒有存在過完全的自由。」
榮昌點頭。
榮昌和昭宜離開,朱翊鈞才施施然回來,「嚴母教子結束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231 章

鬼醫本色:廢柴醜女要逆天
她是二十一世紀醫毒雙絕的古武天才。她是東陵帝國第一武將世家嫡係唯一的血脈,一雙黑色的眼珠,讓她一出生便被斷為廢柴。一朝穿越,她成了她。黑髮黑眼便是……廢柴?她冷笑,“我倒要看看誰是廢材!”手握醫療係統,坐擁逆天神獸,修真經,馭萬獸,區區凡胎肉體隨意行走六界,亮瞎眾人的狗眼!渣姐加害欲奪權?揪出姦夫讓你萬人辱罵!敵對太子欺上門?率領萬獸踏平你太子府!說她囂張?說她跋扈?嗬!我就囂張我就跋扈,你又能奈我何?不過,這個一出場就震驚天下的男人冇病吧,一看到她便要剜她雙眼?“挖我的眼?”她輕笑……
408.9萬字8.18 75895 -
完結1256 章

絕世醫妃
現代超級學霸風雲菱,醫毒雙絕。一朝穿越,感受很強烈。一針就讓渣男王爺軟弱無力,耳刮子唰唰響,告禦狀,陰謀陽謀齊下,光明正大休夫!休夫後,大小姐風華萬千,亮瞎眾人狗眼!溫潤皇子表好感,渣男警告:“風雲菱是我的女人!”謫仙美男表愛慕,渣男:“她,我睡過了!”某女:“睡,睡你妹,再說讓你做不成男人。”某男:“那,做不成男人你還要嗎?”“滾……”
223.4萬字8.18 154998 -
完結1487 章

妖孽狼君別亂來
她一泡尿讓王爺『濕』身了,王爺翻身而上,要了她一身作為回敬。數月後。「美人,做我的女人如何?」「王爺,我是二手貨。」「沒關係,本王就是要有經驗的,這樣才能侍候爽了本王。」反正,她的第一手也是他,多一手少一手無所謂。「王爺,這孩子是別的男人的……」「美人放心,本王會視為已出的。」反正,這孩子本來就是他的。「王爺,我今天戴這頂帽子出門,如何?」他望著她頭頂的綠帽,狼眸微瞇,隨手給她換了一頂小紅帽,「美人,你說過的,小紅帽更適合你,乖,你要懂得享受就乖乖躺好,你要想逃爺也有本事讓你乖乖躺好……」
279.9萬字8 45684 -
完結212 章

將軍三嫁
一個他不要的女人居然成為了搶手的香餑餑,宋瑾瑜表示這些人還真是喜歡撿他剩下的。 無奈一張圣旨,那個他之前千方百計擺脫掉的女人居然又變成了他的夫人,這特麼的還讓不讓人活了! 圣心已決,斷無反悔。 宋瑾瑜裝死表示天要亡他。 慕容金也很頭疼,聽說她這次要嫁的人和她當年有所牽扯,可是為什麼她一點都想不起來? 喂!她身邊的男子都是個頂個的英雄好漢,純爺們,那個長著一張比女人還漂亮面孔的小白臉真的是男人嗎? 慕容金表示懷疑! 內憂外患的,這次容不得她不嫁。 之前種種,她真的想不起來了,這人既然這麼渣,那就大不了和離唄。 宋瑾瑜暴走:“你以為我想娶你?那叫迫于無奈!” 慕容金撓頭:“沒事,我有軍功,大不了以后拿軍功和陛下換一張和離書!” 宋瑾瑜一
56萬字8 7353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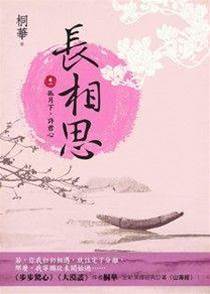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