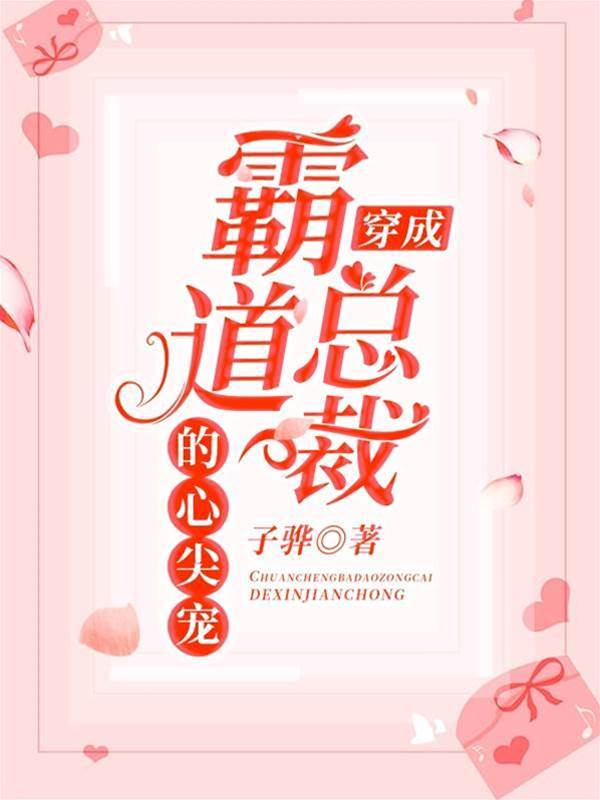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錦繡大明》 第二十五章 處心積慮
張府前廳,楊震有些不耐地坐在椅子上,雖然他面前擺著好幾樣茶點,可他卻連都沒有心思去。他只是不斷把眼往廳外掃,可都半個時辰了也不見人來。
在得伍知縣的點撥后,楊震就來到了張府求助。不過張家人的態度卻頗有些曖昧不明,要說不肯幫他,尋常人進不去的府門卻準他進了,還在前廳給他備下了茶點,招待周到;可要說肯幫他,這都半個時辰了,也不見個管事的出來招呼一下,這就讓楊震不他們的心思了。
就當楊震的忍耐到了極限,想就此離開時,一名穿著上好錦緞面料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他也沒有解釋自己為何來遲,仿佛有人等著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我是張府管事張守禮,你就是楊震吧?”說話的他居高臨下地看著楊震,顯然是沒把這個年太當回事了。
楊震此時反倒顯得氣定神閑了,至他們還是派人來了。至于對方的態度,他是可以接的,畢竟是張府的人,向來是頤指氣使慣了的。他只是淡然一笑:“正是楊震。在下此來……”
他的話才剛開了個頭,就被張守禮揮手打斷了,他眼下這態度可一點都不守禮:“你是為了想救楊晨而來的吧?他犯的可是殺人重罪,就是咱們張家,也不能視國法為無哪!”說這話時他是一副正義凜然的模樣,仿佛這些年來張家橫行鄉里的事都不存在。
楊震當然不可能如此說話,只得賠笑道:“在下當然知道此事難為,但在下卻找到了一些證據表明家兄是被人嫁禍的,這才敢來貴府求助。”
“嗯?”張守禮的心里一,忍不住道:“你發現了什麼?”
楊震再次把自己從尸上的發現說了出來:“……就此可斷家兄絕不是那個兇手,行兇者當是第三個人。”
Advertisement
張守禮有些吃驚地瞥了楊震一眼,想不到他如此年輕竟有此膽和本事,不但去了義莊查證,還真他找出了一些破綻來。不過他的面上卻不聲,只是淡淡地道:“你這話雖然有些道理,但終究只是一家之言,未必會被府采信。而且你的份又是嫌犯的兄弟,到時候可就更難說了。”
“所以在下才來求助貴府,以張家在此的聲名,足以府衙相信另有兇手了。還張管事看在家兄曾與貴府有些的份上……”還是不等楊震把話說完,張守禮就出言打斷了:“我張家若開了口,楊晨自然不會有事。不過我們憑什麼要幫你們出頭,就憑他曾來過我們張府?真是笑話,這天下間來我張府的人多了,難道我們都要照顧到嗎?”
雖然他這話看似回絕,可楊震還是聽出了一些門道來,顯然他是要自己有所付出才肯為出面相幫了,卻不知這是不是張家主人的意思,他們又在圖謀什麼。
在沉默了一會后,楊震才道:“不知貴府要如何才肯幫我這一次?”
“聰明!”張守禮見他如此上道,心下一喜,說道:“凡事有付出才有收獲,你想救你兄長也是一般。只要你把自家在城南的那片地送與我們,你兄長這次的牢獄之災便可免了。當然,此案未必能破,他依然是本案的嫌犯,所以他舉人的份也必須剝奪了。”
“什麼?”楊震猛地提高了聲音,同時心下大怒。城南那片地他自然知道是父親的墳塋,現在張家要去自然不可能保留墓地。而一旦被奪去舉人份,兄長一生的追求也就徹底斷了,這怎麼能他答應呢?
“怎麼,你不肯答應?一條人命與一塊地一點虛名相比,孰輕孰重我想你雖然年輕總也分得出來吧。”張守禮冷笑道:“我也沒有太多時間等你細琢磨,你自己回去好好琢磨,想好了再來找我。不過有句話我卻要告訴你,你我是等得的,但在牢里的楊晨卻等不了太久。”
Advertisement
他這話也是實,不說府衙那隨時會開堂審案,就是兄長一直關在牢里對他的子也很不利,更別提眼下已是十月上旬,離春闈的日子已不遠了。
在一番看似激烈的心理斗爭之后,楊震終于咬牙:“我自然肯答應了,但是家兄那里我還需要去征詢一下意見。只是府衙卻不肯讓我見他,不知……”
張守禮似乎很喜歡打斷人說話,當即道:“這個不問題,明天你就可以見你兄長一面,其他的事到時再說吧。來人,送客!”
在將楊震打發走后,張守禮就急匆匆來到了后面的書房,見到了正在看書的張敬修。此時的張大管事早沒了剛才的氣焰,只安靜地站在門口低聲喚了句:“大爺。”
張敬修也不理會他,自顧翻看了一會書后,才慢條斯理地道:“把條件都和他說了?事辦得怎麼樣?”
“這楊震倒也不是個蠢人……”張守禮走進書房,把剛才和楊震所說的話都復述了一次,“他說要與兄長商量著辦,想來不會有什麼差錯了。”
“唔,能與聰明人打道總比和蠢人說話要好,聰明人對利害的判斷總是和我們一致的。那你就等把事做后再報與我吧,我也好爺爺放心。”張敬修揮了揮手,示意對方退下。
這麼件小事,對志向遠大,希有朝一日能像自己父親那樣立朝堂之上的張敬修來說實在算不得什麼,在吩咐下去后自然就被他拋到了腦后。
但他并不知道,他口中的那個聰明人此時正看著張家氣派非凡的府邸心里暗自冷笑:“看來一切都是你們張家搗得鬼了,而目的應該就是我家城南的那片地,你們還真是心積慮哪。”
Advertisement
原來在伍知縣向他推薦張家時,楊震就敏銳地覺察出其中有問題了。而在張府走這一遭,就更讓他確信這次嫁禍一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張家。在他們提出的兩個要求里,舉人顯然不可能真被他們所重視,他們可不是像姚家那樣的土豪地主,把個舉人,甚至是一個鄉試資格看得很重。所以城南的那塊埋著楊家兄弟父親的那塊地就是他們唯一這麼做的原因所在了。
同時,楊震也就猜到楊晨那次來張家赴宴后為何會又驚又怒了,顯然張家也曾向他提了這個非分的要求,而兄長必然回絕了他們。想不到以張家的份在明索不后竟還有如此卑劣的手段巧取。雖然他猜不出對方這麼做究竟是為什麼,但他一定不能他們得逞了。
帶著滿腹的心事,楊震往家里行去,不想在家門口卻看到了阮通與王海在張著,一見自己就奔了過來:“二郎,我們找到陸大年下落了。”
雖然本來找他的意圖已不存在,可楊震依然面上出一笑容問了聲:“此話當真?”他看得出來,這兩個兄弟為了自己是費了大力氣的,他不想因此讓他們的付出看著像白費一般:“他現在哪里,你們是怎麼找到他的?”
“咱們滿城都找不到他,又覺得他帶著老娘不會走遠,就想到了守株待兔這個笨法子。我和王三流守在他家門口,好幾日下來直到今日早晨,才見他鬼鬼祟祟地回家。在家里拿了些東西后,又走了。因為不好拿他,所以我們就跟著他,看他去哪。沒想到,他居然……”說到這里,阮通咽了口唾沫,似乎顯得很是張:“他進了一個氣派不小的宅院。我們事后大廳才知道,原來那竟是張家的一個別院。”
Advertisement
說完這話他們看向楊震的目就有些猶疑了,但楊震卻只是輕輕點頭:“果然如此。”
“怎麼,二郎你早知道此事與張家有關?”王海吃驚道。
對這兩個兄弟,楊震也不瞞,把自己幾日來的調查和猜測都說了出來:“……所以當你們說陸大年藏在張家別院時我才不意外。”
“原來……原來竟是如此。那二郎你有什麼打算?”在兩人面面相覷了好一陣后,才有些吃力地問道。
楊震看著他們,眼中帶著暖意:“你們到了這個時候還肯問這句,就說明我楊震沒有白了兩個朋友。不過接下來的事,你們就不要過問了。我楊震除了兄長就是孑然一,你們卻不同,你們還有父母兄弟,有些事還是不知道的好。”
“二郎,你是我們不顧義氣地在這時候什麼都不做嗎?”阮通有些不快地說道。王海卻是一聲不吭,顯然看得比這位兄弟要長遠些。
“其實在我和兄長見上一面前,我也不知自己接下來要怎麼辦。我面對的是張家,我可不想因為這點事而連累了你們兩個好兄弟。我知道你們很講義氣,但這事實在太大,你們還是……”楊震地說道。
“阮五,二郎說的是,這事咱們也幫不上什麼忙,我們還是走吧。”在王海的勸說下,阮通終于不再堅持,有時候形勢總比人要強。
就在他們轉走時,阮通又突然回過來:“二郎,你忘了問我們人在哪個張家別院了。”張家在縣里有好幾別院,他說的倒也在理。
但楊震卻只是淡淡一笑:“現在還不能把他怎麼樣,知道了他的下落又如何?”他這話雖然說得輕描淡寫,可阮通他們卻覺到了的寒意。
PS:昨天,路人發現了一件足以聞者傷心,見者流淚的悲催之事,原來作者后臺的那個作者有話說的容是傳不到書里!!!!!這實在太悲劇,太尷尬了,路人之前有不章節都寫了些各種求的文字,居然都沒有被人看到,真是浪費了我那赤誠的一片心哪!!!
所以現在路人只能在這兒鄭重求一次收藏,求一次推薦票,求一次評論,求一次點擊了。各位,看在路人如此悲催的份上,就給我點安吧!!!
另外,之前章節我也稍作改變,把各種求放了上去,要是后來讀者看到,就不要挑路人這個刺,只要收藏,投票就好了o(∩_∩)o
最后,今天終于有了封面,所以在此多求一次收藏啊啊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71 章
一世紅妝
林慕夕一夜之間穿越到一個叫做青木的小國家。她成爲了林府的娣長女。可是她這個大小姐做的真是憋屈,不但父親不疼,還從小失去了母親。在家裡常年遭受弟妹的欺侮。可是現在的林慕夕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懦弱的林慕夕。她可是從現代來的百富美。不但知識淵博,還身懷各種技能,怎麼可能繼續任人宰割?於是,林府開始雞飛狗跳。林慕夕一個
50.4萬字8 26193 -
完結548 章

農門桃花香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穿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村姑。村姑就村姑吧!姑娘我只想過平凡日子,種種田,養養花。蝦米?爲情自殺?情郎死了,她卻被十里八鄉的人唾罵,天降掃帚星,斷子絕孫星,造孽剋夫星……連累父兄下獄,母妹受欺,還有一大堆極品親戚。這小日子可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容易!柴米油鹽,事事鬧心。窮鄉僻壤,觀念閉塞。沒有良田
163.8萬字7.82 54859 -
完結2261 章

影視世界當神探
陸恪重生了,還重生到了美國。但他漸漸發現,這個美國并不是上一世的那個美國。 這里有著影視世界里的超凡能力和人物,他要如何在這個力量體系極其可怕的世界存活下去? 幸好,他還有一個金手指——神探系統。 一切,從當個小警探開始……
416.5萬字8 46115 -
完結1136 章

薛小苒的古代搭夥之旅
薛小苒穿越了,睜眼就落入了荒無人跡的原始森林中,撿到一個半死不活又殘又醜的男人,兩人在叢林中苦逼求生,掙紮著相攜走出叢林,開啟一段異世生存之旅,可就在日子慢慢朝好的方向轉變時,男人不僅越變越好看,連他的身份都陡然一變!哎,說好的搭夥過日子呢?怎麼變得不一樣啦?那誰,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這是一個吃貨在古代吃吃喝喝,混混日子,順便拐個極品郎君的故事。
208.3萬字8 36899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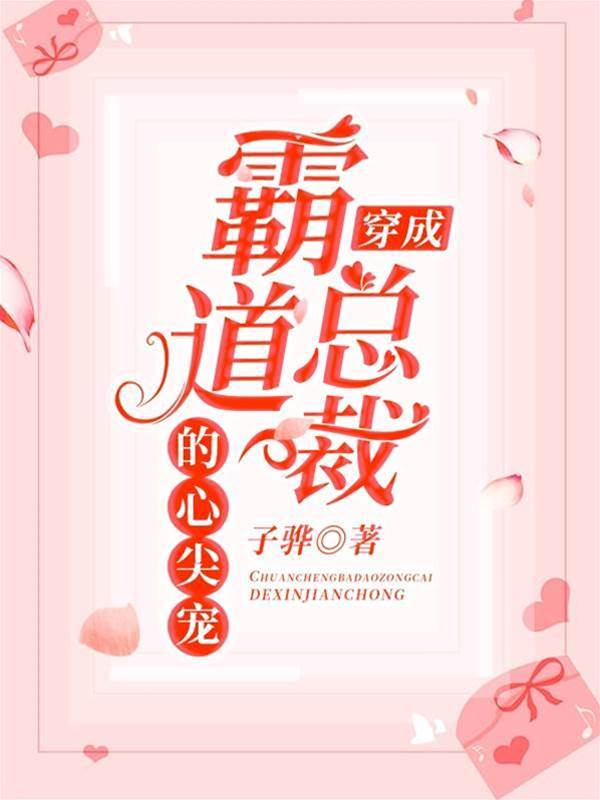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7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