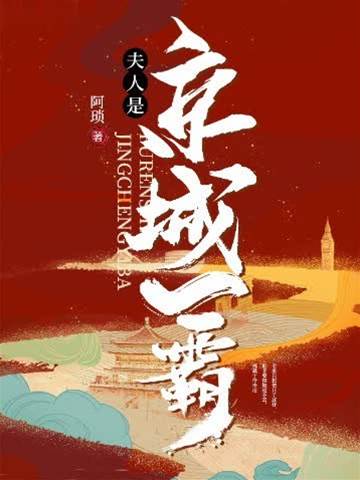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庶女毒後》 連月大雨
“清良郡主如果一直打算這麼胡言語,我們也沒什麼好談的了。”他起,作勢要走。
季莨萋知道他會否認,這件事牽扯太大,大到一經揭,朝後宮,都將譁然。
其實就三年前,季莨萋還不敢這麼肯定,畢竟那件事瞞得太了,除了前世的一些蛛馬跡,今世幾乎一點苗頭都沒看到,不過也幸虧了還急的前世的那些零零碎碎,在建立了天王樓後,這件事的調查,被提上了日程。
而最終結果,老實說,也是三個月前纔拿到的。
現在,如果不是太子突然婚,並不想這麼快手,這件事還需要從長計議,可以安排的東西應該更多,要想將司蒼宇以及他的黨羽一網打盡,太之過急,其實並不是好事。
可是現在沒時間了,所以,只能主約他出來了,打算用另一個方法。
“五皇子就不好知道,我到底要求你什麼?”
他停下作,轉首,目冷漠,“那你說。”
笑著比了比對面的椅子,“坐下吧,不用弄得這般水火不容,你我並不是敵人,至這一刻不是。”
不是敵人?
這是他今年聽過最好笑的笑話。收集他的人員名單,在所有有他勢力的地方使絆子,這要還不算敵人,那什麼纔算?
但他還是坐下,他倒要聽聽,還能編出什麼來。
“五皇子可知道,莨萋爲何這麼多年,一直未定親。”
司蒼宇眉頭一蹙,“這是郡主的事,我如何知曉?”
苦笑一記,眼底出黯然。
這還是司蒼宇第一次看到出這麼脆弱的表,不覺有些新鮮,只是這脆弱中,有多是裝蒜,相信只有自己知道。
Advertisement
“莨萋心裡念著一個人,那個人初見時,對我施以援手,再見時,對我翩然一笑,早在那個時候,我的心裡便有了他,心中抱著一個念頭,或許將來,有朝一日,我能與他相攜白首,只是子的青春太過有限,我今年便是十六,但他……”
“他如何?”初見時施以援手,方纔就說第一見太子,他救了,那說的,就是太子?
若是太子,那還真是新鮮,這些年來太子對如何,朝野上下誰人不知,一個司凌風不算什麼,但太子對,那心一直是足的,對誰都沒笑臉的司蒼斂,唯有對著季莨萋,纔會賞臉扯扯角,只要有的地方,他滿心滿眼也只看得見一個。
仰頭,似乎看出他心中的猜測,輕輕搖頭,“不是太子。”
他一愣,不說話了。
季莨萋繼續道,“不是司蒼斂,不是司蒼序,是另一個人。”
“誰。”
吐了口氣,苦笑,“這個五皇子不用知道,你只需知道,我願爲了他,與你結盟就是了。”說著,起,走到窗臺下的櫃子旁,拉開屜,從裡面拿出一個冊子。
將冊子遞到他面前,“你的名冊。”
他眸一斂,神驟變,盯著那本名冊,卻沒有去翻。
季莨萋今日的一舉一都太奇怪了,他不可能貿然行。
“上次我與康側妃有過約定,這個冊子,是我與的協定,現在冊子給你,放心,我沒有備份。”
有沒有,只有自己知道。
司蒼宇呵的冷笑一聲,還是沒有作。
見他始終不,嘆了口氣,“你何必這麼戒備,我若要對你不利,也不會半夜約你出來,孤男寡,我的名聲更重要。”
Advertisement
“這麼說半夜相見,還是你爲了安我的心?”
“可以這麼說。”
他不置可否,手翻了兩頁,看到某幾個名字後,眼眸瞇了起來,他翻到最後一頁,看清最後的那些新加的名字後,擡頭看著,眸冷,“清良郡主好本事,連那幾個小兵小卒也一清二楚。”
淡笑,了他這句“誇獎”,“這冊子就當我的誠意,我這兒還有些別的東西,需要勞煩五皇子。”
說著,從袖子裡掏出一節花枝,放在他面前。
他捻起來嗅嗅,挑了挑眉,“這花香,有些古怪。”
“此花爲罌粟,這是我特地找人從遠方帶回來了,這東西,飽含劇毒。”
他眉一挑,將花放下。
季莨萋笑了,“放心,這支花理過,只是我知道,有人將這種花研製花香膏,這東西有提神養氣之效,但常年吸食,上癮不說,毒心肺,便只剩一個死字。”
“所以?”
“這東西,我在皇后寢宮見過。”沉沉的說。
司蒼宇瞬間眸一凜,放在桌下的手僅僅攥住。
季莨萋臉也配合的嚴肅起來,“這就是我今日要與你說的事,皇后邊只怕有了旁人教唆,這種東西,說是對付皇后,實際上重傷的卻是你,若是皇后出事,到時候你的份再被揭出來,那死的是誰,我想不言而喻。”
“你到底想說什麼!”司蒼宇的心了,就算表面故作鎮定,眼神也能看出略微遲疑。
“我要的很簡單,不管用什麼方法,將杜信煒從宮中調走!”
“杜信煒?”他不可思議,“你說的中意的人,就是杜信煒?”
皺眉,“不是。”
“那你……”
Advertisement
“五皇子,若你接我的加盟,那我們便是夥伴,我的報,可以全部供你,但是同理,我的私事,請你不要過問,我與心月姐妹深,杜家不宜被牽扯進來……”頓了一下,看他滿臉不信嗎,季莨萋咬咬牙,“我中意的那人,杜信煒能聯繫到。”
這晚的對話一直著古怪,司蒼宇不知該不該信季莨萋,這個人何等機智,他從來不敢小看。
但是的主示好,來得太急太陡,讓他一時竟然手足無措,上的也太多,多的他判斷不明。
只是可以確定的是,他手裡的名冊是真的,而那朵罌粟花……
他明天會親自進宮,好好確定一番。
季莨萋回到季府後,小巧一邊伺候梳洗,一邊不贊同的說,“小姐,今晚這種事,以後可萬萬不能發生了,與男子半夜相會,這要是讓人知道了,那可是……”
“小巧,你越來越囉嗦了。”季莨萋沉沉的道。
小巧委屈的憋著脣,不說話了。
此時,窗外突然狂風大作,將窗戶扇得啪啪作響。
季莨萋走到窗前,推開窗戶。
頓時,一強風襲擊而來,夾雜著大雨侵襲而至。
季莨萋用手擋住風,小巧連忙將窗關上,抱怨道,“看來要下大雨了。小姐,早些睡吧。”
季莨萋盯著窗戶又看了一會兒,心中有種不祥的預。
下雨……
真是隻是下一場雨嗎?
吐了口氣,暗歎自己想多了,眉心,回到牀上休息。
可事實證明,的預沒有錯。
這場雨,從晚上下到第二天,足足下了五天五夜。
這是近幾年來,最大的一次風暴。
京都附近的不農田村莊,都了災害。
Advertisement
就連皇宮裡也無法倖免。
季莨萋在季府呆了五日,司蒼宇的消息沒有傳來,知道這點雨擋不住司蒼宇,他要調查的東西,不會停止,只是進度肯定會放慢。而這個男人在沒有充足的準備之前,是不會對的結盟提議,做出迴應的。
這五天,季莨萋每天都坐在窗前,看著淅淅瀝瀝的的大雨下個不停,總覺得自己忘了什麼,心裡有的地方空的,可每次即將想起來時,又怎麼也不不到。
是什麼?
是什麼呢?
突然,又是一陣電閃雷鳴,季莨萋驚了一下,仰頭就看到一片刺眼的白在眼中反。
心臟咚咚咚的跳個不停,不安的緒越來越重了。
靈竹躲著雨跑進走廊,就看到自家小姐正坐在窗前看雨。
嘩啦啦的大雨伴隨著強風,將窗臺前打的一片澆溼,卻置若罔聞一般,只盯著天空發呆。
“小姐?”靈竹跑過去,擔憂的看著小姐,這幾日小姐越來越不對勁了,每日不分早晚的這麼看雨,有時候半夜都要開著窗戶睡,私心是覺得小姐有什麼心事,可是小姐卻什麼都不肯說,空是擔心,也沒用啊。
“小姐,雨太大了,我們進去坐吧。”
季莨萋偏頭,看自己頭上都是溼漉漉的,不覺好笑,“去換服吧,我再坐坐。”
“可是小姐……”
“讓你去就去,乖。”
靈竹委屈的嘟嘟,還想說什麼,可看小姐又偏過頭去看雨了,滿腔話語都咽回了肚子,一步三回頭的出了房間。
五天的雨,不是極致,只是開始。
第六天,天晴了半天不到,晚上又開始狂雨大作。
然後接著,又是五天。
斷斷續續,整整一個月,這雨一直沒停乾淨過。
接著,朝堂中傳來不好的消息,先是洪水,接連幾個村鎮被淹,再是路上爲了支援泉國與晉國的戰爭,蜀國做出了態度,而趁著這次蜀國大水,晉國竟然派了兵馬,對蜀國南方邊境進行滋擾。
南方邊境不似北方那麼重兵把守,因爲那裡地勢險峻,羣山環繞,因此防守除了佔領高地外,兵馬並不太多,這次晉國趁著大雨,蜀國鬆懈之際,竟然繞到山谷之後,對大軍進行襲。
邊境軍馬打敗,皇上接到捷報,立刻派兵趕赴支援,但是因爲路途遙遠,加上中間不路被洪水淹沒,兵馬遲遲不能送往,如今每日我邊境戰士都在死傷。
而晉國因爲常年溼,雨水多,雨中作戰,幾乎小菜一碟,這卻苦了蜀國的戰士們,在那盡侮辱。
世人皆知,這晉國只是給蜀國一個下馬威,挑些邊關問題,也無外乎警告蜀國,莫要手別人的恩怨,畢竟他們這次純粹佔了天時地利的便宜,依照晉國的實力,本無法傷到蜀國本。
可是蜀國泱泱大國,又豈是他區區晉國可以威脅的?這次的矛盾,已經激化,看起來或許只是點小,但是蜀帝已然怒,若是沒有這該死的大雨,只怕援軍早已趕到,將那子叛軍,一網打盡。
分給朋友: 章節報錯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惜花芷
藏拙十五年,花芷原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穩一輩子,可當花家大廈將傾,她不得不展露鋒芒出麵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拋頭露臉是常態,打馬飛奔也常有,過不去了甚至帶著弟妹背著棺材以絕戶相逼,不好惹的名聲傳遍京城,她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她刀子的心理建設,也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獨獨沒想到會有人在出征前盔甲著身向她許終身!好稀奇,這世上竟然還有人敢娶她!?
132.4萬字8 211843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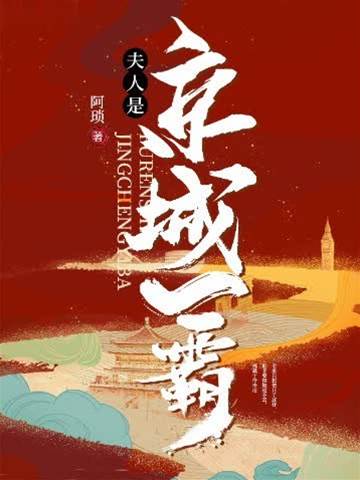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23 章

我不做妾
沈瀾穿成了揚州瘦馬。 雲鬢花顏,瑰逸絕倫,當得起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正因這份美貌,她要被送去給巡鹽御史裴慎做妾。 沈瀾不願意做妾,千辛萬苦逃了出去。 陰錯陽差,成了裴慎的丫鬟。 對丫鬟這份工作,沈瀾尚算滿意。 雖然全年無休007,但薪俸極高,常有外快。 更讓她滿意的是裴慎快要成親了。 只等裴慎成婚後,她便能銷去奴籍,靠着自己積攢的人脈、錢財,快快樂樂過完這輩子。 就在她滿心歡喜,只等放良之時,忽然發現,裴慎想納她爲妾。 沈瀾:我不做妾。 * 裴慎三年前就想納沈瀾爲妾,只是因爲守孝不得已忍了三年。 越隱忍,越剋制,想得到她的心思就越強烈。 如今三年已過,將要成親,正是納妾的好時候。 * 裴慎一生順風順水,官路亨通,遇到沈瀾,才知道世間唯情愛二字,最是摧心折肝。
39.9萬字8 74912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1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