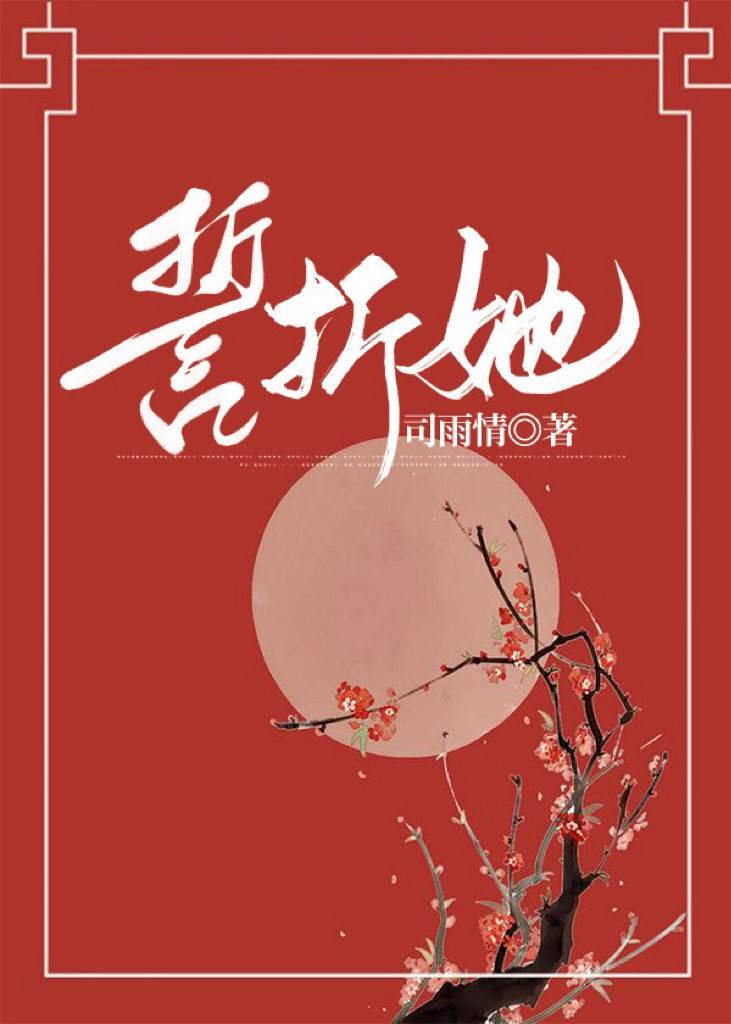《宮闈花》 第106章 認賊做父
蘇流螢決然的回絕讓在場的兩個男人都怔愣住了。
不等樓樾回過神來,眸冰冷的看向臉發白的他,冷冷下逐客令,“世子爺請回吧,我家公子方纔外出辛苦了,奴婢要伺候公子小憩一會。”
說罷,調轉頭聲的對韓鈺道:“公子累著了吧,奴婢伺候公子去休憩一會,晚膳時候奴婢再喚公子起牀。”
對韓鈺的態度異常的溫親,因爲韓鈺坐著子,與他說話時,都是俯低子在他耳邊輕聲細語的說著。
雖然知道是故意與別的男人親近氣走自己,但樓樾還是覺到蘇流螢對這位北鮮大皇子不同尋常的。並不是完全在做戲,而是真的有在。
之前在雲夢臺,給蕭墨做婢,那時的,總是不自由主的離他遠些,每每蕭墨向靠近半分,都會不自的往後面退步……
樓樾知道,在經歷了太多磨難波折後,蘇流螢心孤傲又自卑,更是對靠近的人帶著防備,就連對李修都是如此……
而如今與韓鈺在一起,一切都是那麼自然。主靠近他,一點不適的覺都沒有。他一個眼神一個細微的作瞬間就能明白。
而且從樓樾進來開始,竟是護犢般,寸步不離的守在韓鈺的邊。
這一發現,讓樓樾心裡更是心酸難,也生出了無盡的恐慌來,如臨大敵!
眼見蘇流螢推著韓鈺再次進間,樓樾再也忍不住衝上前去,攔在了主僕二人的面前。
如墨的深眸深不見底,樓樾忍住心裡的痠痛和高燒下的不適,咬牙向韓鈺拱手道:“大皇子請見諒,本世子與蘇流螢之間還有未了結之事。等事完結,本世子不會再來打擾!”
Advertisement
蘇流螢心口一窒——
他們之間,從他說下那些狠心話開始,從萬念俱灰跳下荷花池開始,一切皆已了結,還有什麼未了結之事?
韓鈺眸冷然的看著面前一臉悲痛的樓樾,想著他在戰場上大敗北鮮時的叱吒風雲,面對千萬大軍廝殺時的鎮定自若,而如今爲了一個子卻慌無措起來,心中不由想起了父皇訓斥自己的那些話。
帝王者,最忌諱重。
所以,他空有一的才華,卻沒有一顆做帝王的絕之心。
而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大庸最出衆的將帥,同樣如此……
收回心神,他回對蘇流螢聲勸道:“既然有未了之事,你就同世子爺好好說清楚罷……不要留下憾!”
蘇流螢瞭解樓樾的脾,更不想因爲自己與他之間的糾纏,讓他再來驛館打擾到韓鈺,所以就依韓鈺所言,隨樓樾來到了屋外的院子裡。
兩人來到院子裡的石桌面坐下。
短短幾日未見,二人皆是形容消瘦憔悴,而此時的樓樾更是全難至極,高燒下的子忽而如放在火焰上煎烤,炙熱難。忽而又彷彿掉進了冰窖裡,全冷得直打冷。
但爲了不讓蘇流螢發現他的異樣,他咬牙鎮定坐著,表面一點異樣都看不出來。
蘇流螢眸冷冷的從他鐵青的臉上劃過,轉而看向別,冷冷道:“世子爺有話就快說吧。”
神間的冷漠與疏離,讓樓樾心痛如絞,後背****一大半,傷口又開始在流。
然而,傷口的撕裂不是最痛,最痛的卻是他的心。
頭腦昏沉間,他差點就將那晚雲夢臺上發生的一切告訴給蘇流螢。
可是話到邊終是被他咬牙忍下。
Advertisement
從懷裡掏出蘇流螢退回去的木盒放到面前,樓樾著嗓子冷冷道:“本世子不收你的賀禮!”
不用看,蘇流螢都知道木盒裡裝著退回去的玉牌,心裡一痛,面上卻冷冷道:“這原本就是世子爺的東西,本就不屬於我,世子爺何必要將它強留在我邊——世子爺還是將它送給它真正的主人罷!”
說罷,手一推,將木盒再次被推到了樓樾面前。
看著絕然的樣子,樓樾心裡越發的慌失落,就像手裡握住的某樣東西正在悄悄的流失,不再屬於他……
蘇流螢又冷冷道:“若是因爲這玉牌之事,本無需爭執,我不會要,世子爺也不要因此事再來糾纏……”
說罷,再無留,留下樓樾,轉朝屋走去。
“這一塊……與四年前給你的那一塊本就是一對。人已分離,玉牌也要分開嗎——若你執意不要,就將兩塊一起還我!”
後,樓樾聲音冰冷刺骨,卻帶著難以察覺的落寞與傷痛無奈。
蘇流螢執意不肯要玉牌的態度,代表了要與他徹底劃清界線,一刀兩斷的決心!
可樓樾那裡是真的想放棄?!
可偏偏是他拋棄在先,是他愧對。
所以,在所有事真相大白之前,他怕忘記自己,那怕讓恨著自己,他也不願意忘記自己!
‘人已分離’四個字再次刺痛了蘇流螢的心,而他的話更是讓憤恨——
原來,他將玉牌退回,並不是要挽留的心意,卻是在向要將四年前的那塊玉牌一起討要回去,還其名曰是不讓玉牌分開!?
可是,四年前求親的那塊玉牌,明明在拒婚時就一併退回給他了,那裡還有什麼玉牌?!
Advertisement
回頭冷冷的看著臉蒼白的樓樾,蘇流螢語氣冰寒的嘲諷道:“四年前我明明拒婚不嫁給你,又怎麼會再留下你的玉牌?世子爺莫不是納妾歡喜過了頭,腦子糊塗了吧?!”
毫不遮掩的諷刺讓樓樾心口一窒,全如墜冰窖!
他相信沒有騙自己,可四年前他送到家府上求親的其他聘禮悉數退回,卻單單沒有那半塊玉牌。
一直以爲,他都以爲玉牌被留下了,所以纔會在出征前將自己剩下的一塊也給了。
但如今聽話裡的意思,那塊玉牌並不在手上?!
樓樾相信沒有騙自己,可爲了讓不徹底將自己從的心裡抹去,他卻顧不得這麼多了。
頭腦越發的昏沉,有幾次他站立不穩,只得藉著石桌靠著。
面上,他勾脣冷冷笑道:“四年前你們家確實退回了聘禮,卻單單了那塊玉牌。想來你們蘇家也是宦大家,也是識貨的,知道那玉牌價值不菲……本世子還是那句話,要還我玉牌可以,但必須是一對的。不然,只能當你欠了本世子的東西了!”
咬牙說完這些違心的話,樓樾的子搖搖墜,趁著蘇流螢被他這些話震驚住尚未回過神來之際,他逃也似的離開了院子。
再晚一步,他就要在面前倒下了……
看著他離開的影,蘇流螢全僵住,站在原地久久回不過神來。
無法想象這樣的話會從樓樾的裡說出來。
與他經歷波折走到現在,相信他對自己是有真的,那怕最後他背叛了自己,也明白,那不過是他在與樓家之間,選擇了樓家從而拋棄了罷了……
可如今聽到他說出這樣無恥的話,卻是讓徹底膽寒了。
Advertisement
難道,這纔是他樓樾的真面目嗎?
眼淚滾滾而下,蘇流螢寧願相信樓樾是因爲樓家拋棄自己,也不願意相信自己錯了一個不值得去的人……
裝著玉牌的木盒被樓樾留在了石桌上,蘇流螢呆呆站立好久,終是艱難的走過去,手指抖的打開盒蓋,看著裡面的玉牌,心裡苦如,同時也涌上了疑——
如果那塊玉牌真的如樓樾所說,並沒有退回安王府,那玉牌去了哪裡?
頹廢的在石桌前坐下,經過方纔與樓樾之間的糾纏,蘇流螢傷痕累累的心再次被勾起傷痛,而想著不知下落的玉牌,更是陷迷茫的痛苦中……
屋,韓鈺坐在窗前默默的看著院子裡的蘇流螢,眸沒有掉臉上一的神,看著神間的落寞傷痛,他明白,的心裡並不如表面那樣真正放下樓樾,的心裡還有他……
眸暗下去,韓鈺心裡同樣苦起來,等看到蘇流螢重新進屋,他恢復以往的淡然模樣,關切問道:“與世子爺淡得怎麼樣了?”
事到如今,蘇流螢並不想再瞞他,於是將玉牌之事同他說了出來。
聽說完,韓鈺卻是明白了樓樾真正的心思,微微擰眉道:“玉牌之事世子爺應該不會假意騙你,可能當初在還聘禮的過程中出現差錯,不小心弄丟了……”
“你不用擔心,此玉牌非同尋常,若是有人拾到,要麼珍藏,要麼會拿去典當,我們沿著這兩條線索細細尋找,應該可以找到。”
“等你將兩塊玉牌拼齊全了,到時再還給世子爺,想必他也無話可說了。”
聽了韓鈺的話後,蘇流螢心裡釋懷不,決定如韓鈺所說,找出玉牌,再徹底與樓樾一刀兩斷……
而拼著最後一口力氣走出院子的樓樾,終是子抵抗不住的往地上倒去。
可就是他子堪堪要摔下去之時,斜刺裡卻是出一隻手來穩穩的扶住了他。
回頭看去,扶他之人竟是胡狄太子蕭墨。
眸涼涼的看著他,蕭墨勾脣冷冷笑道:“看來蘇流螢了別人的人,讓世子爺很傷啊。”
雖然蕭墨已呆在大庸大半年的景,但樓樾與他之間的集之又,更不曾深聊,平時那怕遇見,彼此卻是連最基本的招呼都不打的。
而兩人之間,彼此間的敵意,更是各自心知肚明。
如今自己狼狽的樣子被蕭墨看到,樓樾心裡生出惱意,不由甩開他的手,自己靠著牆壁緩著氣,冷冷道:“堂堂胡狄國的太子爺,留在大庸不走,竟無聊到開始管別人的兒長了。不知道的,還以爲你是被胡狄王趕出胡狄無家可歸了。”
從樓樾裡聽到‘胡狄王’三個字,一臉輕浮懶散看好戲的蕭墨卻是變了臉。
他眸冰冷的看著臉蒼白、直冒冷汗的樓樾,咬牙恨聲道:“本太子再怎麼樣,也比某些認賊做父的人強。”
他氣得拂袖離開,眸在看到樓樾後的圍牆時,腳步卻滯住了。
樓樾因後背傷口裂開,鮮淋漓。但他上穿著玄裳,一時間竟看不出來。
但他方纔靠在圍牆上,如今,他靠過的地方卻是浸上了一層鮮紅的。
看著他面容間強忍的痛苦,蕭墨眸裡閃過一意味不明的亮,神間更是猶豫遲疑,下一刻卻是拉過他的右手臂搭上自己的肩膀,將他扶進自己的院子。
樓樾已被高燒頭腦昏沉,再加上失過多,人已是半昏迷狀態。
恍惚間,他以爲蕭墨是要將他扶進韓鈺的院子,心裡越發的慌起來——
他可以讓蘇流螢恨自己,卻不想讓看到自己如今狼狽的樣子……
咬牙抑住上冒出的陣陣寒意,樓樾再次去甩開蕭墨的手,冷聲道:“滾,本世子不需要你的幫助!”
他雖然病得利害,可掙扎起來力道還是不容小覷。
蕭墨同樣黑了臉,臉上出不耐煩的神,反手一記手刀重重砍在樓樾的後頸上,徹底將他砍暈過去。
修羅見蕭墨扶著樓樾進屋來,嚇了一大跳,下一刻卻是嫵歡喜的笑了,“殿下將他解決了?!”
蕭墨將樓樾扔在屋裡的玉榻上,黑著臉冷冷道:“去幫他請個大夫。還有,去驛館門口將他的隨從進來。”
修羅一臉不可思議的看向蕭墨,“殿下竟是要救他?不是應該趁機殺了他麼?!”
猜你喜歡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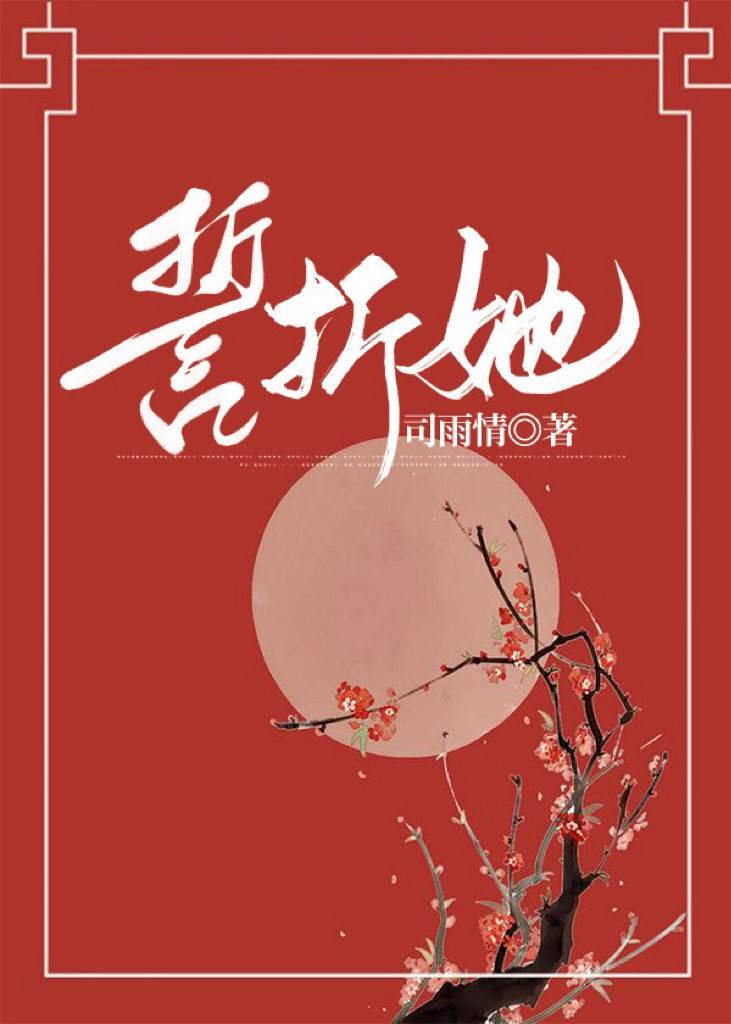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7033 -
完結485 章

重生迷死九皇叔
前世,她嫁給心上人,助他登上帝位,貴為皇后卻慘遭摯友背叛,親人死絕! 她悲憤而亡,化作一縷幽魂,卻看見桀驁冷酷的九皇叔闖入皇宮,一腳踹飛了帝王。 他替她復仇,替她守護江山,卻終身未娶,無后而終。 重活一世,她撕毀婚約,踹飛渣男,飛撲進九皇叔的懷里撒嬌。 所有人都認為她配不上九皇叔,殊不知,他在見她第一眼時,便已淪陷…… 她說:“皇叔,我想當皇后。” 他寵:“好,那本王明日便去登基。” 她說:“皇叔,我想要個兒子。” 他欺身而上:“一個哪夠?”
89.2萬字8 62924 -
完結188 章

折幽香
季枝遙從出生起便是個不起眼的草芥,誰都能來踩她一腳。不起眼到前朝覆滅,宮人落荒而逃時也不帶她。聽留下的宮婢說,新帝陰鷙殘暴,只在宮中待了一夜,苑中侍從便無人生還,全部慘死。她徇徇度日,如履如臨,卻還是沒逃過被抓去太極宮當侍女。*日子過得慌亂,新朝建立不過數月便再度岌岌可危,季枝遙不得不跟著他離開皇宮,過上隱姓埋名的生活。一日,地痞流氓趁她不備沖進院中,一群人生拉硬拽要將人搶走。她雖學了些繡花拳腳,卻敵不過人多勢眾。絕望之際,院門被人從外推開,一陣冷風卷入,吹至宮殿的各個角落。禁衛將偌大的庭院封鎖,截斷任何能逃跑的通道。那群人眼見身著墨色蟒袍的男人不疾不徐走到她身前,丟下一柄長劍。嘭一聲落地,滿院的人嚇得直接跪地,瑟瑟發抖地看著那塊標致至尊之位的令牌。可季枝遙卻不知道他會做什麼,昨夜他們大吵一架不歡而散,想來他很樂意置自己于死地。然而死寂須臾,所有人都在等下一步,卻只見他蹲下與兩眼微紅的人平視,語聲溫和,拉過她的手,讓她握緊劍柄。“孤今日教你殺人。”——他給她榮華富貴,給她身份地位,可寫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出逃的三月后,他卸下偽裝,突然出現在自己面前,無論如何都要將人強行帶回上京。意識到這一點后,季枝遙雙眼空洞又絕望,一柄長簪毫不猶豫指向了自己的喉嚨。當看到眼前男人滿面慌張,變得毫無底線時,她就知道自己賭對了。這條命,就是她能和他叫板的、最簡單的東西。
28.5萬字8.18 26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