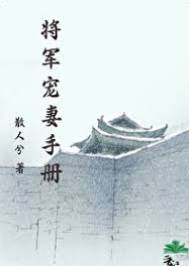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重生成了反派的掌中嬌》 第383章 不讓進?打進去!
可就在氣到快炸的時候,卻聽靳無殤道:“原來如此,郁掌門可是天佛門的掌門,
怎會沒有請柬呢,想必是忘了吧,
宗門大比在即,事鬧的太難看了也不好,
能否給家父和我一個薄面,讓他們先進去,至于請柬,找大管家補一個不就行了嗎?”
所謂宗門大比,顧名思義便是玄門百家之間的比賽,
自然也只會給每個宗門發一張請柬,
每個宗門抵達不夜城之前將赴不夜城的人數確定好,守衛只要核對請柬與人數便可,
往屆宗門大比也不是沒有人丟了請柬,先進城再補請柬,也無甚不可,
可這次,那守衛聽到后卻面為難,
請柬是他自己撕掉的,若是去找大管家補辦,問起請柬是如何丟的,豈不是連他都要代出去,
而且,他已經將這些人得罪死了,若是讓他們進了城,萬一要是進了不夜幻境,到時候得了勢,豈不是還要與他為難?
而就在守衛滿肚子計較之時,溫婉也冷聲道:“靳主年紀不大,耳朵卻是不怎麼靈敏了,
我這師姐方才說了,是這人為了拍藥王宮主的馬屁,撕了我們的請柬,
而不是我們弄丟了請柬,從始至終,錯在他,而不是在我們。”
“溫師妹?!”
靳無殤了溫婉一聲,語氣中略帶不滿。
溫婉忙后退一步,“靳主別,我可是你睥睨峰的叛徒,
若非這件事,楚晟銘那小人就算想刁難我們,還得想辦法找個借口呢,
你們既然把現的借口送給人家了,就請堅定立場,別搖擺不定的,到時候兩邊不討好就不好了!”
話語里的諷刺幾乎要化作實質,
靳無殤卻無從辯解,從他沒有阻攔父親和二長老污蔑謝淵渟與溫婉為師門叛徒,
Advertisement
以求自保之時,他就料定會有這麼一天,
因為他知道,謝淵渟和溫婉都是眼里不得沙子的人,只是沒想到,這一天會來的這麼快,
而又如此的猝不及防。
靳無殤從未被人如此當面嘲諷過,一時難堪又愧疚,慚愧道:“溫師妹,我知道是我們……”“好了無殤。”
靳無殤的話被靳北堂打斷,“既然有人自甘墮落,你就別白費心思了,人家也不領,
我們該走了,去晚了失儀。”
靳北堂話說完就走,靳無殤本沒有反駁的機會,
為難的看了看父親,又看看溫婉,終是咬牙跟了上去。
那守衛見狀,更為得意了,唾沫星子幾乎要濺到溫婉臉上,
得意洋洋道:“請吧各位,再耗下去,大家面上都不好看,我還……”
守衛說著說著,忽然“哎喲”一聲痛呼出聲,原是被一塊大石頭砸到了臉上,
接著,悉的聲音罵罵咧咧的響起來,“閉吧你!
捧高踩低的小人!我讓你說,我讓你說說說說……”
只見一青的靳無不知道從哪兒拎了塊石頭,對著守衛一通砸,
刷刷的作配合著噼里啪啦的罵,給那守衛打的暈頭轉向,
其他守衛們都呆住了!
那守衛胡掙扎著過氣兒來,忙扯著嗓子吼了一句,“還愣著干什麼,把給我抓起來,抓起來!
那些守衛們這才后知后覺的提劍向靳無沖過去,
溫婉愣了片刻,當即提劍沖了上去,一,謝淵渟和元英自然也不能干看著,
般若小姑娘早就忍不住了,跑的比元英這個護衛還快,
一時間不夜城門口了菜市場,打的人仰馬翻的,連后面來的宗門參賽人員都被攔在了外面。
Advertisement
也不知道是商量好了還是心有靈犀,打起來的時候眾人對不夜城的守衛都沒有下死手,
唯獨那個挑事的守衛了眾人的火力中心,
你一拳我一腳,這個還用劍背拍一下,那人在人群中顛來倒去,連運氣保護自己的機會都沒有,
整個人被打的慘不忍睹,塌塌的趴在地上爬不起來,溫婉和靳無、般若三個小姑娘才放過他,
轉就見謝淵渟和元英、元嘉以及幾個天佛門弟子正圍著楚晟銘拳打腳踢,
有幾個藥王宮弟子想上前救人,被紅衫和郁掌門不聲的攔在戰斗圈外,本沖不進來。
“住手!”
隨著一聲高喝,不夜城的守衛們先停了手,溫婉幾個趁機又踹了那守衛兩腳,然后一臉乖巧的站在原地,
來人是一位看上去四十來歲的中年男子,冷冷越過圍觀的人群,徑直走向郁掌門,
可就在他看到謝淵渟的一瞬間,像是被嚇到了一般,整個人都僵住了,
謝淵渟不喜這般無禮的直視,不喜的皺了皺眉,
那人見狀,也回了神,轉而對著郁掌門的方向抱拳道:“不知郁掌門和紅衫圣手大駕臨,有失遠迎!
下面的人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二位貴客,還請二位多多海涵哪!”
出乎意料的,他對郁掌門和紅衫圣手的態度客氣極了,
聽那說辭,顯然是早就知道了守衛所為,一上來就道歉,
郁掌門和紅衫也不好發作,后者只是略帶諷刺的道:“不夜城的門檻這些年真是越來越高了,
這不,今日連這城門都進不去,
若非城主夫人的親筆信還在懷里揣著,我都要以為今兒個我不是城主夫人相邀而來,
而是自己厚著臉皮倒來了!”
Advertisement
“圣手可真是折煞我了!”
那人汗道:“下面的人有眼不識泰山,怠慢了二位,
我這就嚴懲。”
說完,直接道:“來人,把他給我拖下去,廢去修為,送到白云山與反思,
其他人,先迎客人進門,
夜崗后自己去暗堂領一百杖,
安淮,你親自盯著,輕打打,全算在你上!”
“是,二爺!”
后一勁裝的黑青年沉聲應下。
守衛們驚呆了,完全不明白威風堂堂的二爺為何要對兩個外域來的人如此客氣,
那故意撕掉請帖的守衛則驚慌道:“二爺饒命啊!
小的不是故意的,是楚主他故意暗示小的,小的才會犯下如此大錯,
二爺饒命啊!”
任他再怎麼求饒,被稱為二爺的人連眉頭都沒眨一下,直接揮手讓隨從將其押了下去。
凄慘的求饒聲中,被稱為二爺的人笑著道:“如此理,二位不知可還滿意?”
“二爺事就是痛快。”
郁掌門微微頷首,“不過有一點那個守衛沒撒謊,
若非有人故意播弄是非,區區一個守衛還不敢撕本座的請柬。”
一旁的楚晟銘被謝淵渟幾人摁著打,二爺來的時候快哭了,
聽到這話,莫名有些心虛。
二爺抬頭瞥了一眼楚晟銘的方向,不不慢道:“郁掌門請放心,關于這件事,我會和楚宮主好好聊聊。”
郁掌門畢竟是一宗之主,和楚晟銘這種小孩子一般見識,且安二爺言出必行,
又是在別的地盤上,郁掌門找回了場子,也不鬧的太僵了,
便點點頭,道:“二爺辦事,本座自是放心的,家里小孩子沉不住氣,讓二爺見笑了。”
“郁掌門說的哪里的話?”
二爺連連搖頭,面帶欣賞的道:“不瞞您說,我來了有一會兒了,
Advertisement
您這幾位高徒可真是各個都不一般啊!
尤其是這幾位,看著年紀不大,一個個實力不可小覷啊!
實力等級嚇人也就罷了,外功還都湛非常,毫不夸張的說,就方才那幾下,是近幾十年,我看過最彩的外功了!
只是這幾位小友看著有些面生,是郁掌門又收高徒了嗎?”
“是門中新弟子不錯,不過,我可當不起他們的師父。”
郁掌門搖著扇子不聲的轉移話題,“先進去吧,晚了,城主大人該訓你了。”
不夜城,雖然名字上帶了一個城字,可絕不是簡單的一座城池,
溫婉他們跟著二爺坐上不夜城專門用來迎接客人的角馬車,
四馬并駕的馬車可容十幾人共乘,走在寬闊的街道上,仿若一幢移的小房子,
饒是富可敵國的溫婉,也未見過這般豪華的座駕,
不是沒錢,而是曾經的三國一部本沒有如此寬敞的道路供這種車行駛。
城主府更是修建的恢弘大氣,比之天玄皇宮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只是金和白完結合的宮殿比金碧輝煌的皇宮了一些世俗的奢華,
多了一些令人神往的尊貴大氣。
幾人的馬車一路駛城主府,了門,眾人下車,門口的下人忙迎過來,恭恭敬敬道:“二爺!”
安二爺應該是早就習慣了這樣的場面,并不理會下人,
而是對郁掌門和紅衫道:“今日府中瑣事諸多,我實在是不開,
您二位先帶著孩子們到客院里稍事休息,
晚一點,我一定自罰三杯,向兩位請罪。”
“二爺客氣,這不夜城我們又不是第一次來了,您請便。”
紅衫亦是頷首附和,
二爺便歉聲道:“多謝二位海涵,那我就先失陪了!安虎,帶幾位客人去花廳休息,
郁掌門和圣手都喜靜,安排客房要仔細了!”
說是要失陪,又叮囑了許多,才轉離去。
正是一年好時,滿庭花香令人心曠神怡,
眾人跟著安虎的黑青年走了沒多久,就聞到陣陣馥郁芬芳,
伴隨著喧鬧聲傳到院墻外,想來,玄門百家許多人都已經到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59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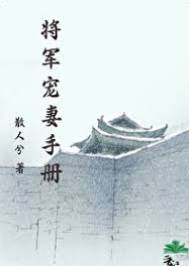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12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