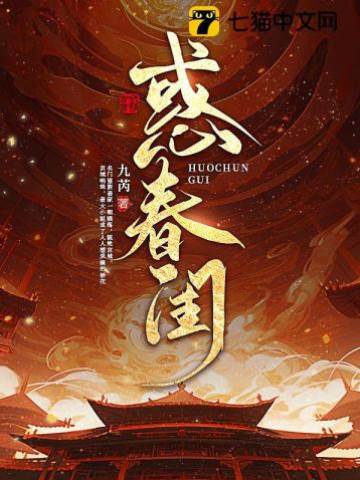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舊時燕飛帝王家》 第196頁
樂平的確遇到了一個妙人兒。在在運河游玩的最后幾日,在夜闌珊里遇到了一個chuī奏地笛子的樂師,那樣的白男子立在船頭,被溫潤的燈籠罩著,簡直第一眼便迷醉了樂平公主。
當下便是將這樂師一同帶回了京城,竟是連府外那面首府都舍不得放,地帶回到了宮里。
也不知道飛燕為何有此一問,當然是不能說出自己獵艷的荒誕,便只說自己游船,無非是看些歌舞,并沒有遇到什麼特殊的人。
飛燕的眼卻是異常犀利,只命人拿來早前通緝宣鳴時的畫像問道:“公主可是遇到了這個人?”
說實在的,那畫像雖畫得jīng細,卻是難以畫出宣鳴一半的貌。所以那樂平雖然早前也看過宣鳴的畫像,可是見了真人時卻從未將他與當年在飛燕那看到畫像聯系到一。
可是現在被飛燕刻意的這麼一問,才猛然醒悟,這的確是同一人,當下心便是有些忐忑,不知這畫中人犯了何事,竟是讓一向從容的皇后變了臉。
飛燕看了樂平的神就知在撒謊,當下便是一針見地指出樂平上的那熏香味道,簡直是跟當年太子呈現給先帝的編鐘樂隊,奏樂時點燃的沉香一個味道,此香有迷人心之功效,飛燕向來對這蠱的迷香就敏,所以當樂平刻意親近靠將過來時,一下子便嗅聞出了這味道。
當飛燕道出原委后,樂平也驟然變了臉,終于是期期艾艾地說道:“只是遇到了個chuī笛子的樂師,看著他chuī奏得不錯,便帶回了京城……”
飛燕站起問道:“他現在在何?”
樂平只覺得自己已經是yù哭無淚,直覺自己又是闖下了大火,哭喪著臉到:“他現在暫居在宮中的耳院……”
Advertisement
宮中的耳院是沈太后在世時,經常為唱戲解悶的戲子們暫居之所,雖然是在宮中卻自一院,若是想聽戲了,只需有太監引領這穿過一條宮街,便來到太后的宮中了。
而太后的宮苑又是離觀月宮并不甚遠……糟了!飛燕的心中只有這一個念頭,當下便是命人調撥侍衛兵分兩路,一部分趕往耳院拿人,一部分前往觀月宮嚴防。
可惜到底是晚了一步,等到觀月宮,外院雖然有侍衛站崗,可是院里的侍嬤嬤們卻是東倒西歪迷暈了一大片。而服下了安神藥,本該在chuáng榻上休息的安慶公主卻是不見了蹤影。
最要命的是,那樂平的管事太監發現,自己隨的出宮門的腰牌也不見了……
安慶服下藥后,便因著藥xing昏昏沉沉的睡去,可是夢里依舊是不安穩,許多的影像抑不住地噴涌了上來,一會是湖中的怪shòu襲,一會是是個中年子坐在花團錦簇的后花園摟著笑著“安慶”,一會又是那個曾經驚嚇到的皇帝,一輕便的獵裝帶著騎馬she箭,而則開心地催著小馬,不住地喊著:“二哥,等等我……”
夢境到了后來,便是兩個鄙的大漢,狠狠地住了的雙頰,不住地往的口里灌藥,那藥的味道奇苦,是生平嘗過最難吃的東西……
看著那兩個的大漢一臉的獰笑,安慶呼吸變得局促,拼命地搖頭低喊著:“不……放開我,放開我……”
終于猛地一睜開眼時,卻發現自己被一人攬在懷里,下一顛一顛的正騎在馬背之上。
微微抬頭一看,用披風包裹住自己的,正是晉王宣鳴。
Advertisement
微微的出聲著“晉王”,卻發現自己嗓子都因為方才在夢里的嘶喊而有些嘶啞了。而臉上也是一片的意。
此時已經離得京城老遠,宣鳴卻不肯停下馬匹,直到來到碼頭,起錨開船后,他才終于正視萱糙,里淡淡地說道:“你想起來了?”
他利用了樂平宮以后,便裝扮著太監利用腰牌出了耳院,稍微打探后,一路潛行了觀月宮,迷暈了眾人后,將昏睡的安慶打扮了小太監,略略地涂抹了些藥,出些紅斑,便裝了生了麻風病的小太監,在宮里的下役房的眼線幫助下,從宮中專門運送老病而死的宮人的偏門出了宮來。
這一路來,安慶囈語不斷,他聽得分明,不過心也是放下了一件——這個孩到底是失憶的,并沒有存心開誆騙于他。
安慶睜開眼便見到了這幾日來日思夜想的宣鳴,可是夢境與現實不停的沖撞著混的腦子,這一時間竟然不知該是如何面對宣鳴,若是夢中的種種只是夢,那該是多麼好……這麼一想,眼淚又是止不住地流了出來。
宣鳴此時解了外衫,只著里面的單,長發從解開的發冠里披散了下來,微微遮住了冰冷的眉眼,坐在船艙里厚厚的絨墊之上,慢慢地開口道:“該是如何稱呼你,我的小公主?
打從來到了宣鳴的邊,安慶從來沒有見過宣鳴這般冷漠,甚至是帶有仇視的目看著自己,一時間,心竟然是像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般,難得很,直覺慣xing地想要靠在宣鳴的手臂上哭一哭。可是卻是被宣鳴一推,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這下子,安慶再也是承不住,便是哽咽出了聲音,再次地向宣鳴的邊爬去,宣鳴不肯給胳膊抱,那便gān脆扯住了宣鳴的角,蓋住了自己的小臉,聳著肩膀哭個痛快,不一會,宣鳴冷眼在一旁看著,只見邊哭便慢慢地又朝著自己這邊挪了過來,冷著心腸手再推,眼看著又應聲倒下,那哭聲驟然變大了許多,嗓子都變了音兒。
Advertisement
宣鳴慢慢地出手,想要安下趴在地上痛哭的水娃娃,可是手了一半,便qiáng自又收了回去。他拼命地提醒著,是那個惡毒人的兒,大齊霍家的公主,萬萬是心不得的。
于是出的手便再次慢慢地握了,只是不急不緩地在一旁小桌上拿起了小食盒,取了些酸梅曬gān碾磨打碎的梅,又放了一竹勺的冰糖,再用熱水沖泡,然后便將茶杯放在了小桌三。
安慶哭得一時口gān舌燥,終于起了,看見了那冒熱氣的茶杯,便又爬過去,小口喝了一下,溫度正好,便一飲而盡,那酸甜的滋味倒是平復了不委屈的心qíng。
知道這是晉王特意為自己沖泡的,這樣酸酸甜甜的飲品,他是向來不的,一時間碎裂的心又是有了些藉。
咬了咬,小聲道:“晉王想必是心厭棄了我的,為何還要將我從宮里帶出來?”
宣鳴看著安慶哭紅了的大眼,神冰冷地說道:“既然你是霍家的兒,自然是用你來要挾霍尊霆了,想想看,該是如何用你來rǔ一番霍家?賣秦淮jì戶當是不錯的選擇,讓天下之士盡嘗皇家金枝玉葉的滋味……”
宣鳴此言,自然是有些恫嚇的意思,并不會這般去對待,畢竟也是自己養出來的,就算是利用報復,也不會如此下作。只是本以為聽了這話,安慶一定又要狠狠地痛哭一番,可是誰承想,卻是陡然止住了眼淚,只是愣愣地跪坐著。
半響過后,才慢慢地低語道:“晉王對霍家之恨,萱糙是最明了的,可是安慶對自己兄長的敬,卻是萱糙不知道的,上天給萱糙與安慶出了一道難解的題目,可惜這題目就是天下最聰慧的頭腦也是解不開來的,這可是如何是好?”
Advertisement
慢慢地抬起頭來,著宣鳴俊卻冷意十足的臉,略帶哽咽地說道:“在京郊的宅子里,有我親手種下的金jú花,剛剛發了芽,花開時一定很,原想著待到秋天時,曬gān了給晉王泡茶之用,味道一定甚……剛剛生了崽的狗兒土豆有些虛弱,也不知這幾日怎麼樣了,晉王一定要給它和寶寶找個心腸好的人家寄養……萱糙有太多的放不下,可是……最舍不得的是晉王您,您年歲這麼大了,還沒有娶媳婦,以前萱糙不晉王親,因為您若有了媳婦,便親近不得您了,可是現在,盼著你親,起碼有人在您邊接著照顧您了……一切……保重……”
說到這里,萱糙突然起,朝著船艙外奔去,生平最最怕水的,義無反顧地跳進了凌冰冷的江水里。的腦子愚鈍,生平的好就是吃吃喝喝,那樣的一道難題擺在的面前,竟是怎麼解都解不開的。一邊是自己敬的哥哥,一邊是這幾年來一直陪在自己邊的晉王,在的心里,這倆人都是一樣的重量,既然是解不開的,放不下,離不得的,唯有一死才能各自全了。
這樣的話,皇帝哥哥也不會因著自己的緣故而折損了皇家的威儀,而晉王若是肯看在自己一死的qíng分上,減了對霍家的仇恨,活得舒心暢快些,那麼死得其所!
冰冷的水一下子倒灌進了的口鼻之中,萱糙停止了掙扎,任憑著自己的子漸往下沉去……
第201章被擒
就在窒息的渾然不知中,只覺得下墜的猛地被一力量拉拽了起來。等到劇烈地咳出水來時,才發現晉王渾漉,臉鐵青地跪在的旁著的前,看到醒了,便將抱了起來,移了船艙,只是只是地抱著……待得安慶的也漸漸恢復了知覺時,才發覺貌似面沉穩的男子實際上抖得甚是厲害。
安慶的眼淚又是盈滿了眼眶,方才也是因著年,一時被晉王的話語兌到了死胡同里,只覺得只有一死才是解決諸多麻煩。可是此刻當靠近的抖傳遞過來時,才覺得一陣后悔。
曾經在一年前的月夜,他與在西域異鄉看著明月,趁著酒勁,他講述了一個關于前朝宮苑的令人惋惜的故事,知道那故事里的主人公便是晉王宣鳴。
那個他心的子,便是被大齊的皇后沉深潭活活淹死的。這是他的心結,而自己跳水之舉卻是又勾起了他的傷心往事,這麼想來,不懂事的自己真是死不足惜……
這一時間,便是從這個死胡同又一路馳騁去了另一牛犄角,愈加的悲切,可是卻再也哭不出眼淚,只是瑟瑟發抖地了一團。
這幾日心海的起伏澎湃,恨的攀附回繞也是晉王躲不開,避不得的。他的xingqíng寡淡,素來不喜外自己的喜怒哀樂。卻偏偏一不下心跌進了暗藏著無盡尖刀利刃的qíng網之中。他可以在談笑之間謀算著千百條人命,冷地看著他人死在自己的眼前。可是方才這素來香懦弱的小丫頭,竟是在他眼前膽橫生地跳了江中。有那麼一刻,他不知該是如何反應,心中竟是想著,若是這麼的死了,一切倒是都簡單了,可是就在這麼想時,他又聯想到了平時日日相見的那張巧笑嫣然的俏皮小臉被水浸泡得浮腫的樣子……只是想一想罷了,竟是忍不住一陣的gān嘔,接著便是莫名的刺痛襲向心頭,子竟是像被水中的一莫名的力量拉拽住一般,一頭扎進了水中……
猜你喜歡
-
完結906 章
攝政王是病嬌,要寵著
【重生+甜寵+虐渣+爽文,男女主1v1】身為丞相府千金嫡女的南曦,上輩子腦子被門夾了,喜歡上那個徒有其表卻滿肚子陰毒詭計的渣男,落了個眾叛親離淒慘死於渣男賤女之手的下場。重活一世,她智商上線,看著身邊這個權勢滔天,容顏俊美的攝政王,忍不住再次懷疑自己的眼光,攝政王殿下要顏有顏,要權有權,還對她千依百順,她怎麼就眼瞎放著珍珠選了魚目?隻是這位攝政王殿下時不時地心疾發作,是要鬨哪樣?攝政王是病嬌,要寵著
147.7萬字8 33340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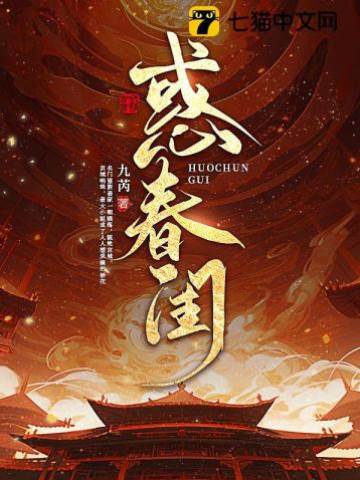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