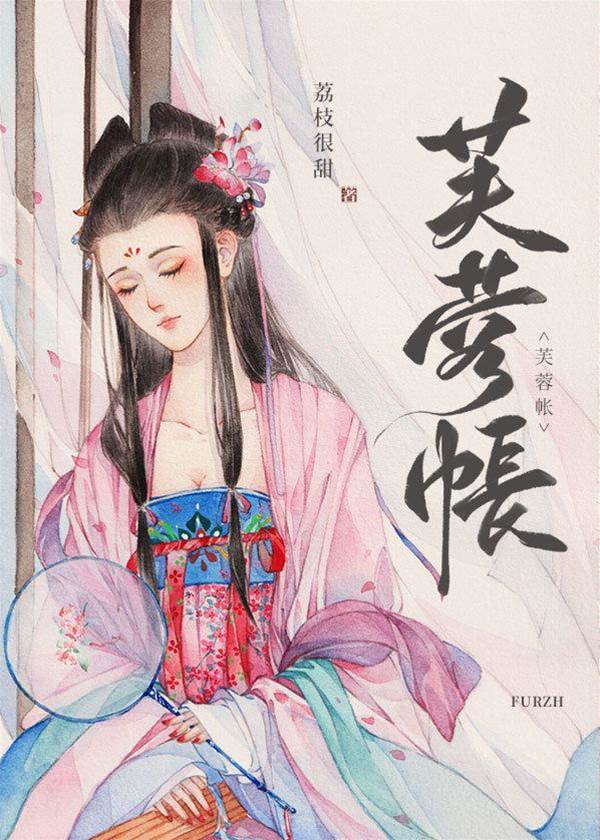《我是奸相他哥遺孀(重生)》 第12頁
青年眸定定,手里躺著的赫然就是那玉簪。
馮玉貞莫名有些難以啟齒,手腳不安。
即使崔凈空只字未提,卻像是被他用一雙烏黑沉冷的眼睛,從頭到尾目睹了獨屬和崔澤兩人的親。
“哪兒找著的?”
“桌子底下。”
裝作無事點點頭,掩飾地往后攏了攏碎發,耳垂發燙。
屋檐下的臘不見蹤影,大抵是被什麼鷹鳥或者狐貍叼走了。礙于容量有限,他們只能把近期急用的東西打包帶走。
馮玉貞在上門的那刻生出猶豫,無論怎麼看,山里的屋子似乎都明顯要比村西那個破磚房好太多,可仔細一想,也有不小的患。
譬如崔澤在時,每晚都要在屋前生火,每月擱四五天就繞著墻澆雄黃酒、燒艾草以驅散蚊蟲走,半夜偶有風吹草低便驚醒,起查看。
但是現在只剩馮玉貞一個人了。既沒有靠山吃飽的生存能力,也缺乏獨自過活的勇氣。
寡婦門前是非多,目前也只有依附小叔子才能得到一條可能的生路。
兩個人一人一個包裹,趁著時候早趕下山。可中午還炙熱火烤似的慢慢去威力,抬頭卻見飄來一團厚重的烏云。
Advertisement
氣漸重,馮玉貞的跛腳因此作痛,但是和崔凈空兩個人都沒有停下的意思。
才剛剛走到中途,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眼下真正陷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天沉,山林間樹木枝條搖曳擺,冬日的枯黃葉子簌簌掉落,吹到兩人的發頂和臉上。
起風了,風勢很大,這場雨來勢洶洶。
馮玉貞口劇疼,崔凈空原本還和并肩,見越發吃力,就走到前面領著。
初春的風倒不至于凍得跟拿刀子割似的,但一冷風徑直鉆進灌肺里,刮過五臟六腑,一口氣沒有勻,不得不停下腳步。
崔凈空仰頭,只見烏云如同披著漆黑甲胄的大軍境,云層最低點幾乎要把遠的山尖垮。電閃爍,沉悶的轟隆聲開,似有雷公躲在云里擂鼓。
他果斷地下了結論:“不能再走了,我們找個地方避雨。”
崔凈空向捂著口的馮玉貞,“還能走嗎?”
馮玉貞白著臉點了點頭,崔凈空換了方向,兩人快步朝西邊行進。天抑,他們速度也愈來愈快。
可跛腳經不住這樣疾走,踩在松的泥土上沒立穩支住,失去重心,子朝一側徑直摔下,左腳踝重重一折,骨骼發出清脆的錯位聲,再也站不起來。
Advertisement
恰在此時,昏黑的天際渲染下,醞釀許久的大雨終于傾盆而下,猶如集的雨幕,黃豆大的雨珠落在葉面上彈起迸濺。
崔凈空扭頭的功夫,寡嫂半倒在地上,額發微,左綿的狼狽態就映眼底。
關鍵時刻,他像一頭形矯健的豹子,回蹲下,展臂攬過的腰肢和彎。
不顧下意識的驚呼和反抗,把人輕輕松松地抱在懷里,一套作行云流水,抱著長立刻跑起來。
馮玉貞窩在青年懷里,顯得人很小一團,雙手撐在他膛上,很努力的想要拉開些距離——因為太燙了。
不管是噴灑在耳側的氣息、還是牢牢摟著自己腰和的手,哪怕隔著厚厚的,都覺得過分燙了。
憾的是,所做的努力全作廢了。因為左腳踝疼痛難忍,像是小刀進骨頭里旋轉。
疼得沒有多余的力氣,只得無力地全然倚靠著他。耳朵在對方口,因為跑而砰砰加快的心跳聲傳鼓,一聲比一聲鼓噪。
崔凈空速度明顯提高不,淋雨跑了沒幾步,山出現在視野里,順利躲進去后,他把人放下來,上才追了一句“冒犯了”。
Advertisement
這時候說冒犯還有什麼用?抱都抱了……
何況對方本意是幫,要是把撂在外面不管也不是干不出來,恐怕現在還算干爽的自己早了流落野外的落湯,哪里還有理由蹬鼻子上臉埋怨他。
實際也已經沒那個力去應對了。
馮玉貞靠坐在凸起不平的石壁旁,屈抱住傷,額頭上冒出麻麻的冷汗,白的可怕。
見這副難至極的模樣,崔凈空往下一瞟,人的小呈現怪異的弧度,應該是方才摔倒時崴了。
湊近低下頭:“我看看。”
“不……”
心里陡然一,馮玉貞從牙里出一個字,人家的腳怎麼能隨便給別人看?他又不是懂醫會正骨的大夫。
“我是要為嫂嫂正骨,絕無什麼旁的心思。”
轟——
馮玉貞睜大了眼睛,幾乎生了幾分惱。
,什麼時候懷疑崔凈空這些有的沒的了!
單從禮法上說,自己都是崔凈他的長嫂,民間自古就有長嫂如母的說法。
即使只比他大了兩歲,也是對方不折不扣的長輩,怎麼就沒頭沒尾繞到這個上面來了。
可他氣勢冷峻,眼神沉著,一本正經的模樣很有些說服力,好像心里半點雜念都沒有。
目復雜地瞧了一眼那張還在往下滴水的俊臉,馮玉貞百口莫辯,又怕他冒出什麼驚世之語,只覺得腦門和腳踝兩疼一塊去了。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782 章

軟軟嬌妻馭惡夫
惡霸宋彪,是十里八鄉人人提之色變的混賬無賴。 “小娘子,等著老子去下聘娶你。” 顏卿,是舉人家賢惠淑良的姑娘,不管是模樣還是性子,誰見了都要誇上一聲好。 卻是被這個宋惡霸盯上了,眼看著是羔羊入虎口,怕是要被吃得骨頭渣都不剩。 顏小娘子抬起眼,水盈盈的鳳眼迎上男人一張黢黑大糙臉,“好。”
128.7萬字8 60642 -
完結1187 章

旺夫命:拐個夫君熱炕頭
沈九娘穿越了,還嫁了一個活一天少倆半晌的藥簍子,自己這是隨時可能做寡婦的節奏啊。不過好在一家人和和睦睦,婆婆溫柔,小叔可愛,相公又是個極品貼心暖男,日子倒也過得去。家里一貧如洗,她能賺,她一個農大高材生收拾點兒莊稼還不是小菜一碟;有極品親戚…
210.7萬字7.91 54201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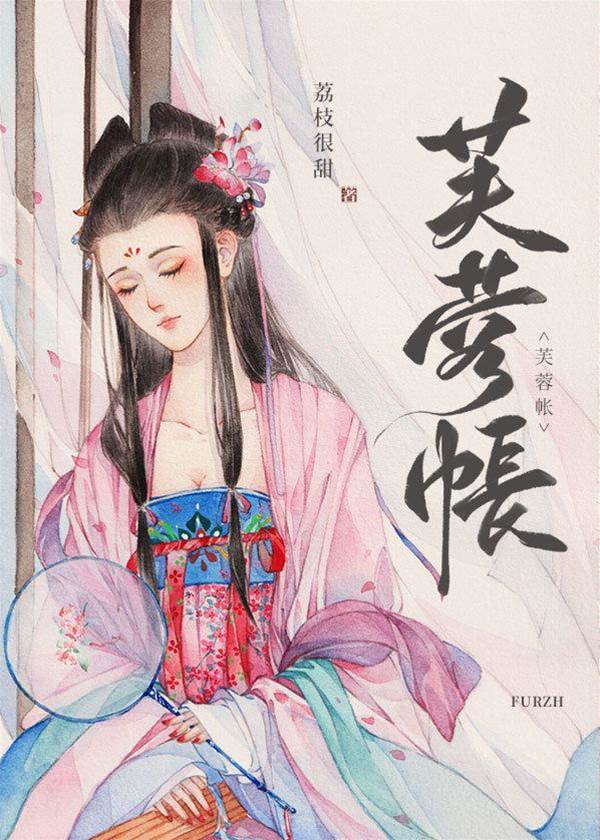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