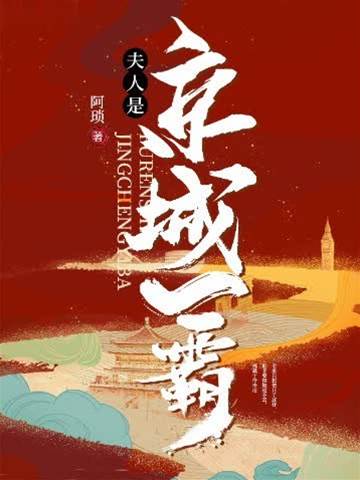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瑤臺春》 第 85 章
殿一下子便靜了下來,蕭明稷側頭過去,雖然隻能瞧見帳外窈窕背影,影影綽綽的,但依舊存了一點僅有的期盼。
鄭玉磬隨手拾起了薄紗披帛,遮住潔肩頭,淡淡道:“若是再立一個皇後掩耳盜鈴,我不會舍得把孩子抱給別人,三郎也不願意睜著眼做瞎子,指鹿為馬?”
蕭明稷願意立元柏做皇太弟,心中便已經足意了,並不願意節外生枝,如今這樣就已經足夠好了。
人的心就是偏的,別說萬一真的生出個男孩來,蕭明稷必然千方百計地將皇位留給他們的孩子,就算是生了一個孩子,自己尚且還在索怎麽做一個母親,兄妹之間也未必就能一碗水端得平。
“三郎雖然能將先帝的事瞞了這麽久,可你近臣知道的也不在數,”憑借這麽多年的了解,鄭玉磬覺得蕭明稷還真有可能會這樣做:“他們本來就覺得元柏是你與我私下生的孩子,如今再來一個,隻怕私底下還以為你有什麽癖好。”
鄭玉磬放得開了,倒也不願意在這種時候同他吵起來,有耐心回轉來哄一哄他。
“生孩子做什麽,如今安安生生的多好,三郎想要瞧我經曆一番苦痛嗎?”頰邊紅霞猶在,滿目波漾,風無限,“不過三郎還是病弱些好。”
鄭玉磬瞧著牛皮做的繩索將皇帝捆得結結實實,他本來就是奄奄一息,那上除了刀傷、箭痕以及新
合的傷口外,滿是遭人輕佻戲弄過後的痕跡,依言解了繩索,連鈴鐺都收好放在一側。
將方才沒來得及放下的帳子隨手落了下來,遮得嚴嚴實實,等著他傳人進來。
他全沒有一好地方,正是弱可欺,鄭玉磬了那被勒得狠了的地方,舒活了他的筋骨,雖然看著可憐,卻又忍不住覺得他實在是自作自。
Advertisement
“你倒是也該惜自己的子,酒與原是伐人的斧頭,本來太醫便說你不好,三郎就這麽急不可待地見閻王,非得走這份捷徑?”
“音音這是惜我的命?”蕭明稷如今被伺候,聽著這樣的奚落倒也不覺得心,含笑握住的手,示意躺到自己邊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這些時日早便盼著音音來主這樣一回,每次你來都會提前服了避子藥,省得掃興。”
他雖然是這樣笑著,但鄭玉磬卻看得出來他心下實則怏怏。
“江院使說那些東西與近來服的藥相衝,勸朕最好不吃,”蕭明稷抬頭向,神平靜道:“可是朕後來想,音音一月也不會到紫宸殿來幾次,你本來就不吃避子藥,萬一你肯,現服可又得等那藥生效,等你沒了興致就又不了。”
他已經好多了,除了偶爾高燒,那骨折帶給人的折磨由痛徹心扉的劇痛轉為酸,太醫們說那滾落卸勁的時候皇帝免不了些外傷,如今這樣也算
正常,隻要心養著,不要活過多令髒出,倒也沒什麽可令人擔心的。
他日日吃那些滋補的藥膳,卻躺在床榻上彈不得,側又有溫香玉,哪怕讓子主有些不自在,但也早早打了這樣的主意,每回過來的時候都會提前修整儀容,隻有病弱而無邋遢,讓音音多注意自己一些。
隻是這些鄭玉磬卻是看不明白的,他早知道音音心好說話,秦君宜與寧越之所以能記掛,無非就是皮相還好,看著慘些,隻要他能音音知道他苦最多,音音就一定更會心疼他。
鄭玉磬聽他這樣說,檀口半張,但是見一貫好強的他眼角有淚痕,不知道是被舒服哭的還是心酸哭的,一時竟然不知道說些什麽好:“我這些日子來得還不夠嗎,你既然用了藥何不早說,平白人擔心?”
Advertisement
“那怎麽夠,音音若是再多來一些才好,我時時刻刻都想見到音音。”蕭明稷側過頭去,避開了鄭玉磬想要為他淚的手,“其實我也知道音音如今不適合再有皇子,不過是想要音音一份心意而已。”
“音音這裏生得這樣好,怎麽藏在衫裏麵,不肯郎君嚐一嚐?”蕭明稷再度看向的時候似乎有幾分失落,“是郎君服侍你服侍得不好了?”
像是總吃不飽的瘦弱小狗,每日到人懷裏乞食,哪怕後來長大了變得強壯也是一樣,眼眼地等在那裏
,強壯,卻又顯得十分弱小無助,可憐的。
蕭明稷暗暗攥了錦被下的拳,然而卻又鬆開了,服侍了一會兒,趁著換另一邊的空檔,不舍地,延長方才殘存的快樂,溫聲道:“音音喜歡就好,你如今倒是信我,郎君說服藥你便信了。”
他倒是也不敢不服,鄭玉磬當真不願意為他生育的時候,即便是懷上了也會想方設法打掉,或者子憑父貴,他如今還隻是能音音主來同他燕好,可是兩人還沒好到能孕育子嗣的程度,不會對這個孩子和他好,反而對那個孩子心存愧疚。
“倒不用這樣麻煩,我將三郎綁在榻上堵住就夠了,”鄭玉磬隨手拿起自己的青掃過他的臉龐,低聲相近:“郎君邊可用之才多得是,我若是有孕,隨便趁聖人昏睡,同哪個男子在榻之側尋歡,將那孩子流掉了,你也不會知道。”
像是哄孩子一樣威脅著他,手上輕拍他的後背,“讓我想一想,到底尋哪個好呢?”
那曼妙曲線上的手臂忽然將人勒得有些不過氣,幾乎子都酸了,倒在他側。
多用了幾分力氣去拍打蕭明稷的肩頭,可不知道蕭明稷是不怕疼還是怒意太甚,竟然怎麽也不肯放開,方才的楚楚可憐與小心翼翼消失不見,連帶手也不安分了起來,牢牢固定住,。
Advertisement
“音音,朕就算是怎麽順著你都好,可
你若是想這些,郎君明明白白地告訴你,絕無此等可能!”
蕭明稷對哪裏喜歡輕,哪裏喜歡狠辣差不多都是曉得的,在自己手裏狼狽了一回,心裏想殺人的戾氣才平複了許多,他憐道:“音音缺了滋潤隻管來尋我,郎君樣樣都比別人強的,便是手或者舌也能音音舒坦。”
他果然還是沒有那麽大的襟,這些事他對先帝來做,隻會覺得刺激與報複的快意,可換作他是病榻上的天子,別說真的那樣去做,即便是想一想那種畫麵,都足以他心神俱碎,恨不得即刻從榻上起來取劍親手斬下那男子的狗頭。
好在沒說要秦君宜來這裏同重溫舊夢,否則他現在就會人賜死秦君宜。
“那皇帝往後倒是用舌來一回,這樣幹地說誰又不會?”鄭玉磬冷哼了一聲,“我瞧著皇帝怕是傷得也沒有那麽重,力氣比我大得多,又怎麽需要我來照顧?”
“音音喜歡的話,朕伺候便伺候了,”蕭明稷聽到的話心裏一,含笑咳了兩聲道:“郎君方才氣極了,所以才忘了疼,隻怕一會兒還要去尋江聞懷重新請脈。”
“音音,你以後別那樣說了,”他平複了咳嗽,才用額頭相抵,聲哀求道:“你這樣說比拿刀來剜我的心還人難,郎君都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些什麽樣的事。”
他人吩咐傳水沃手,又讓人換了幹淨的
給,鄭玉磬才覺得自己得了解,可是卻不願意理他,讓他一個人吃力地來拭自己。
果不其然,聖人這一回又把人惹惱了,隻吩咐侍將東西都送進了帳子裏,可是不讓人伺候用水,還得親力親為。
Advertisement
他留神聽著,鄭娘子在的時候,聖人咳嗽要水的次數都比平日多了十倍不止,果然是傷,可是他也不敢去求太後勸一勸聖人,本來鄭娘子就夠不願了,萬一聖人知道是他的“好心”,隻怕恨不得立時三刻要了他的命。
鄭玉磬等到皇帝替細細過了才冷著臉起,瞧一瞧外麵的日,也知道時辰不早了,冷著臉賭氣下榻,卻聽到帳中男子撕心裂肺地咳了幾聲,聲音略啞地說道:“夏天裏日頭更足,音音回去也是難耐酷暑,不如留在這裏多些,等到日頭落了再走。”
“那裏還有好些折子,朕頭疼難當,不如音音替朕念一念,權當是消遣,好不好?”
萬福也正想跟著應和幾聲,但看到聖人當真是有幾分頭疼難耐的模樣,上傷痕累累,猶豫了幾息,最後還是恭順地喂了聖人幾口止咳的水,沒有搭話附和。
聖人是被鄭娘子一時之歡衝昏了頭腦,鄭娘子偶爾來一回也就算了,真這樣日日往來,別說是聖人如今臥病在床,就算是魄強健,也不得這樣。
“皇帝不盡的時候怎麽不說頭疼,不惦記著批折子?”
鄭玉磬瞧著他的淒慘也覺得活該,讓枕珠進來替弄一弄頭發,施施然坐在妝鏡臺前,擺弄脂,“若是真對國事這樣上心,合該做那檔子事的時候也惦記著國計民生,一刻不忘才是。”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供侍寢嬪妃梳妝打扮的妝鏡臺已經不是在紫宸殿的側殿,而是在天子議事的殿。
蕭明稷知道現在還不願意在自己的寢殿見臣子,怕臣子們見了兩方尷尬,可是偏偏又將本來獨屬於皇帝的殿安置了許多子所用之,進來議事的宰相偶爾一瞥也能瞧得見。
可是今上後宮空虛,並不像父親那樣有可以破格寵的嬪妃,那來皇帝寢宮又需要梳妝更的子是誰,答案一目了然。
這嫌避了,似乎又沒有完全避開。
“音音所言不差,朕以後一定改的。”
蕭明稷起倚在榻邊,看鄭玉磬梳妝,在榻上的時候嫵萬分,下了榻又是渾帶刺,雖然依舊紮手,可比起從前的一味冰冷卻是好上許多。
“讓寧越進來給你弄吧,他手巧些。”蕭明稷看著枕珠在給鄭玉磬盤發,似乎有些不夠靈巧,“你梳一個輕便些的發髻,頂著也輕鬆些。”
鄭玉磬不知道皇帝弱不風地倚在床榻邊,心裏惦記的都是些什麽齷齪事,他上穿得不夠整齊,也肯讓侍進進出出打掃,換了新的焚香,開窗灑掃,便應了一聲,讓寧越過來侍候。
蕭明稷
在這件事上倒是很倔,在的時候不許人挪聖躬下榻更換床榻上的舊,非得走了才行,雖然覺得好氣又好笑,但也懶待去管。
寧越今日跟來,就一直在外麵守著,皇帝平日不喜歡有侍在殿打擾他與太後“理公務”,而紫宸殿的侍比他這等更合乎皇帝心意,因此並不需要他。
他進來的時候先請安,覷到今上神間的饜|||足與邊的笑意,知道他大概是存了幾分炫耀的故意,但是仍舊沉悶地走到鄭玉磬邊,伺候梳妝。
銅鏡清亮如水,映照著子略顯倦乏的嫵麵容,雖然一便知是午間缺休息的困乏,可是卻比往常的氣更好些,麵如桃花,眼含秋水,正適合梳一個華麗的發髻。
隻是那薄羅衫子下約浮現的點點紅痕有些刺眼,仿佛在無聲地宣告方才殿的男做了些什麽。
他知道皇帝無論是在做什麽,眼神一定在著這裏,心裏忽然起了些爭強好勝的心思,一點點為鄭玉磬理順發,一一分開備用,低聲道:“娘娘想來也疲倦了,不妨奴婢回去伺候沐浴,給您好好按一番,養一養神。”
鄭玉磬沐浴是從來不用寧越伺候的,即便是濯足,也隻是偶爾才出於看重他手藝的份上做幾回,沒有細想他為什麽忽然問起這些,隻是順著話說了起來,一時沒有顧上蕭明稷送來的目
。
蕭明稷正有些不悅,想要讓寧越梳了發便到一側去,省得妨礙他同音音說幾句,讓消一消氣,明日繼續過來。
然而鄭玉磬的頭發才盤到一半,一個外殿伺候的小黃門忽然躬進來,向聖上與太後請了安,恭聲稟告道:“聖人,秦侍中求見。”
蕭明稷沒在殿見過臣子,隻是秦君宜最近自覺避開皇帝的目,很宮,都是托另外一位周侍中宮覲見。
他瞥見鏡中的子笑容似乎有一瞬間的僵直,想到方才那些說來氣他的話,心中的妒意不覺加深了許多,咳了兩聲,示意鄭玉磬起避讓,同那吩咐道:“他進來。”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惜花芷
藏拙十五年,花芷原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穩一輩子,可當花家大廈將傾,她不得不展露鋒芒出麵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拋頭露臉是常態,打馬飛奔也常有,過不去了甚至帶著弟妹背著棺材以絕戶相逼,不好惹的名聲傳遍京城,她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她刀子的心理建設,也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獨獨沒想到會有人在出征前盔甲著身向她許終身!好稀奇,這世上竟然還有人敢娶她!?
132.4萬字8 211841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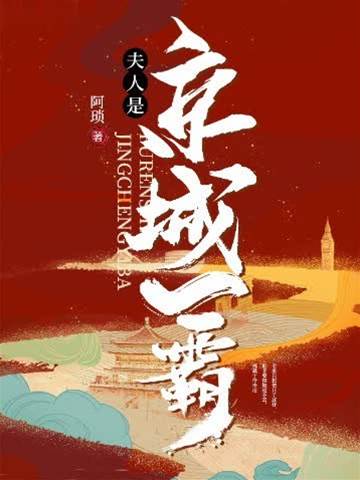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23 章

我不做妾
沈瀾穿成了揚州瘦馬。 雲鬢花顏,瑰逸絕倫,當得起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正因這份美貌,她要被送去給巡鹽御史裴慎做妾。 沈瀾不願意做妾,千辛萬苦逃了出去。 陰錯陽差,成了裴慎的丫鬟。 對丫鬟這份工作,沈瀾尚算滿意。 雖然全年無休007,但薪俸極高,常有外快。 更讓她滿意的是裴慎快要成親了。 只等裴慎成婚後,她便能銷去奴籍,靠着自己積攢的人脈、錢財,快快樂樂過完這輩子。 就在她滿心歡喜,只等放良之時,忽然發現,裴慎想納她爲妾。 沈瀾:我不做妾。 * 裴慎三年前就想納沈瀾爲妾,只是因爲守孝不得已忍了三年。 越隱忍,越剋制,想得到她的心思就越強烈。 如今三年已過,將要成親,正是納妾的好時候。 * 裴慎一生順風順水,官路亨通,遇到沈瀾,才知道世間唯情愛二字,最是摧心折肝。
39.9萬字8 74908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