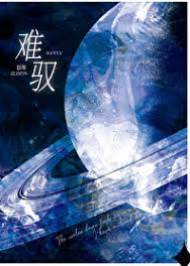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掐腰寵,被痞子三爺撩哭了》 第345章 自食其果
進茶水間后,虞笙邁著輕盈的步伐,若無其事地走到吳月旁,然后低聲音,輕地問道:“吳月,你是不是有什麼東西不小心掉在走廊上啦?”
吳月聽到這話,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疑,但還是條件反般地轉過頭去,朝著走廊方向張過去。
眼見吳月走出茶水間,虞笙趕躡手躡腳地走到趙思思的水杯旁,輕輕將握在手中的神品放其中。
就在虞笙做完所有這些作的時候,非常湊巧的是,吳月恰好在這個時候回到了茶水間。
的臉上掛滿了狐疑的神,地盯著虞笙,不解地追問道:“什麼東西呀?我怎麼沒看見呢?”
面對吳月的質問,虞笙迅速調整好自己的表和狀態,故意裝出一副茫然失措、十分困的樣子回答道:“啊,是嗎?”
說著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快步走到門口,朝走廊上瞥了一眼。
著空的走廊,出滿臉狐疑的神嘟囔著:“奇怪,我剛才明明看到有個東西在那里的呀。”
吳月被虞笙的話勾起了好奇心,忍不住又追問一句:“你看到的究竟是啥玩意兒啊?”
“我當時真的沒有注意到啊,說不定真是我看花眼了呢。哎,你也是了解我況的呀,畢竟懷著孕嘛,眼睛有時候會花也是正常現象啦。”
Advertisement
吳月聽了這番話,并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默默地接滿水,然后端起水杯徑直離開了茶水間。
虞笙跟著也走進茶水間,接好一杯水后便返回了辦公室。
可誰知前腳剛踏進辦公室,后腳就被司南給喊住了。
“虞笙。”
虞笙略帶驚訝地看向司南,疑地問道:“組長,找我有什麼事嗎?”
自從上次陳璐在公司鬧那麼一出后,虞笙特意的和司南保持了距離,也不像一開始一樣司南南哥,而是稱為組長。
聽到虞笙如此生疏的稱呼,司南心中不泛起一苦,但臉上卻并未流出毫異樣。
他強作鎮定,擺出一副嚴肅認真、秉公辦事的樣子說道:“跟我去一趟工地吧。”
虞笙聽聞此言,當場愣住,下意識反問道:“現在就要過去嗎?”
司南眉頭微皺,語氣生地反問:“難道你現在還有別的安排不?”
虞笙見狀,連忙擺手解釋道:“那倒沒有,不過稍等一會兒哈,我先整理下東西。”
說完,快步走到自己的工位前,迅速將尚未完的工作進行保存,關閉電腦并整理好相關品。
就在拿起筆記本準備之際,突然間,一陣尖銳刺耳的尖聲從后傳來。
“啊!我的!“
聲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整個辦公室的人都被驚了,紛紛側目過去。
Advertisement
眾人目所及之,只見趙思思捂住自己的,里嗚嗚呀呀地嘟囔著些什麼,但由于說得含混不清,誰也聽不懂說的到底是什麼。
吳月滿臉憂慮地看著趙思思,關切地問道:“思思,你怎麼......“
然而,的話還沒說完,便驚訝地發現有鮮紅的正順著趙思思的手指隙流淌而出。
吳月頓時嚇得臉蒼白,驚恐萬分地問道:“你,你的怎麼了?“
趙思思則死死捂住,用充滿怨毒的眼神狠狠地瞪著吳月,然后一言不發地徑直走到吳月旁,揚起手毫不猶豫地給了吳月一個清脆響亮的耳。
此刻的趙思思滿口都是鮮,含糊不清地咒罵道:“賤人,你在我水杯里放了什麼?“
這突如其來的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大家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而被打的吳月更是驚愕地呆立當場,臉上火辣辣的疼痛和心的委屈織在一起,
做夢也沒有想到,趙思思居然如此不顧面,竟敢當眾掌摑自己!
那一瞬間,的眼底掠過一抹惡毒,但轉瞬間便恢復如初,仿佛一切從未發生過一般。
只見捂住自己被打的面頰,淚水在眼眶里打轉,滿臉無辜地向趙思思,哽咽道:“思思,你怎能這般冤枉于我呢?”
然而,趙思思似乎并不打算善罷甘休,揚起手來又施暴。
Advertisement
就在此時,司南站出來制止了,并將目投向趙思思傷的,不眉頭蹙,關切地說道:“好了,流不止這樣子,還是趕快去醫院檢查一下傷勢。”
趙思思聞言,拿起紙巾拼命拭角不斷滲出的鮮,可無論怎樣努力,跡依舊源源不絕。
怒目圓睜,狠狠地瞪了吳月一眼,咬牙切齒地罵道:“賤人,你等到,要是讓我知道是你弄的,我弄死你!”
虞笙見勢,不僅不退,反而膽子大了起來,眨了眨眼,調皮地開口:“哎呀,有句老話兒怎麼說的來著?”說完,還故意裝模作樣地沉思片刻,這才慢條斯理地揭曉答案:“哦對了,自食其果。”
趙思思愣住了,眼神中閃過驚愕與憤怒,猛地轉頭,目如刀般向虞笙。而虞笙呢,就像是早有準備一樣,臉上掛著那副標志的得意笑容,靜靜等待著趙思思的反應。
當趙思思的目落在虞笙那張笑臉上時,突然明白了什麼,手指直指虞笙,聲音尖銳得幾乎能劃破空氣:“是你!”
虞笙角微翹,笑意更濃,故意裝出一副無辜的模樣,仿佛對趙思思的指控一無所知。!”
趙思思的雙眼鎖定虞笙,怒火中燒,的聲音充滿了質問:“虞笙,是不是你做的?你怎麼能如此狠毒?”
Advertisement
虞笙卻似湖面般平靜,微微挑起角,語氣冷淡而堅定:“趙思思,你憑什麼認為是我?沒有確鑿的證據,就別扣帽子。”
趙思思被的話一噎,張了張,下意識地反駁:“除了你,還能有誰?那些刀片明明……”
話到邊,突然剎車,戛然而止。
虞笙的笑意更深了,似笑非笑地看著趙思思:“怎麼?‘明明’后面的話,不敢說了嗎?”
趙思思瞪大了眼睛,眼中閃爍著惡毒的芒,狠狠地盯著虞笙。
的心充滿了困,完全不明白眼前的狀況是怎麼一回事。
原本藏匿在虞笙杯子里的那把刀片,竟然意外地出現在了自己的杯子里,這讓到無比的震驚和惶恐。
的大腦一片混,完全不知道如何解釋這個詭異的局面。
猜你喜歡
-
完結235 章

她是翟爺掌中嬌
暮家千金得了怪病,六年來藥石無醫。傳聞她犯病時兇殘成性、六親不認,最終釀成大錯,成為眾矢之的!偏偏,有個大佬寵她入肺。「翟爺,暮小姐又犯病了……」「這次又傷了誰?」「倒是沒有傷了誰,就是把後院的花草樹木都給剪禿了……」男人漫不經心:「那一定是那些花草樹木得罪了她,全部挖了!」「……」「不好了翟爺,暮小姐她又犯病了!」「嗯?」「打碎了夫人的寶貝玉鐲!」「那一定是那枚玉鐲得罪了她。」「……」翟母急得跳起來:「兒子!你對她的偏袒還敢再明顯點兒麼!?」「不好了翟爺,暮小姐又犯病,把您和她的婚房給拆了!!」「……」婚房!?男人驚跳起身,即衝到二樓,一臉禁慾溫柔:「夫人乖,婚房拆不得……」
20.6萬字8.7 55183 -
完結1242 章

和大佬閃婚後馬甲掉光了
“今天是黃道吉日,我們離婚吧!”“顧少,我就是個惡女,我配不上你!我們離婚吧!”“顧少,我……,我們離婚吧?”為了繼承遺產,她隨便閃個婚,卻不小心招惹到大佬。從此纏她入骨,寵她上天…怎麼甩也甩不掉!頭疼,說好的臨時老公呢?說好的一拍兩散呢?梁希成天變著法作妖,就為了離婚。結果卻被他反手擒住:“結婚容易離婚難。想離婚,下輩子吧!”梁希慘兮兮地哀嚎:“你到底看上我啥,我改還不行麼?”某男含笑:“超級黑客、絕世神醫、頂級殺手、異能者…你這麼厲害,我為什麼要離?”原來,她的小馬甲已經被人剝光了!
204.6萬字8.18 191827 -
完結823 章

第一名媛,總裁的頭號新妻
她叫慕晚安——後來,安城所有人提起她時的眼神都是不屑又艷羨的。………………他在雨夜將她撿了回去,瞇眸淺笑,「嫁給我很委屈?」她挺直背脊,煙視媚行的微笑,「顧公子心有所屬,私生活不檢點,嫁給你不能更委屈。」隔著青白的煙霧,顧南城英俊的容顏模糊,「可我看上你了。」顧南城看上的女人無處可逃,第二天各大有錢人都收到消息,誰敢借錢給落魄名媛慕晚安,就是跟他作對。她最沈淪的時候就是他在床第間親著她低聲呢喃,寵溺繾綣,晚安,晚安。…………後來的後來,新貴名導慕晚安因殺人未遂而入獄,判刑四年。坊間八卦流言四起,顧太太因嫉妒開車差點撞死的是情敵。據說,顧公子等了一個白天,換來的也只是她對獄警彎唇淺笑,「我不見他,永遠不。」…………四年後出獄,她勾唇淺笑輕而易舉的推翻了當初的誓言,長裙嫵媚的出現在他的面前,像是第一次見面那般伸手微笑,「顧總,有興趣投資我的新電影嗎?」他吞雲吐霧,意味不明的盯著她,「不是不肯見我?」「我有孩子,要養家。」當初端莊矜持的第一名媛開始遊走於各路男人之間,香艷旖旎的傳聞紛至沓來,卻抵不過顧氏總裁日漸濃厚的寵愛。顧南城像是得了一場心理疾病,病態般的寵愛著他的前妻。哪怕她從不拒絕任何男人的花。哪怕她偶爾被狗仔拍到跟金融界的大亨約會吃飯。哪怕……她的孩子,壓根不是他的種。有天她醉得酩酊,媚眼朦朧口齒不清的笑,「顧公子他啊……可能就是犯賤,偏偏最愛那個不喜歡他的……,現在這樣……從前也是這樣……一直都是這樣……」眾人看著從後面緩緩而來接心上人的顧公子,嚇得恨不得消失。他一言不發,沈默不語的抱著她上車。她湊過去噴著酒氣,笑瞇瞇蹭著,「生氣了?」「怎麽會,」他淡淡的看著她的笑意不達眼底的模樣,「能生氣就不用犯賤了。」————誰都知道,你是我的鬼迷心竅。
205.4萬字8 32442 -
完結207 章

嚴總要跪搓衣板哄小心肝了
【雙潔】【偏執霸總追小尾巴】【無底線追妻,寵妻狂魔】“你就沒有一點喜歡我嗎?”“我不喜歡你,現在不喜歡,以後也不會喜歡”終究,他的心還是捂不熱……在她轉身離開後,他才知道他錯得有多離譜……深愛而不自知的他,把跟在他身邊18年的小尾巴,弄丟了。四年後“嚴辰煜,你到底想怎樣?耍我有意思嗎?”“沒有,我隻是想請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可是,我已經不喜歡你了”最後嚴辰煜高冷禁欲的形象不複存在,死皮賴臉,窮追不舍,妥妥變成了纏人的大醋缸……“夏夏,我們別穿那麼短的裙子好不好?”“夏夏,不能看別的男人。”“夏夏,我愛你……”(本文無天降,不會換男主,男主前期榆木腦袋,愛而不知,後期瘋狂追妻,寵妻狂魔!甜寵文,不是be文哦,喜歡大女主虐渣男的請勿入錯坑!)ps:男主前期隻是木頭,不是不愛,相反的是很愛,沒有白月光,身邊沒有女人,不渣,希望有天降男友,請勿入錯坑!)
34.7萬字8 25211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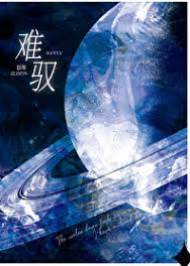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9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