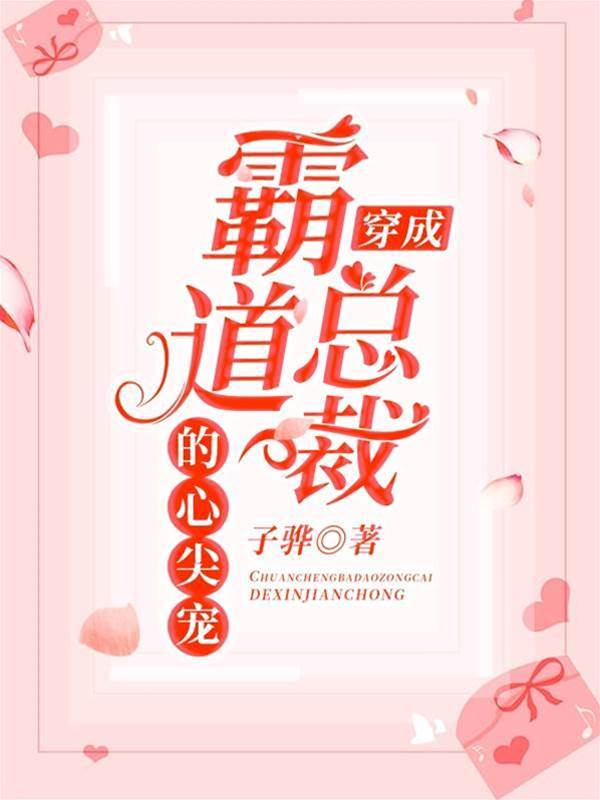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折她豔骨》 第159章 需要點刺激
“你怕你死的不夠快嗎?”
慧覺口而出,而後反應過來,裴宵是要把長公主、九郡王、大王爺統統釣到青雲寺來,讓他們廝殺。
南齊半壁江山混戰起來,可是一場大戲!
裴宵瞇眼著紫城的方向,饒有興味道:“這麽彩的戲碼,還得勞煩大師再去請一位夠分量的看客才行。”
“行,他本來每三個月就會來一趟青雲寺,這件事給我。”慧覺應道:“另外,千仞了傷,被北營的人救了,要不要讓他回來?”
裴宵鬆了口氣,思忖片刻,“讓他留在北營靜養吧。”
青雲寺接下來會不得安生,一個傷員就沒必要回來湊熱鬧了。
慧覺深以為然點了點頭,“那你醒了的事,不打算跟夫人說實話嗎?”
裴宵眸晃了晃,“就這兩三天了,再忍忍吧!我怕知道我活著,演戲會餡了。”
“你夫人可會演得很,連長公主都被騙了呢。你不知道吧?你家夫人差點和長公主同歸於盡了。”
慧覺把從千仞來信裏知道的關於薑妤的事,跟裴宵一一道明。
裴宵愣在原地良久,他怎麽也沒想到薑妤會為了他不顧命。
裴宵心中五味雜陳,眼尾攀上笑意。
屋子裏沉默了片刻。
慧覺靈一閃,“你在你夫人麵前裝死,不是怕演戲餡,是想你夫人一直微伺候你吧?”
Advertisement
裴宵腦海裏頃刻浮現出幫他沐浴的畫麵。
薑妤平日,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剛剛清洗得倒很仔細。
手的……
裴宵耳微燙,清了清嗓子道:“我沒那麽無聊!”
“你有!”慧覺已經看他眼神裏的猥瑣了。
裴宵懶得理他,將一本冊子拋了過去,“你閉就好!記得把此給夫人。”
“這什麽啊?”
慧覺到了書冊上未幹的墨跡,翻開一看,差點沒被噎死。
裏麵寫的不是別的,是各種詩。
“你哪弄來的?”慧覺翹著蘭花指,拎起那本書,嫌棄地恨不得給他扔了。
上麵的話麻兮兮的,也太惡心了!
“合著你剛剛筆疾書,是在寫詩?”
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慧覺還以為他在做什麽大事呢。
“你一個和尚,管那麽多做什麽?給就是了!”裴宵負手走過慧覺邊時,催促道。
而後,步伐輕盈地朝寢房去了,仿佛十分期待。
裴宵大約覺得薑妤說的那些話還不夠,自己專門寫了本寶典,讓媳婦兒讀給他聽。
慧覺覺得裴宵這個人多是有點變態在上的……
這種變態,值得給大家分。
於是,半個時辰後,慧覺便帶著裴宵的傾力作去找薑妤。
彼時,薑妤醒過來後,發現裴宵還躺在邊,並沒有轉醒的跡象。
Advertisement
薑妤穿了服,急匆匆出門,剛好到了慧覺來敲門,“大師,我夫君怎麽到現在還沒醒啊?”
薑妤抹了把額頭上的汗,“我剛剛已經跟夫君聊過了,覺他心跳似乎恢複正常了,但總不醒。”
慧覺瞧了眼床榻上躺著的裴宵,分明他一副眉飛舞、小人得誌的模樣。
“他可能就是單純想跪板了。”
“大師,你說什麽?”
“我說……”慧覺把裴宵的書給了薑妤,故作深奧捋了捋胡須,“以貧僧醫病數十年的經驗來說,可能夫人太過委婉,給他的刺激不夠,對裴施主這種死變態……不是,這種子清冷的人來說,需要下點猛藥!不如夫人試試這本書?”
“好!多謝大師!”
薑妤不疑有他,畢竟慧覺剛剛教的法子的確奏效,裴宵臉好多了。
薑妤想著大約和針灸一個道理,進針三分不夠,就進五分,總能把裴宵刺激醒的。
薑妤懷著這樣的心思捧書坐在裴宵榻邊,細聲輕語地念著。
前麵尚且還是“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之類的詩,可後麵越來越離譜。
薑妤頂著通紅的臉,在裴宵耳邊糯糯道:“夫君是妤兒的天,是妤兒的心頭,妤兒每天都想和夫君親親,每天都想和夫君睡……”
Advertisement
薑妤說不出來了,幹嘔了一聲。
躺在榻上裴宵卻聽得麵紅耳赤,心跳加速。
妤兒,從不肯跟他說話。
裴宵倒想趁這次機會,聽聽他家乖巧的夫人說起骨的話,有多好聽。
可嗬氣如蘭,吳儂語像清風吹進裴宵耳朵裏,裴宵著實有點抵抗不住,呼吸微。
正等著後麵更親的私房話,薑妤卻停住了,將書本丟在了桌子上,雙手托腮自顧自和裴宵聊了起來。
“夫君,你說慧覺大師該不會是個變態吧?冠禽那種?”
“表麵上一本正經,壞心思多得很!正常人誰能寫出這麽骨的話啊?”薑妤越想越篤定,“他這話信手拈來,我怎麽覺寫書的人定是場老手,調戲過不姑娘?”
裴宵眉頭幾不可查地皺了起來,覺頭頂上方有雷隨時要劈中他。
“一個大男人能寫出這種話肯定作風不檢點,經常去勾欄坊耳濡目染!”
薑妤越想越不對,“我還是去問問慧覺安得什麽心,把這種書送到夫君邊!”
“咳!”
裴宵幹咳了一聲。
什麽逛青樓、調戲姑娘?
裴宵怎麽不知道他家夫人原來想象力這麽富。
“咳咳!”
已經走到門口的薑妤聽見裴宵終於有了反應,才折返回來,讓裴宵的頭枕在自己上,著口幫他順氣,“夫君,你還好吧?”
Advertisement
裴宵麵蒼白,很不好。
薑妤要知道這書是他寫的,豈不又誤會他是什麽好孟浪之徒?
這樣的大家閨秀,哪裏能接?
剛剛建立起來的一點好眼見就要崩塌了。
裴宵心緒浮。
薑妤近距離抱著他,輕易到他心跳加快,儼然就快要醒了。
看來慧覺大師還是英明的,下點猛藥,多刺激刺激就會有覺。
無論如何,讓裴宵醒過來才是最很重要的事。
薑妤忽而靈一閃,頂著紅撲撲的臉,在他耳邊聲道:“夫君,要不我給你背、背《金瓶梅》?”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