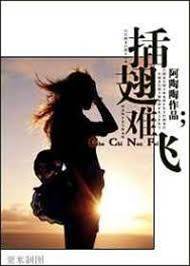《你被開除了!》 第83章第八十三章
因為早上六點就要趕去公司最終確認談判方案,季臨本想悄悄地起床, 不吵醒白端端, 留下讓繼續睡,結果沒想到十分警覺, 又因為抱著的姿勢,自己微微一,白端端就睜開了眼睛。
然後就黏上了季臨……
白端端洗漱完畢, 坐在餐桌前,一邊安安靜靜喝牛,一邊盯著季臨, 語氣堅定:「我和你一起去。」
雖然季臨心裡已經不再那麼介意輸, 但說起來總是不希朋友目睹自己輸的過程的, 他下意識找理由拒絕道:「公司並沒有聘請你作為代理律師,你留在酒店等我。」他親了親白端端的側臉, 「我會儘快回來。」
白端端善解人意地點了點頭:「對哦, 我沒有和公司簽代理協議。」然後抬頭看了季臨一眼,「但是, 我記得我職盛臨的時候, 除了作為獨立提律師外,還兼任你的助理工作呢,不能作為這案子的代理律師一同前去也沒事, 我作為你的助理一起去就行了。」
「……」
論歪理邪說,季臨覺得自己好像都快不是白端端的對手了。
隻是白端端對付自己,好像總是非常有一套, 說完歪理邪說,輕輕歪了歪腦袋,用溫順乖巧的目看向自己,然後地又開了口——
「我就是想這種時候陪在你邊。季臨,好不好啊?」
季臨抿著:「別撒,撒沒用。」
隻是話雖然這麼說,一刻鐘後,季臨卻已經皺著眉麵冷酷地和白端端坐在同一輛駛向公司的車上了……
很憾,白端端的撒總是有用。
*****
納米企業的負責人蔡銘接待了白端端和季臨,白端端作為助理份前往,隻坐在會議室裡安靜地聽著季臨和對方通不同方案,闡述告知即將到來的談判裡將會出現的任何可能,蔡銘對當下的況愁眉不展,也補充了一些細節,然而對支撐贏得談判並沒有什麼幫助。
Advertisement
「總之,做好最壞的打算,先聽聽員工開什麼價。」在客戶麵前,季臨永遠是值得信賴的穩重模樣,他鎮定道,「越是這個時候,你越是要保持冷靜,淡漠一點,讓來談判的勞者代表不知道你的緒和底牌,穩得住,不要流什麼表,其餘的談判給我,先清他們的要求。」
「一般而言,這種時候,這些員工想要省心省事的快速拿到錢,所以也不會願意真的勞心勞力到必須對簿公堂的地步,何況他們自己心裡有數,勞合同本是簽約過的,隻不過被高管損毀了,但他們不掌握我們的資訊,不清楚我們是否有別的佐證可以證明曾經簽過書麵合同。所以第一次談判至關重要,這是彼此的一種試探,公司方一旦有任何怯,那員工就會獅子大開口了。」
勞資糾紛,第一次談判時,勞者和企業方隻要還沒有徹底撕破臉皮,還是存在各退一步達協議的可能的,畢竟走仲裁和訴訟,對時間力都是一種虛耗。
「所以我們先聽一下這第一次談判勞者代表的開價。」季臨微微皺了皺眉,「據我的經驗,隻要他們的態度並沒有那麼堅決,這第一次報價都是可以砍的,隻是還需要經過多次談判再進行磨合,彼此試探對方底線,有時候也是一場心理戰了,你要做好準備。」
蔡銘一臉凝重,然後對季臨點了點頭。
幾個人,都是嚴陣以待,而在他們最後確定完方案和談判策略後沒多久,前臺就來了電話。
勞者代表已經到了。
白端端看了季臨一眼,他的表冷靜自若,然而眉心還微微皺著。
白端端出手,在桌下握住了季臨的,季臨先是愣了愣,他側頭看了白端端一眼,白端端隻對他笑,然後季臨也握了的手。
Advertisement
*****
很快,會議室的門被開啟,勞者代表一共三人,陸續走了進來。
白端端快速觀察了下,這三個代表裡,為首的是個四十來歲戴著眼鏡的中年男人,看起來文質彬彬,有讀書人的氣質,大概對法律條款略有所通,不太好對付的樣子。
這個中年男人的左側是個更為年長的子,年齡看起來似乎都快要退休了,白端端沒忍住皺了皺眉,這類正是戰鬥力最強的老阿姨,也有些棘手啊……
而三個代表裡最後一個,倒是個還比較年輕的男人,看起來工作了沒幾年,和另外兩個代表對比起來,就顯得不那麼穩重和難以接近了,白端端幾乎當下立斷,覺得這個人將為談判的突破口。
心裡甚至盤算好了,如果是以這個年輕的勞者代表為突破口,倒是不一定季臨談判會有優勢,或許自己來會更好,異之間有時候對抗會減弱一些,雖說職場上大部分時候存在弱勢,但也並非完全沒有優勢的。
隻是尚在計劃中,倒是對方三人中為首的那個中年男人先開了口——
「蔡總,今天我們想來談談我們勞合同的事。」
蔡銘看了季臨一眼,擺出了鎮定而沒有破綻的神:「可以,所有一切我委託了季律師和你們通。」
這中年男人愣了愣:「不用,其實不用找律師談的。」
季臨皺了皺眉:「所以你們的要求是什麼?」
他並不喜歡虛與委蛇,更喜歡不浪費時間的開門見山,而就在季臨白端端和蔡銘都等待著勞者開口要錢之時,對方三個人的反饋卻完全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不,我們其實不是來要求解除合同和賠錢的。」那個中年男人有些失笑,「我們就是想來問問,這個月的工資月底還能發出來嗎?」
Advertisement
「月底要是發不出,那下個月月初能補發出來嗎?」這中年男人邊的年輕男子也開了口,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蔡銘一眼,「我正好裝修婚房,這個月添了好多大件,刷了信用卡,這個月工資不發還能支撐下,但是下個月月初我就要還款了……」
蔡銘顯然愣了愣,而別說他,白端端和季臨也有點意外,勞者代表這個開場白,是葫蘆裡賣的什麼葯?探底嗎?
季臨對蔡銘使了個眼,蔡銘理智地沒有開口,季臨便向了三個勞者代表:「工資的問題,隻要你們當月確實付出了勞,正常在進行工作,那公司將合法支付應當支付的款項。」
這回答其實非常方,然而細細一品,什麼資訊也沒有,就算對方準備了錄音筆,這番話也是滴水不。
那中年男人頓了頓,然後有些失笑:「蔡總,真的,沒有必要請律師的,其實我們直接談效果會更好。」他不認同地看了一眼季臨,然後看向蔡銘,語氣溫和,「我們沒有想要去勞仲裁,也沒有想過離開公司。」
「我們知道張臣他們幾個高管做的事,我們知道他們是故意銷毀了所有的勞合同書麵合同,也知道公司最近資金周轉困難,確實這個月按時付工資很難,但我們沒想過去告公司,也沒想過利用他們毀掉合同的事,訛公司一筆雙倍工資。」
對方的語氣平和真誠:「我們這次來,其實主要就幾件事,第一件,也是大家最關心的,想問問公司的困境,會持續多久?這個拖欠的工資,下個月能不能發?如果能發,我們這裡整理了一份名單,都是員工裡家庭況比較困難或者是近期急需錢的,能不能讓財務先把工資打給這些員工?我們其餘剩下的人,公司要是短期發不出來,也出個證明,給個說法,最晚什麼時候能發,讓大家安個心。」
Advertisement
對方說到這裡,明明討薪是他們在理的事,卻有點不好意思:「我們都是工薪階層,就算有些家裡條件相對好些能撐的時間長一點,但其實可能也沒幾個月……所以蔡總,我們就想問問,公司現在到底是什麼況?」
蔡銘了,想開口,卻被季臨的眼神製止了,季臨的意思非常明確——先聽勞者講完。
「要是公司雖然資金鏈有點問題,但是隻是一時的問題,那能不能明確告訴我們,需要我們撐多久?要是隻有一兩個月,那我們就一起勒腰帶,陪著公司過去,那些家裡確實困難的員工,我們也告訴他們真實況,讓他們自己選,他們急需用錢,可能等不起,那就先去找別的工作。」
「要是公司真的不行了……那我們也都儘早去投簡歷。」
這個態度,眼看著是勞者有極大的化,完全朝著任何人沒想過的好的方向去發展了。
不過季臨仍舊十分謹慎,對員工天然的抵和過去自己父親的經歷讓他仍舊覺得不妥,總覺得這些員工代表是在計劃著些什麼謀,用這種方式麻痹他們的神經,他抿了抿:「這是你們想談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我們過來是想和公司補簽勞合同的。」那中年男人誠懇地看向蔡銘和季臨,「我們知道公司的勞合同都被毀了,我們兩百來個員工討論過了,大家都願意和公司補簽勞合同,把合同備份的流程補全。公司的合同版本雖然沒了,但我們手裡都還有原件。」
這時候,他纔有些想起來似的再次看了季臨一眼:「這樣說來,還是需要麻煩律師的,我們可以提供原件給公司,蔡總讓律師按照一模一樣的再準備一份,我們都補簽了就行了。」
對方說完,就朝邊年輕的男子看了眼,那年輕男人立刻開啟了隨攜帶的包,把一堆檔案遞給了季臨:「這幾天我們也開會表決了,然後把大家自己儲存的那份勞合同都收齊了,先給到公司,律師就可以先去準備了。」
如果說開始探討方案尚且存在勞者以和解為幌子騙取公司信任的可能,那如今這個舉,就完完全全能表明這些勞者的態度了。
季臨拿過檔案翻了翻,又和蔡銘確認了下,這確實是此前真實的勞合同,而對方把這些原件給公司,就是完全放棄了利用沒有勞合同而可以主張雙倍工資的這條路……
「還有現在拖著沒發的工資,我們也不要讓公司再賠錢或者罰款,隻要拿到我們該拿到的就行了。」這中年男人說完,又拿出了另一份檔案遞給了季臨。
這是一份完全手寫的協議,下麵歪歪扭扭的簽了大約百來個名字。
白端端湊過去看了眼,纔看清這份協議是什麼容。
這是一份所有員工的聯名申明,出自工會,白紙黑字寫明瞭經過工會討論,全員工同意公司拖延支付工資的決定,並且放棄追究公司為此造的經濟補償金。
這是一份文字非常簡單甚至沒有什麼措辭可言的宣告,寥寥幾句話,下麵則是工會的蓋章和所有員工的簽名,而因為簽名的人數太多,這一頁甚至本簽不完,季臨把這頁紙翻過來,才發現背後也麻麻都是字型不一的簽名。
季臨白端端和蔡銘嚴陣以待,甚至一直抱著遲疑的態度等著員工代表們給自己挖坑,然而等來等去,千算萬算沒想到等來的這樣一個結果。
這些員工代表本沒給季臨發揮的機會,他們主而坦白地亮出了自己的所有底牌——他們並不想追究公司的責任。
甚至完全正相反,他們想站在公司的邊,陪伴公司度過困境。
季臨看著自己手裡這份宣告,沉默了片刻,才抬起了頭,他的眼睛裡是真實的迷茫和不解,白端端聽到他問,為什麼。
是啊,為什麼,就算問心有愧不給公司潑髒水汙衊公司沒有簽訂書麵勞合同而主張雙倍工資,但公司延遲發放本月工資有拖欠行為卻是真,這些勞者完完全全可以要求公司立刻支付並且給予一定額度的經濟補償金。
猜你喜歡
-
完結36 章

愛你不為人知
他曾說會照顧她一生一世,不離不棄,卻又在婚後翻臉,冷漠以待。 她懷孕,他要打掉。 他說,娶你隻是因為你的家產,不離婚,也是因為你的家產,其實我早就受夠你了。 她被困大火,命懸一線,他卻轉身摟著情婦腰肢,眼睜睜看著她葬身火腹……
4.4萬字8.09 20877 -
完結3045 章

天價萌妻:厲少的33日戀人
他是歐洲金融市場龍頭厲家三少爺厲爵風,而她隻是一個落魄千金,跑跑新聞的小狗仔顧小艾。他們本不該有交集,所以她包袱款款走得瀟灑。惡魔總裁大怒,“女人,想逃?先把我的心留下!”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遊戲,誰先動情誰輸,她輸不起,唯一能守住的隻有自己的心。
236.6萬字8 22964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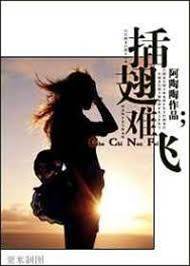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69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