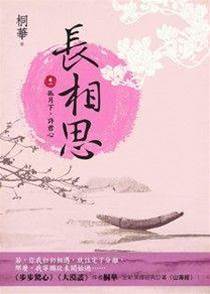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長門好細腰》 第565章 迷局定局
宮里的詔書到達裴府時,裴獗剛剛服下一碗湯藥,平躺下去。
閻王殿里走了一遭,他上的丘疹風團未散,面蒼白,發紺,一直冷汗涔涔。
隔著層層裳,馮蘊也能察覺到他劇烈的心跳,以及極力的克制。
低頭看去。
“大王可好了些?”
裴獗嗯聲,沒有說話。
馮蘊道:“宮里的圣旨,只怕是為了試探你,是不是當真無恙……”
裴獗抬眼,眉頭蹙起。
馮蘊看他的樣子,“傳旨的公公在外面。你且休息,我去應付便是。”
剛要轉,被裴獗拉住手,拽了回來。他握住的手不放,凝視著,聲音沙啞地吩咐門外的左仲。
“就說我歇下了。讓他將圣旨呈上來。”
馮蘊一怔。
這話說得平靜,可字字重錘。
當臣子的如何能狂妄至此?
除非,他不想再當臣子了。
馮蘊抿不語,慢慢坐在他側。
左仲下去了。
回來的時候,帶來一個傳旨的侍。侍沒有進門,就在庭院里,念誦了皇帝的禪位詔書。
皇帝曰:
“朕以菲薄之才,天明命,承祖宗之業,冀以安邦定國,福澤蒼生。然疾病纏,力日竭,深力不從心,恐難擔重任,執掌乾坤。今觀雍懷王仁德兼備,智勇超群,實乃天命所歸,人心所向。
朕思量再三,茲禪位于雍懷王裴獗,以承天運,主理國事,統四方。能恪守天道,興邦安民,使國運昌隆,百姓安居。
朕退意已決,即日起,不再干預朝政,惟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共襄盛舉,同太平。欽此!”
Advertisement
四下肅靜。
圣旨念完許久,都沒有聲音。
馮蘊低頭,看著裴獗平靜的眼睛。
“大王如何想?”
裴獗目灼灼凝視著。
“拒了。”
馮蘊微笑,沒有意外。
“好。”
今日政和殿里,臣子上奏,裴獗拒了一次。
如今皇帝將禪讓詔書送到家里,也得再次推拒。
因為在大眾的心里,自古禪位和篡位,并無差別。
沒有什麼天命移轉,只有權勢的傾斜,和不得已為之。
這個時候裴獗要是欣然接下詔書,那就是有不臣之心,總歸會拿話給旁人說,后世也要脊梁骨。
推拒幾次,才可彰顯清白。
“不過這詔書來得甚好。”馮蘊角微抿,意有所指地道:“大王正好以避嫌為由,在府里休養幾日,誰來也不見。”
裴獗哼笑,“機靈。”
“多謝夸贊。”馮蘊眨眨眼,看他氣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不是太好,不再多說了。
“我下去把他打發了。”
裴獗微微點頭,“辛苦蘊娘。”
“不辛苦,應該的。”
為他的妻子,或是王府長史,這都是馮蘊應當應分的事。
安地了裴獗的手,又叮囑了姚儒幾句,徑直打了簾子出去。
公公沒得到回應,還在庭院里等候,張,彷徨,手足無措。
馮蘊笑著將人請到花廳。
奉了好茶,又讓小滿塞了個錢袋,微笑道:“公公,陛下一片好意,大王卻甚為惶恐。這回,怕是要抗旨不遵了……”
Advertisement
傳旨公公尷尬地看著馮蘊,拭了拭腦門的冷汗。
面前的人哪里是雍懷王妃啊。
一旦接下詔書,那就是母儀天下的皇后娘娘。
公公不敢直視馮蘊的眼睛,小心翼翼地低頭告罪。
“請王妃容雜家說句掏心窩子的話,這一紙詔書,是陛下心意所致,大王還是萬莫辜負得好。”
“唉。”馮蘊看他說得實在,也做出一副為難的樣子,輕輕嘆息道:
“這陣子,大王都要被坊間的流言和唾沫給淹沒了。那些說法,哪個忠肝義膽的臣子承得住?公公,這詔書,大王是萬萬接不得的,不然,這謀逆篡位的罪名,就坐實了啊。”
公公臉更是窘迫。
“這,這也不是雜家能做得主的……詔書傳到裴府,大王領旨,此事便算是了。”
“不了。”馮蘊笑了一聲,溫和地看著他,“九五至尊之位,可不是兒戲,勞煩公公轉告陛下,當真有心恤臣子,便不要再說這等話了,省得讓大王為難。”
公公看著的笑,心思微。
“雜家明白了。”
他點點頭,收了東西,朝馮蘊一笑。
“雜家這便告辭回宮,將王妃的話,一字不地回稟陛下。”
馮蘊朝他欠,好似松了口氣。
“有勞,公公慢行。”
公公還禮,出門自去了。
馮蘊一席話點到為止,這公公卻聽了個明白。
這麼傳一道圣旨來,就要讓雍懷王接位,也未必太過兒戲了。讓裴獗自己拿著圣旨去金鑾殿坐龍椅,何異于宮?
裴獗要的,不僅是皇帝位。
Advertisement
還是明正大的皇帝位。
-
長公主在明殿里來回踱步,神焦灼。
文治帝倒是坦然,寫完那封詔書,他
便輕松了一半。此刻,他要做的,就是等著,看裴獗如何理。
“陛下,懷仁回來了。”
文治帝連忙從榻上坐起。
“快傳。”
懷仁便是那傳旨的侍,是文治帝從潛邸里帶出來的人,深知他的脾。
進屋一看長公主也在,懷仁公公怔了怔,方才分別行禮。
然后,稟報裴府的事。
文治帝一聽,吃驚不已。
“雍懷王不?連皇位都不要?”
他的意外,長公主沒有半點意外。
在意的是,“裴獗沒有出來接旨?一直不曾面?”
懷仁應聲,“是。出來的是雍懷王妃。”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果然。果然是他。”
文治帝看著灼人的眼眸,張道:“皇姊,這可如何是好?雍懷王不肯,會不會……會不會還有別的圖謀?”
長公主猛地轉頭,死死盯住他。
文治帝嚇一跳,“皇姊……”
長公主道:“千不該,萬不該,就你不該寫下那道禪位詔書啊。如此一來,時局于你我,便如臨深淵了。”
文治帝眉頭深皺,“我不明白……”
長公主嘆息一聲,坐下來緩緩地道:“詔書一發,裴獗接不接旨,滿朝文武、王公大臣的心,就算是散了……人心一散,敗局也就定了。”
文治帝抿了抿,“皇姊,我以為,朝臣的心,早就散了。敗局也早已定下。不然今日政和殿上,阮溥豈會是那般下場?”
Advertisement
長公主一怔。
注視著自己窩囊的弟弟,沒有說話。
文治帝不知在想什麼,幽幽一嘆。
“這陣子我在殿中養病,倒是想了許多事。這江山,這天下,這皇位,從古到今,更替頻繁,從不是萬年不變的。每每改朝換代,無一不是尸橫遍野,白骨累累……皇姊,既然大局已定,掙扎也無用,何不保全自?”
他認真地看著長公主。
見不語,又徐徐說道:“歷史多為勝者頌。為抗爭而死,史書只會留下罵名。茍且生,說不定還能千古流芳,博得一個慧眼識人的譽。”
長公主冷哼。
文治帝看出臉松緩了些。
又道:“一個好皇帝,當以天下子民,蒼生福禍著想,倘若我將皇位托付給一個可以振興大晉的人,這豈不是做的功德?祖宗泉下有靈,想必也不想基業敗于我手……”
“皇帝。”長公主看著他一副不爭氣的慫樣,千方百計的為弱找借口,眉心皺起,再散不開。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你我了。”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
不得不說,長公主料事如神。
一紙毫無預兆的禪位詔書,就如同一瓢冷水澆在熱油上,在西京朝堂炸開了鍋。
朝臣們沒有料到,皇帝會自作主張將皇位拱手于人。
此舉,對一些心存僥幸,還對皇帝抱有希的臣子可謂是一記重錘,瞬間將人推向了另一邊。
整個大晉朝堂,態度空前一致。
——元氏皇朝氣數已盡。
別說裴獗未必肯扶他,就算裴獗無心稱帝,想將這位稱病不肯上朝的皇帝扶上龍椅,只怕也會自己栽下來。
與其如此,何不順勢而為?
眾人生怕去得晚了,趕不上熱乎的,從那天晚上開始,裴府便門庭若市,來來去去的馬車,文武百,或相約,或單獨,前來勸諫雍懷王,接圣旨、即大位。
理所當然的,雍懷王為了避嫌,閉門謝客。
滿朝王公,一個都不見,就連敖政,都被府里謝絕了。
事仿佛陷了膠著。
朝野上下,風云變,只有裴府里,庭院春深,一派祥和氣氛。
十日后,裴獗的病已然大好。
外間關于皇帝禪讓的消息越傳越遠,消息擴散出去,天底下,無人不知。
裴媛托人來問過好幾次了,就連久不問政事的裴沖,都有些按捺不住,急切地想要裴獗給一顆定心丸。
裴媛當然是喜歡,覺得門楣生,大有作為。
裴沖當然是不肯,認為裴府滿門忠烈,當護大晉江山,而不是自己登基為帝,落一個臣賊子的罵名。
每個人都想要一個結果,塵埃落定。
就連府里掃地的小廝都著急了。
唯獨裴獗和馮蘊好像沒事人似的,一個閑看落花,一個青梅煮酒,高興了便對弈一局,兩個人的比任何時候都好,相也極是愜意。
“娘子,仆都要急瘋了……”
馮蘊問:“怎麼了?”
小滿這幾日聽了太多流言,角都長出了水泡。
嘟起,撒般輕哼,“你說呢?”
馮蘊笑而不答。
夕西下,在屋檐的瑞上灑下一層金。
在更遠的天邊,一遠月已朦朧的升起。
日月同在,芒空蒙,淡淡地落在馮蘊的襟上,襯得眉眼俏麗過人。
小滿看得有些呆了。
半晌,才回過神來,一邊沖茶水,一邊看向靜心觀棋的裴獗,小聲問:
“大王到底要怎麼辦啊?”
馮蘊輕笑,平靜地道出一個字。
“等。”
猜你喜歡
-
連載550 章
病嬌掌心寵:四個反派哥哥也重生了
【甜寵+虐渣+重生+病嬌+馬甲+女寵男+雙潔+哥哥團寵】重生而來的顧笙。不是在虐渣就是走在虐渣的路上。身後跟著四個追妹火葬場的哥哥。天天裝可愛的求她的原諒。卻眼巴巴的看著自己的妹妹,將那個病嬌偏執的男人寵上了天,他們雙眼羨慕嫉妒恨。“笙笙,大哥哥也要抱抱舉高高……”“笙笙,二哥哥身嬌體軟很容易舉高高……”“笙笙,三哥哥比他們都強!”“笙笙,四哥哥最小,你要疼四哥哥!”他們變著法子爭寵,卻冇有看見,有一雙墨黑的眼眸正盯著他們,彷彿潛伏的狼,下一秒就要將他們給撕碎,看的幾個人害怕的瑟瑟發抖求抱抱。結果卻看見自己的妹妹,笑意盈盈的將偏執可怕的男人擁入了懷裡麵。“乖,我最疼阿淵。”被擁入懷裡麵的男人。緋紅的眼角勾著得意,衝著身後羨慕的幾個男人洋洋得意的一哼,身嬌體軟的享受著。
125.3萬字8 38698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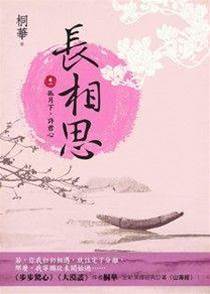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9 -
完結1427 章

玄學王妃算卦靈,禁欲殘王寵上癮
末世玄學巨擘南璃一睜眼,成了安陽侯府走丟多年的六小姐。以為是受虐劇本,誰知五個哥哥一個比一個寵她!南璃大喊別寵了,其實妹妹超能打,捉鬼除妖算卦看相看風水,治病救人樣樣精通,帶領家人升官發財!一不小心救下的九王爺,權傾朝野,是出了名的冰冷寡情,更是獨寵她上癮,不肯納妾。綠茶白蓮怒喊:“王爺子嗣單薄,怎麼能行?!”南璃指著排成一隊的捉鬼小崽崽們:“眼睛不好我給你治!”’九王爺將她抱起來:“
249.6萬字8.18 1258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