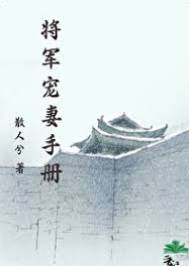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看到彈幕后和病弱太子HE了》 第268頁
說著說著,他突然注意到,元容一開始褪下的子,不知何時又被穿了回去。
方才將那假的顧休休扔下去的時候,元容若是并不知此事,在傷心絕之時,又怎會有時間想起來把子提上?
西燕君主頓了一下,笑容僵住:“原來你一早就知道了此事,卻還愿意為了繼續演下去……”
他嘔出一口來,疼得渾發,聽到顧休休冷笑了一聲:“你用換蠱騙了我數次,先是我大哥顧懷瑜,又是元容,還有謝懷安。我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便了心機深沉,那你又算什麼?”
“瞧你那狗急跳墻,挑撥離間的模樣,我一早就讓人去了驛站,將此事告訴了元容。”
是了,顧休休去找謝懷安之前,便讓顧月稍作喬裝打扮,先他們一步進了燕都,到驛站給元容送信去了。
但元容的演技實在是太好了,方才一打開蛇窟的門,看到他赤著跪在地上,將顧休休嚇了一跳,忍不住愣了愣。
甚至有一瞬間在懷疑,元容沒有收到顧月送的信。以防萬一,從元容邊肩而過時,從地上順腳往前一踢,仿佛不經意般,將那顆石子踢到了元容旁,以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的扔石子來提醒元容。
Advertisement
剛剛沒機會跟元容說話,現在終于擒住了西燕君主,那一劍下去,他此時已是沒有了威脅,還能活著全憑著那續命蠱,半死不活吊著一口氣茍延殘。
至于那西燕國師,他沒什麼武功,顧休休方才進來蛇窟前,便頂著那張太監羅一的臉,將其騙到了金屋殿,三兩下就被顧懷瑜擒住,與羅一一起吊在金屋殿的房梁上。
他們兩人皆是西燕君主的走狗心腹,往日幫著西燕君主不知殘害了多無辜年,先前在元容為質的那三年,更是對他百般欺辱。
顧休休讓顧懷瑜挑斷了羅一和西燕國師的手腳筋,又給他們也喂食了續命蠱,如今也是了生不生,死不死的廢人。
等顧懷瑜將驃騎將軍救出暗室,西燕君主便也失去了利用價值,只等元容對他們親手做個了結。
顧休休服下換蠱的解藥,變回自己的容貌,越過滿地侍衛的尸,將視線從西燕君主上,轉到了元容上。
他渾冰冷,手上的銀劍上沾滿了黏稠的,一滴滴沿著劍刃向下淌落。
烏黑的青流瀉在肩后,略顯病態的臉龐上迸濺了殷紅的,襯得他皮更白,那雙黑眸也更深了些。
Advertisement
顧休休像是沒有看到他上的,大步跑向了他,用力撞進了他的懷里,雙臂環在他的頸上。
踮起腳,埋著頭,輕聲問:“長卿,你見到我阿姐了嗎?”
元容低低應了一聲:“嗯。”
顧休休想起方才進到蛇窟里時,看到的那一幕,眼睛倏忽一下就潤了:“對不起……”
就算元容清楚蛇窟里掛著的人是津渡而不是,卻還是為了給爭取時間,對于西燕君主近乎侮辱人格的命令言聽計從。
寬大冰冷的掌心落在的腦后,輕輕拍了兩下:“說什麼對不起,能救出他們,了結我畢生的心愿,此生足矣。”
兩人的對話被倒在蛇窟石欄下的謝懷安打斷,他捂著生疼的小腹,蜷著一條,有些痛苦道:“顧休休,你們等會再煽,你現在是不是應該先跟我解釋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們一共就四個人,顧休休、顧懷瑜、津渡還有他謝懷安,他們從始至終都沒有去過驛站,到底是誰跟元容通的風,報的信?
顧休休也沒有跟他提及過,這中間還有變羅一這一茬,更沒有告訴他,津渡會蛇,掉進蛇窟里也不會死。
Advertisement
明明謝懷安也參與進了這個計劃,可如今計劃功了,他卻像是被蒙在鼓里的傻子似的,他們都不知道剛剛津渡掉進蛇窟里,他的心跳都嚇得驟停了。
顧休休抬了抬腦袋,看向氣急敗壞的謝懷安:“過程不重要,結局才重要,你說是不是,太常大人?”
顧月畢竟是假死出宮,雖然謝懷安幫了很多,但還不至于因此就忘記了,謝懷安是謝家下一任家主,更是北魏九卿之首的謝太常。
顧家與謝家算不得對立,卻也極來往,才不會因為一點小恩小惠,就將顧月的事告訴謝懷安,讓謝懷安拿住顧家的把柄。
至于津渡不怕蛇,以及要扮作羅一的事,不說是因為謝懷安沒有問,而且任務這麼繁瑣復雜,時間又那麼迫,哪有那麼多時間一一解釋。
見顧休休不準備多說,謝懷安卻沒有想要這般輕松放過的意思。
他正要說些什麼,只聽見‘當啷’一聲響,元容握在手中的劍柄掉在了地上,整個人像是虛了一般,朝著地上直直栽去。
顧休休下意識手接住他的,卻抵不住那的重量猛地砸過來,跟著他一起摔了過去。
Advertisement
元容沒能像是先前從謝家離開后,冒雨送顧休休回到玉軒,卻因力不支,與一同摔過去的那次一樣,即便摔下去,還不忘護住的腦袋。
這一次,他已經完全失去了意識,就連顧休休爬起來后,慌得掉出眼淚,一聲聲喚著他的名字,他都毫無反應。
津渡走過來,蹲在元容邊,了他的脈搏:“沒死,別哭了。”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59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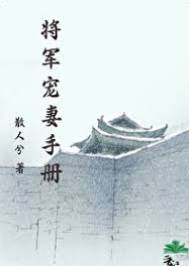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12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