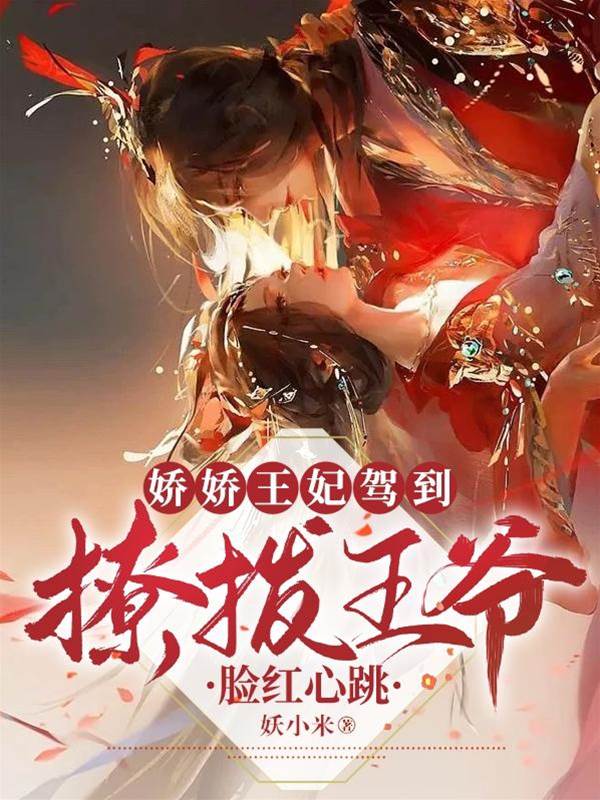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春滿酥衣》 分卷閱讀148
在閱讀其中一本自通城買來的書籍時,他發現了一樁很是蹊蹺的事。
晨徹底明了,日影鋪撒向大地,將西疆照耀得一片生機。
酈也循著那日影、循著沈頃的眼神,目落在信紙上。
“明安三年?”
酈記得,大凜明安三年,正是沈頃出生的那一年。
明安三年發生了何事?
沈蘭蘅讀書卷,看到——
明安二年至明安三年,京中無端夭折諸多新生兒。而這些夭折的新生兒中,大多都為雙生子。
或許是那“明安三年”的字眼到了他,又或許是那一句“雙生子”,沈頃攥著信紙的手微微發,目稍頓片刻,而後再朝下讀去。
信中,沈蘭蘅道。對此事,他亦十分好奇,便查閱了那一年大凜的相關記載。
蹊蹺的是,在明安二年至明安三年間,大凜既沒有天災,又沒有戰。
唯一記載離奇的,便是明安初年時的那一場幻日。
幻日之後,大凜大旱一整年。
那一整年,大凜不見一滴雨雪。
對於明安初年的這一場大旱,沈頃也有所耳聞。
自那場幻日過後,大凜各地便接連出現了旱事,城池州郡,最後甚至連京都也了那等幹旱之地。
Advertisement
幹旱持續了一整年,來年開春,京都終於迎來了一場救命雨。
看著前之人漸蹙起的雙眉,酈問道:“郎君,有何異常?”
有何異常?
全都是異常。
他先前也翻閱過史書。
那時候,他便覺得——這浩瀚的史書記載中,似乎缺了些什麽。
究竟是缺什麽?
他也說不上來。
日影漸明,沈頃雙手攥著那信件,卻覺到似乎有什麽片段,在史書中蒙塵。
酈與他一樣,想起先前那一出《雙生折》。
先前宋識音曾與提到,蘇墨寅所著的《雙生折》,便是以明安二年至明安三年為原型,一兩魄,亡靈轉生。
“可否要問一問蘇墨寅?”
這廂話音剛落,酈又歎道,“罷了,如今他定是不想見任何人。”
不蘇墨寅不想見,同樣的,也不想去見蘇墨寅。
近些天發生的事,已讓酈對他有了很大的改觀。
沈頃頷首,明白的意思,輕輕“嗯”了一聲。
一想起蘇墨寅,便想起來如今正臥床的宋識音,一想起宋識音,酈的心不免有些低沉。
沈頃拍了拍的肩,說過幾日通城會有一場集市,到時帶前去散散心。
Advertisement
握著他的手,婉婉應“是”。
關於書信上所言的那些蹊蹺點,沈頃著手去查。
因是事關重大,他不敢再用旁人,就連魏恪長襄夫人都未告知,手把手地調查起此事。
酈跟著他,去通城買了諸多相關的書籍。
不止是沈頃,酈也約覺得——這件事,似乎與沈蘭蘅的“出現”、與二人的一兩魄,有著極大的關聯。
沈頃本問蘇墨寅關乎《雙生折》與《上古邪》之事。
奈何對方一直跪在宋識音帳前,苦苦哀求,祈求著對方的原諒。
無論他如何求,甚至在帳外磕頭磕出了,宋識音仍不為所。回答蘇墨寅的向來都是那一方冷冰冰的軍帳,與帳簾外,那呼嘯而過的冷風。
宋識音不願見他。
說過,此生此世,都不願再見到他。
當這句話傳沈頃耳中時,男人翻書的手指一頓,他並未替好友歎惋,而是淡淡道:
“是他自作自。”
當然是他蘇墨寅自作自。
不過短短幾日,蘇墨寅便如同一丟了魂兒般的行走。男人無神的兩眼凹陷下去,眼瞼盡是一片烏青。整個人更是瘦得宛若一張薄紙,風一吹便要倒。
Advertisement
蘇墨寅還未理好與宋識音的事,自然也沒有閑心去顧及其他。
沈頃也不便再去麻煩他,而是帶著酈與沈蘭蘅,去翻閱各種史書典籍,去探尋在這明安二年至三年間,究竟發生了何事。
時間一天天過去,西疆也一日日回暖。
沈頃與沈蘭蘅之間的書信往來,從未有一日停歇。
宋識音亦獨在軍帳中休養,並未再理會蘇墨寅。
直到一日——
便就在酈幾乎要放棄搜尋當年之事時,一個不起眼的話本子,就這般闖了的視線。
心灰意冷,隨意翻開。
誰知,眼第一句,便讓手指一頓。
片刻之後,激地喚道:
“郎君——”
彼時沈頃正在軍帳裏另一張書桌旁,聞言,男人的眼皮跳了一跳,趕忙抬頭:“發現什麽了?”
毫無征兆的,二人心跳忽然加速。
酈捧著那本不起眼的話本子,掌心竟有些發熱。
“郎君,你快來看。”
沈頃闊步,不過頃刻便走至妻子側,迎麵撲來那陣悉的馨香,正是妻子上獨有的味道。
那是一陣花香。
不知那香氣是從上還是發上傳來,花香盈盈,甜津津的,卻不膩人。
Advertisement
外間春意愈濃,影斑駁,落在這一方略微厚實的軍帳之上。
循著影,沈頃低下頭。目跟著妻子蔥白如玉的手指,閱讀著話本上的文字。
——明安初年,皇宮。
容皇後與胡貴妃,接連懷有孕。
話說這容皇後和這胡貴妃,乃是一母同胞的孿生姐妹。二人甚篤,又極得聖心。聖上自然大喜,宮中設宴七日,載歌載舞,未有一刻停歇。
這本該是一件雙喜臨門之事,二人臨盆時又恰恰撞在了一起。那日宮中忙碌萬分,皇帝更是守在儀宮外,期待著嫡皇子的誕生。
可誰曾想,便是在這日,便是在二人皆臨盆這日。
大凜出現了幻日奇觀。
九天之上,懸有兩紅日,金燦燦,灼烈人。
宮中一片嘩然。
而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更是令整個皇宮,不,令整個大凜,都陷一片惶恐不安。
容皇後誕下雙生子後,母子三人俱亡。
接著,胡貴妃竟誕下一死胎,本陷悲痛之中的皇帝大驚失,當晚,竟將貴妃胡氏以“不詳”之名打冷宮。
接著,大凜幹旱一年。
國師言此異兆,乃胡氏雙生所至,皇帝心中懼之,下令,此後大凜不允許再出現雙生子。
看到這裏時,酈已然神,雙目低垂著,瞧著書卷上那些平靜而殘忍的字眼,下意識喃喃:
“大凜明安二年,皇帝下令:如若出現孿生胎兒,需立馬殺死……”
此言罷,酈心中“咯噔”一跳,猛地抬頭。
猜你喜歡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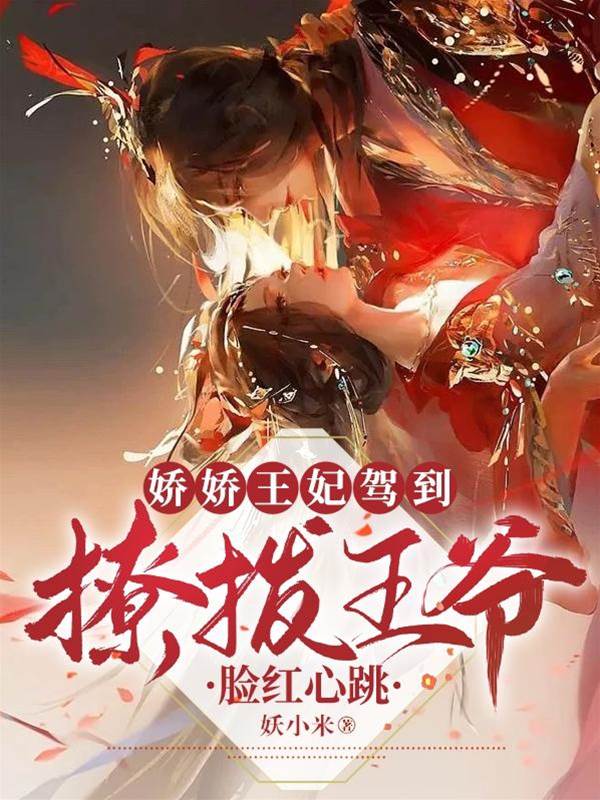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98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882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89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