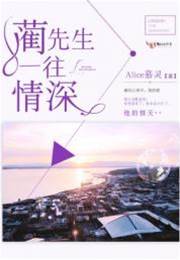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團寵:七個哥哥又爆我馬甲》 第904章 蘇佑受傷
“,佑哥傷了,現在楠哥的醫院做手。你什麽時候回來?”
“什麽?!我,我的飛機馬上就起飛了!我很快就回來。怎麽回事,這,怎麽會這樣?”蘇語無倫次地說著,眼眶裏立刻就盈滿了淚水。
恰好這時,登機廣播響起。
“我要進安檢了,馬上就來。”蘇匆忙掛斷電話。
“怎麽了?發生什麽事了,,別著急。”宋千俞用力握著的手臂,給力量。
“佑哥傷了在醫院做手。”蘇帶著哭腔說道。
“我跟你一起回去。”宋千俞說完,立刻聯絡自己的助理:“聯係航空公司給我加個位置,就現在正要登機的航班。”
蘇:“可是這裏還有一堆爛攤子要你收拾,宋家……”
“讓老家夥出山頂一頂。”宋千俞用手揩去眼角的淚水,道:“反正我惡名在外,是個無法無天的爺,臨時撂挑子也是正常。”
Advertisement
蘇含著眼淚,苦地笑了一下,一把鑽進他懷裏。
還好宋千俞在。
經曆過三五個小時的難熬飛行時間,兩人落地之後風馳電掣地趕往醫院。
蘇佑已經做完手在病房。
蘇跟宋千俞闖進去的時候,一病房的人被突然開門的靜嚇了一跳,紛紛看向。
房間裏隻有周越霖、陳亦楠和謝禹。
楚堯在部隊,葉星冉在外地,蘇辭事務纏,晚些時候才能來。
蘇提心吊膽地跑到病床邊,看到蘇佑好端端地坐在床上,左臂打了石膏掛在脖子上。
除了臉上有些傷,其他的好像一切都好,並沒有想象中病重的樣子。
蘇佑跟眼睛紅紅的蘇對視了好一陣,忽然咆哮道:“周越霖!你他媽怎麽跟說的!”
Advertisement
周越霖瞪著眼睛,無辜道:“我就說你在楠哥的醫院做手,問什麽時候能回來……”
陳亦楠:“沒了?”
周越霖:“沒了啊,還要什麽?”
就連謝禹都忍不住扶額:“蘇佑傷勢不重,你應該再說一句讓不用擔心,隻是傷筋骨。不說的話,會往壞想。”
“啊?……啊!”
一隻黃的香蕉甩過來,狠狠命中周越霖茸茸空的腦袋。
蘇佑:“你這不是咒老子死嗎!”
“噗呲。”蘇破涕為笑:“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安靜下來後,蘇才搞清蘇佑的傷勢。
他是左臂小臂骨折,因為碎地有些厲害,需要開刀把骨頭渣子整好。
其他的都是皮外傷,沒什麽。
不過他的幾個弟兄們還在醫院別的病房呢,看來是一場頗為激烈的群架。
蘇問他:“怎麽會搞這樣?”
“鐵子朝我頭打過來,來不及防了,隻能用手臂擋一下,就斷了。”
蘇佑說得輕鬆,但想也知道當時況多麽混而危險。
而他半遮半掩的解釋讓蘇有所察覺:“佑哥,是不是緬國毒梟的手又過來了?”
蘇佑被道破,隻好點了點頭。
蘇得到回答,轉看了眼病房沙發上的宋千俞。
目對接,一些決定不用通便已能互相知曉。
猜你喜歡
-
連載1164 章
穿到跟殘疾大佬離婚前
遲清洛穿進一本狗血小說,成了商界殘疾大佬作天作地的小嬌妻。小嬌妻驕縱任性,飛揚跋扈,還紅杏出牆。遲清洛穿來當天,原主正因為爬了娛樂圈太子爺的床上了熱搜。大佬丈夫終於同意跟她離婚。遲清洛:“老公我愛你,之前跟你提離婚是我一時糊塗。”輪椅上的大佬眸色深沉:“你糊塗了很多次。”不不,從今開始,她要改邪歸正,渣女回頭金不換。可是漸漸的大佬好像變得不一樣了,對她說抱就抱,說親就親。嗯?大佬不是淡薄情愛,隻把她當擺設的麼?遲清洛眨眨眼:“好像有哪裡不對。”大佬將小嬌妻圈入懷中,指腹摩擦著她的唇珠,聲音嘶啞:“哪裡不對?”
104.7萬字8 56328 -
完結845 章

寵婚入骨
許家多年前送去鄉下養病的女兒許呦呦回來了,回來履行與林家的婚約婚禮前夕新郎逃婚去國外找他的白月光,眾人:哇哦……【吃瓜表情】許呦呦:哦豁。下一秒,白皙細軟的小手攥住男人的衣袖,甜糯糯的語調:“墨先生,您可以娶我嗎?”……墨深白商業巨擘清心寡欲,神秘低調,在波雲詭譎的商場叱吒十年,無一家報刊雜誌敢刊登他的一張照片,也沒有一個異性能讓他多看一眼。所有人都說墨深白娶許呦呦一定是協議婚姻,一年後絕對離婚。許呦呦津津有味的吃著自己的瓜,只是吃著吃著就發現好像不對勁啊。逛街購物不需要買單,吃飯不用點餐,不管走到哪里大家熱情跟她打招呼:墨太太好。後來墨深白的白月光回來了,前未婚夫深情表白:“呦呦,只有我是真的愛你,回我身邊,我不嫌棄你。”許呦呦還沒來得及回答被男人霸道的攬入懷中,低音性感撩人:“寶貝,你沒告訴他,這裡有了我們愛的結晶。”溫熱的大掌貼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許呦呦紅了臉,渣男紅了眼……【無腦瑪麗蘇先婚後愛文|專注虐男二】
142.9萬字8.18 230570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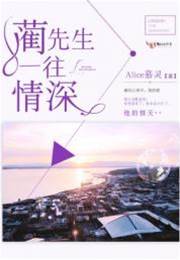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78510 -
完結855 章

報告總裁,你老婆又跑了
黑暗中,他鉗住她的下巴,“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她自輕自賤“知道名字又如何?你只要一分不少的把錢打到我卡上就行了。” 本以為拿到錢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當一切沒有發生。 誰知那古怪男人從此卻陰魂不散的纏住了她。
167.7萬字8 38184 -
連載176 章

軍婚撩人:首長大人請深吻
她代替姐姐嫁給了那個據說身有隱疾的年輕軍長。他的寵,他的溫柔霸道,讓她毫無抵抗的臣服。卻原來爾婚我詐,不過是一段遠的要命的愛情。幾年後,她攜子歸來,撩撥的他欲火焚身。他反身把她壓在辦公桌上,“老婆,按照一夜七次的頻率來算,你已經欠我很多了,要不咱們還是先還債吧!”
30.5萬字8 262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