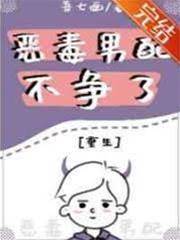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小娇妻怼天怼地怼霸总》 第2章:這是一場謀殺
云朵在飄飛,云薇暖與孩子似乎也在飛。
睜眼,竟然看到了手室外,自己的丈夫梁辰正抱著自己的閨兼室友黃麗婧在調。
“小妖,咱們別等著了,去病房里讓我親親你,你我,我都忍不住了!”
梁辰抓著黃麗婧的手,不住往自己的腰帶位置按去。
黃麗婧一臉,“你這壞蛋!暖暖還在手室里呢!好歹等到手功的消息唄。”
“當初我就是想玩玩而已,誰知道第一次竟然就懷孕了,以死相,我只能娶了,真是晦氣!”
梁辰一臉的不屑和厭煩,仿佛云薇暖與他無關,仿佛云薇暖腹中的孩子也與他無關。
“幸好你有人,提前查出肚子里是個孩兒,哼,我們梁家五代單傳,第一胎肯定是要生個男孩的。”
梁辰著黃麗婧的手,臉上都是,哪里還記得自己妻子在手室里生死未卜。
Advertisement
黃麗婧一臉的:“壞人,昨天你在自習室欺負我,都沒戴那個呢,萬一人家懷孕了怎麼辦?”
“懷孕?今晚咱倆繼續,以后,每個周六都在行知樓的小自習室里玩點刺激的?我有自習室鑰匙。”
云薇暖聽到這話,絕閉上了眼睛。
原來是這樣啊,原來一切都是最好的朋友與過的丈夫合謀起來的。
他們這對夫婦,背著早就在一起了,還合謀將送上了手臺,合謀殺死的孩子,畜生!都是畜生!
“云薇暖的家屬!云薇暖發生了產后大出,你們還是盡快將送到大醫院吧!”
醫生雙手是奔了出來,也是一臉的慌和恐懼,只是想賺錢,可不想殺人啊!
梁辰和黃麗婧對視了一眼,片刻,梁辰揮揮手,一臉的無所謂。
“送大醫院?連個兒子都生不出來的人,留著做什麼?值得我花那份錢?”
Advertisement
黃麗婧佯裝一臉痛心,伏在梁辰懷中聲說道:“暖暖死了沒關系,我會替照顧好你的,將來,我會給你生孩子的。”
云薇暖看著那對心如蛇蝎的夫婦,只覺得恨意滔天,只恨不得化作地獄修羅,將這些畜生都撕碎片吞腹中。
他們聯手害死了的孩子,這仇,哪怕追到下一世,也要報!
云薇暖在這滔天恨意中,意識逐漸變得模糊,抱了懷中的孩子,讓他小小的軀在前。
“別怕,媽媽會一直陪著你的,不管地獄還是天堂!”
就在云薇暖即將逝去意識的瞬間,忽然看到走廊盡頭奔來一個模糊的人影。
“嬈嬈呢?你們把嬈嬈弄到哪里去了?”
努力睜開眼睛,云薇暖看到一個材修長拔的男人背影,他手里握著一柄刺刀!
梁辰抖若篩糠,“嬈嬈?誰是嬈嬈?我不認識!”
Advertisement
“嬈嬈就是云薇暖!你他媽的再敢說一遍你不認識!”
男人背對著云薇暖,怎麼也看不清楚他的長相。
云薇暖有些犯迷糊,這個男人是誰啊?怎麼對他半點印象都沒有?
還有,這個男人怎麼嬈嬈?的小名暖暖呢!
“壞了壞了,云薇暖停止了心跳!”
兩名護士尖著奔出來,死了,那個人竟然死了!
云薇暖“咦”了聲,竟然死了?那現在這是,靈魂出竅了嗎?
就在這瞬間,只見那手持刺刀的男人,狠狠的,將手里的刺刀在梁辰的腦門上,不偏不倚的,刀刃正好刺他眉心!
梁辰腦漿四濺的同時,云薇暖最后一點意識也像是被什麼走。甚至來不及看清那個男人長什麼樣,就失去了所有意識。
猜你喜歡
-
完結1412 章

網遊:這個劍士有億點猛
江風前世受盡冷暖,重生歸來,憑著前世的記憶,一路崛起,猛地驚天動地! 買了個黑暗封印戒指,恭喜你,獲得傳奇任務:尋找梅賈的竊魂卷!爆了個踏前斬技能書,恭喜你,獲得傳承任務:疾風劍豪的傳承! 救了個生活職業玩家,抱歉,他是未來的匠神!建了個沒人要的封地,抱歉,老子自己建立影城!
255.6萬字8 71464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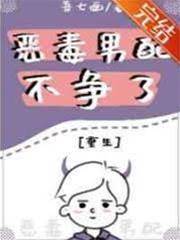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78 章

嬌軟美人[重生]
重生回十九歲,蘇菱發誓,這一世絕不要重蹈覆轍。她要保護家人。進擊娛樂圈。最重要的是,不要被秦驍看上,不做他的嬌軟情人。 秦驍有個秘密,他有點特殊癖好,還喜歡純情嬌怯的美人。直到蘇菱出現,小美人從頭發絲到足尖都符合他的口味。 可惜她厭他入骨。明滅的燈光,他舔舔唇角的傷口,低頭看她怕得要哭的樣子。 秦驍:……臥槽心給你心給你,哭起來都他媽的好看! 【軟萌重生小美人X霸道二世祖】 蘇菱前世最怕他動情時的三句話:菱菱好乖。 菱菱叫得也好聽。 菱菱說愛我。 愛你媽個頭!滾犢子。 1.金手指就是女主美。 2.無邏輯甜寵蘇文,甜是作者以為的甜,讀者覺得的玻璃渣。 3.走劇情改命,可能比較刺激,覺得不刺激我也沒有辦法。女主一開始五毛錢演技,軟萌萌性格,后期慢慢變,能變成什麼樣作者不保證。 4.男主感情不渣,不種馬!看文別誤會,后面會解釋。 5.戀愛小撩文,只為博君一笑,謝扒,謝絕ky。 6.文中所有人物三觀非作者三觀,人物并不完美,也許還有病。可以提意見發表觀點,拒絕人身攻擊。
23.3萬字8 46961 -
完結394 章

神醫毒妃:冷王的心尖寵
前世她被害的毀了容貌和清白,被算計慘死在未央宮外。 重活一世,顧清卿決定要讓這些人血債血償。 首先就是要讓毀她容貌的人自食惡果。 看著顧家徹底亂作一團,顧清卿忍不住笑出聲來,轉身卻被堵在門口。 “成親王,你我不過交易一場各取所需,還望王爺自重。” 歐陽宸聞言看著蕭若云點點頭“是各取所需,眼下你要的已經得到了,本王要的你還沒給呢。” “你要什麼?” 說著欺身上前“本王要你做我的王妃。”
103.8萬字5 51823 -
完結216 章

有嬌來
前世,定遠侯府滿門含冤入獄,身嬌體貴的宋五姑娘在被賣入勾欄紅院的前一晚,得那光風霽月的江世子相助,養於別院一年,只可惜宋五姑娘久病難醫,死在了求助江世子的路上。 【女主篇】 重生後的宋晏寧只想兩件事:一是怎麼保全侯府,二是怎麼拉攏江晝。 傳聞江世子不喜嬌氣的女子,被笑稱爲京都第一嬌的宋晏寧收斂脾氣,每天往跟前湊一點點,極力展現自己生活簡約質樸。 一日,宋晏寧對那清冷如霜雪的男子道:往日都是輕裝簡行,什麼茶葉點心都不曾備,可否跟大人討點茶葉? 後來,江晝意外看到:馬車裏擺着黃花梨造的軟塌,價值千金的白狐毛墊不要錢似兒的鋪在地上,寸錦寸金的雲錦做了幾個小毯被隨意的堆在後頭置物的箱子上...... 宋晏寧:...... 剛立完人設卻馬上被拆穿可如何是好? 清荷宴,宋晏寧醉酒拉住江晝,淚眼朦朧,帶着哽咽的顫意道:我信大人是爲國爲百姓正人的君子......,只想抓住幫助侯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江晝聞言眼底幽深,又些逾矩的用錦帕給人拭淚,看着姑娘因低頭而漏出的纖白脖頸,心裏卻比誰都清楚,他對她可稱不上君子。 世人都道江晝清風霽月,清冷剋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縱容和徐徐圖之......
34.9萬字8.18 105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