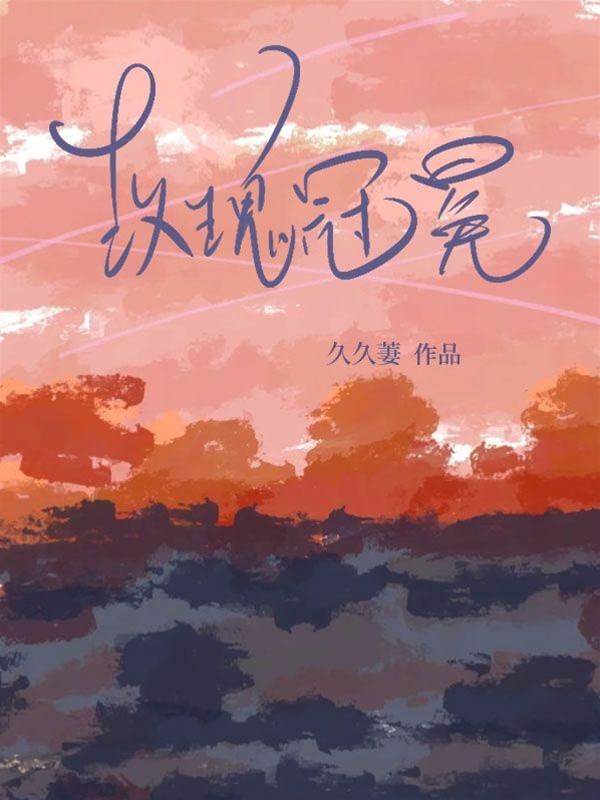《虐愛成癮,他的深情囚籠》 第14章 今晚到我房間來
夏淺了子,想與他保持些距離。怕這男人說不準什麽時候再一次撲過來。
顧墨寒的結上下,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似是意猶未盡的用拇指指腹了自己角。
他瞇著雙眼居高臨下的俯視著眼前的夏淺。
被酒水打的襯衫粘在上,勾勒出一條飽滿的曲線。
上領口被男人撕扯壞的部分,出一條白棉質的肩帶。
那種款式,也隻有一些年紀尚淺的大學生喜歡。
他眼神落在夏淺前的兩團雪白的小兔子上麵。
那兩隻雀躍的小兔子正隨著的呼吸高低起伏。
“倒是長大了不。”
剛才在上吻時,夏淺前的那兩隻小兔子圓滾滾的在他上,他的到外力的,讓原本就一團燥熱的他的更加的難耐。
Advertisement
剛才被那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打斷。
此時的顧墨寒克製著裏的。
他轉下上的外套,重重的向丟了過去。
夏淺這才發現,自己上的服已不遮,前的兩片雪白一覽無餘。
想起剛剛他低著頭看的樣子,的滿臉紅。
於是夏淺慌忙的裹上外套。
夏淺從小就子骨瘦弱,外加一直重男輕,家裏好吃的好玩的全僅著哥哥一人,長大點之後還要幫家裏下地裏幹活,初到顧家時夏淺又矮又瘦,再大一些時顧墨寒便出了國,一年到頭也見不上幾次。
對的印象自然還停留在小時候那瘦瘦小小的模樣。
大學的這幾年裏,倒是各部位都發育了起來,出落得一副模樣。
從小到大,顧墨寒總是經常的捉弄。
Advertisement
這麽多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接過他親手遞過來的服。
外套是顧墨寒從家裏出來時穿的那件,上麵殘留著淡淡的香水味與他裏散發出的荷爾蒙味道。
顧墨寒隻覺得口幹舌燥,他起想找來一瓶水喝,見桌上有一個瓶子便一口灌了下,喝下去才發現是剛才夏淺從酒櫃上拿下來的那瓶40多度的烈酒。
這一口酒下去,裏原來的躁熱不但沒有退去,那團熾熱的火反倒是像一座火山一樣在伺機發。
“你還真會挑酒。”他看著手裏麵的那瓶酒。
“啊?我…我隻是隨便拿的。”夏淺又裹了裹上的服。
不明白此刻顧墨寒的話是什麽意思。
夏淺不懂酒。
隻是在酒櫃上看了半天,選了一瓶覺得瓶子好看的一瓶洋酒。
Advertisement
不是說酒櫃裏麵的酒可以隨便拿嗎,難道是這瓶很貴?貴到賠不起的那種。
顧墨寒吞咽著幹的嚨,熾熱的火在他的裏肆意的湧著:“剛才的事不算,今晚到我房間來。”
“啊?今天不是周末,我…我等下還要回學校。”夏淺輕聲的說。
顧墨寒整理著上的襯衫和領帶。瞥了一眼沙發上的夏淺:“那你就回去試試。”
便。
顧墨寒摔門。
猜你喜歡
-
完結233 章

豪門未婚夫有了讀心術
下一本預收:《重生頂流的隱婚嬌妻》文案在后。本文文案:唐暖是一本甜寵小說里炮灰女配,作為圈子里出了名的草包花瓶,卻有一個頂流豪門的未婚夫。結果未婚夫的初戀女神歸來,直接揭穿了她假千金的身份。她不僅被唐家掃地出門,還會被葉家退婚。眾人都等著看她糾纏葉殊宴的笑話。葉殊宴也這麼覺得,因此準備了足夠的賠償,結果一場意外醒來,他忽然就有了讀心術。還沒搞清楚情況,一個清晰的女聲傳來:【他的讀心術有效范
36.4萬字8 10451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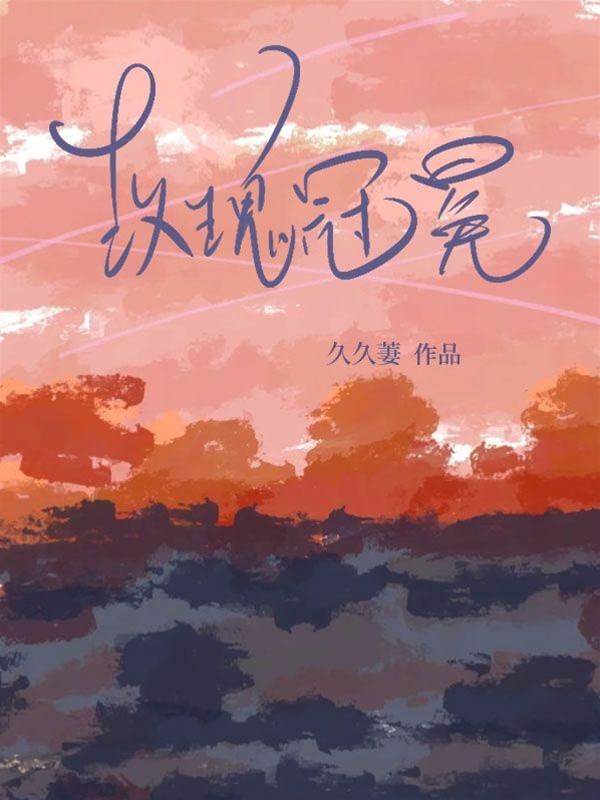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0129 -
連載176 章

偏對你服軟
【宴先生,我想跟著您。】 金絲雀靠這句話,拿下了京港太子爺。 宴先生養的低調,既沒珠寶首飾,也沒金子打造的鳥籠,聊勝於無的這麽養著。 而這隻倒貼的雀兒也不規矩。 愛挑事,心思多。 眾人想著,生於宮闕裏的宴先生心氣那麽高,大抵是不養了。 可誰知,宴先生不僅繼續養著。 還養成了京港最嬌,最媚,最得寵的一位。 直到有一天。 宴先生轉頭護青梅,奉若珍寶,兩個女人在京港鬥了個死去活來。 終是青梅勝利,把金絲雀的羽毛扒光,廢了四肢,丟進了監獄。 金絲雀拿著那支綴滿寶石的筆,在掌心寫下:【我不愛你了】幾個字,毅然捅進自己心髒。 那一夜,監獄到醫院全城封路。 宴先生跪在手術室外,虔誠祈禱。 他什麽都不要,就要在地獄裏把他的金絲雀搶回來!
43.6萬字8 2021 -
完結217 章

濃夜難渡
酒桌上,不知誰提了一嘴:“聽說夜濃回來了!” 沈屹驍手裏的紅酒微微一晃。 有人起鬨:“想當初咱們沈總和夜濃,那可是轟動一時啊!” 大學時,沈屹驍和夜濃談了一場轟動全城的戀愛。 沈家是頂級豪門,而夜濃除了有一張頂級的臉蛋之外,一無所有。 所有人都認爲她纔是被拋棄的那一個,卻不知,那晚的宿舍樓後,最能藏污納垢的陰影裏,沈屹驍把她吻到近乎窒息,最後卑微求她:能不能不走? 可她還是走了,頭也不回。 * 夜濃隨公司回京開疆闢土。新接的項目,面對甲方各種刁難,夜濃不得不親自出面。 夕陽下沉,夜濃在那間過百平的辦公室裏見到了沈屹驍。 他站在霞光粼粼的落地窗前,臉色沉,聲音冷:“好久不見,夜小姐,別來無恙吧?” 當年在他的庇護下,她驕傲、一身硬骨,但時過境遷。 以爲她會服軟,沒想到許久之後只等來一句:謝沈總掛念,我很好。 沈屹驍一步步走過來,影子蓋住她:“夜濃,被你玩了六年,求我一聲,怎麼了?” 可惜,最後服軟、求饒的人還是他,永遠是他。 那夜,書桌上的文件掉落一地,沈屹驍認命吻在她脣角:“夜濃,我上輩子是做了什麼惡,這輩子要被你這麼收。”
31.3萬字8 88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